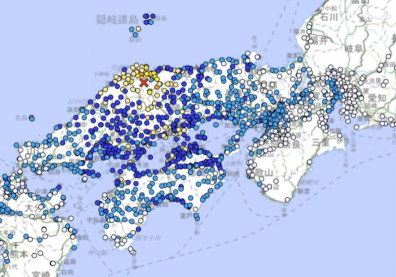現代版的「歐洲民族大遷徙」,總在寒、暑假期間進行,特色是緊張、倉促且瘋狂。
由假期的第一天起,各大城市的火車站,就擠滿了年輕的背包族,高速公路上一輛輛旅行車的塞車隊伍,綿延數公里,各大城市的機場,則更是一幅預備登陸諾曼地的光景;晨曦中,出境大廳已是上萬名睡眠不足的成人,匆忙地辦理登機手續;行李輸送帶上一捆捆打包的衝浪板(冬天則是滑雪板)、高爾夫球推車、折疊自行車;手提行李則是坐在娃娃車中的稚齡兒童,或在透氣塑膠籠中坐立不安的寵物。百架飛機以每五分鐘一班次的頻率,飛向東西南北。
一名威尼斯人,每年要碰到六十八名觀光客在巴黎羅浮宮內走馬看花;五百萬名迷路的觀光客,甚至迫使巴黎人紛紛「逃」往南法普羅旺斯及尼斯海岸;西班牙馬約卡島海邊一排排水泥渡假別墅,僅是今年七月的第一個周末,就住進了十萬名以德國人為主的遊客,他們心甘情願成為當地人口中「在攝氏四十度高溫下,每半小時翻身一次的海灘沙丁魚」;捷克首都布拉格的老城鐘塔下,聚集了一群群西班牙、義大利、希臘的旅遊團,等待十二點鐘響時的玩偶表演。
用盡力氣放鬆
在各觀光勝地的旅館區、海濱渡假區,旅遊業者每天推出不同的節目表:古蹟廢墟的一日遊,潛水、帆船、網球課,乘坐越野吉普車狩獵;各種表演秀及迪斯可……,目的在讓大家覺得緊湊、充實,不虛此行。
儘管仍有許多擅長渡假的歐洲人,喜歡在奧地利、瑞士或瑞典的山區渡假小木屋或農莊裏,靜享為期兩周到四周的田園生活,儘管仍有歐洲人嚮往在夢幻海灘邊做日光浴一邊看書,但是愈來愈多人卻認為這種什麼也不做的渡假方式,缺乏「內容」,糟踢了難得的假期。他們要求盡量「經歷」,向自己的體能極限挑戰。要求刺激,希望最好由下機到搭機回程,沒一刻空檔。
旅遊業者也樂得提供「倫敦健身俱樂部三日遊」、「亞熱帶克里米亞島五日遊」--賣點是搭乘前蘇聯的軍用噴射機,或阿爾卑斯山全能之旅兩天急流泛舟、兩天騎越野車登山,兩天滑翔翼,更刺激的有攀上阿爾卑斯山冰河峭壁,然後作自由落體下降運動(bungee)。這股新潮流的渡假主張是「你應該完全放鬆,用盡全身力氣放鬆」! 位於大西洋的西班牙小島蘭查洛特(Lanzarote),騎駱駝的乘客和越野車騎士摩肩擦踵。拉聖塔健康俱樂部中,前世界空手道冠軍休斯卻吼著:「盡量動!」「腿抬高,左右左右……,」六十名汗流挾背的渡假客,拚了命趕上節拍。
二十六歲,來自德國的製藥廠員工海納,邊喘邊直呼:「只有懶鬼才躺在沙灘上。」她每天的節目表,豐盛得讓人喘口氣才念得完:早上體操、拉筋、舉重及在爬階訓練器上爬一小時的樓梯,下午有氧舞蹈、晚上壁式網球,臨睡前再游個幾百公尺自由式和蛙式。也是來自德國的三十一歲瑞斯則小聲說,「看在交了那麼多錢的份上,也得多利用,這兒的器材和設備。」
創辦這個附設有一千個本位健康俱樂部的丹麥人龍略,對高達八0到九0%的住房率頗感驕傲,他還預備將運動和島上探險的活動更緊密結合,並提供跳傘課程,「這類俱樂部會風行,因為大家?控o一定要把自己累死,才划得來!」
即使所謂的學習旅行,也是用滿滿的經歷裝填;文化之旅是兩周密集的填鴨課,介紹城市歷史、建築、藝術或馬不停蹄地參觀藝術季;參加「橫越新幾內亞之旅」的德國人,將在短短十二天內,於面積四萬六千平方公里的島上活動。行程包括四次境內飛機之旅、三次木船之旅、四整天定點郊遊,拜訪五種不同的土著民族;被亞洲異國風情吸引的歐洲人,則得在北京、上海、拉薩、加德滿都之間起降五次。
這類將渡假的幸福感完全任由旅遊業安排、行程滿檔,不讓自己空閒片刻的方式,亞洲人或許耳熟能詳,甚至覺得理所當然,但是假期多,又最有渡假經驗的歐洲人,為什麼也開始忽視閒暇本身的重要,而在假期中要求速度和經歷密度?
押在一張王牌上
漢堡的社會心理學者文利奇.微特分析:「人們想填補一些在工作時感到的空虛,而且還有虛榮心作祟。」希望獲得周遭認可的人,特別要報告一些不尋常的經驗和活動,「黑森林健行的老生常談,自然不如攀爬喜馬拉雅山驚險萬分的恐怖經歷來得引人注目。」他說。
法蘭克福的一位旅遊公關負責人梅耶則觀察道,「很多人其實很害怕寧靜,因為他們不知道如何和自己相處。」再加上觀光客通常將金錢、時間和精力「押在一張王牌上」,自然要強調經歷愈多愈好。
瑞士伯恩大學觀光研究所的約思特.克利本道夫(Jost Krippendorf),早在八0年代就以一本「假期人類」,成為批評觀光行為的先鋒。他認為,假期的古典定義,是「一種自工業社會的日常生活中解脫,回到自我的狀態」,因而其有紓解因工作而產生的疲勞及緊張的功能。但是假期商品化之後,速度和經歷密度變成品質保證,消費者就必須自我折磨,才能享受假期,「這種投入、講求效率的假期,其實是日常工作的另一翻版。」克利本道夫表示。結果渡假變成紓解疲勞的「工作」,和壓力、懊惱、失望長相左右。
根據德國明鏡周刊的調查顯示,五分之一的德國人覺得上一次假期休息調養的價值「相當低」或「非常低」,四二%的人被塞車及班機誤點搞得一肚子火,二五%抱怨所付價錢和所獲享受不成比例以及天氣太差,一二%受不了爆滿且吵雜的旅館及差勁的服務,甚至在全體渡假的德國人,它有一半慶幸「終於又回家了」。
而帶回家的「紀念品」,已不再是海灘撿來的貝殼,而是腹瀉、胃痛及輕微瘧疾。渡假期間健康出問題的,已不再限於心臟衰竭的退休老人,愈來愈多逞強的年輕人,果真把自己累得「半死」。身體無恙的,也常因乘坐長途飛機,極端氣候轉變、水土不服,在法國汽車拋錨,在邁阿密害怕被暗槍射殺的種種壓力,長期陷於沮喪及恐懼的低潮。
家裏也有渡假美感
到底如何才能渡過一個所謂健康、美好的假期,已經成為心理、文化、社會、觀光學者研究的課題。
德國巴伐利亞那那貝格大學的社會學者--「經歷社會」一書作者傑哈德.舒茲否認乾淨的旅館、豪華的遊輪或美麗的風景,就能保證會產生一種「我渡假了」的滿足美感。「因為由經歷的事物到經歷本身這一步,必須由我們自己的注意力、想像力及耐性加以轉化。」他表示。而且這種美好的感覺通常是在不刻意強求的狀態下自然到來,但是全世界的觀光業、各種商品部卻企圖安排、販賣這種感覺。
舒茲和許多相關學者都認為,只要釐清假期的意義,即使待在家中,也可以產生渡過假的美感。果真如此,也許有一天,巴黎羅浮宮裡的蒙娜麗莎,終將可以靜享沒有觀光客的悠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