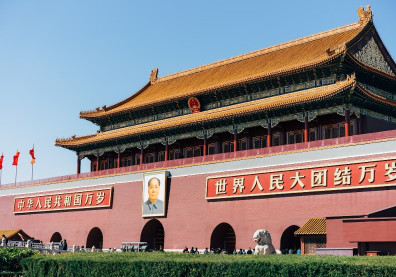周光召:我覺得最近幾年兩岸科技合作的進程在加快,第一個階段是互相瞭解,也就是互訪;第二個階段是實質性的合作;我相信在下一階段,兩岸的科學家可以共同攻某些科技的關鍵問題。
前年開始我們和台大海洋所合作研究南海問題,研究那一帶的地質、水文、動植物、海洋和大氣的關係,今年四月又要一起進行觀察。實際的科技合作會加速兩岸科技發展,很多是有市場潛力的,將來共同開發新的產品、提高質量,在國際上的競爭能力前景很廣闊。
使合作生根
沈君山:互訪有兩個問題,一是政策,一是經費。基本上基礎科學是個人的,就像做生意把攤子擺好。我常覺得有很好的計畫反而不行,給它一個架構,靈活應變是最好的。現在個別科技人才已經可以互相來往,而且國科會可以提供一些錢。舉個例子,現在清大物理系有好幾位從中國科學院來的。互訪除了科技合作之外,雙方瞭解也很重要,因為瞭解是建立任何交流的基礎。
現在在大學中互訪差不多都是五十歲、六十歲的人,將來由博士後研究員或研究生互訪,可以使合作生根。另外也可以延攬在海外非常傑出的中國科學家。
林垂宙:產業科技交流的問題比基礎科學多一點。以工研院為例,這二年有三百多人到大陸去過,我認為除了增加彼此瞭解外,沒有什麼重大結果。問題在哪裡?一是支離破碎,缺乏規畫,另一方面,目前的交往還很表面,不深入。
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主要是彼此信賴的問題。講到產業,大家擔心對方會不會把我吃掉了?有沒有牴觸我政府法令?現在大陸方面很願意跟我們談光電、電子、半導體方面的合作,可是我們的困難是這些工作都是政府花很多經費做出來的結果,如果和大陸合作,政府會不會同意?這是法令上的問題。
我覺得大陸在應用方面,從材料到產品之間的技術開發,做得不多;台灣這些年來開發關鍵性零組件,然後賣給人家。除了材料、市場的支持外,.我認為兩岸可以一起做研究創新,結合彼此的智慧、經驗、創造力,互相幫助。
現在大陸的鍋鐵技術非常好,每年有一千多萬噸的進口,台灣有六、七百萬噸的產量,四分之一外銷。鋼鐵產業的特性是也進口也輸出,因為是不同的產品,這其中就有很多產業的機會。
找出具體課題
在污染防治方面,工研院有幾樣很拿手,例如養豬廠。大同養豬廠可以養二十萬頭豬,本來養豬廢水使整個高屏溪變成黑的;經過三年多的時間,我們幫它設計、規畫,然後由廠商自己去建造,現在排出來的水已經達到一九九八年的環保標準。
我們現在也將技術scale down(下放),使小的養豬場也可以做好污水處理。又如染整廠、紡織廠,廢水也多,我們現在的技術很好,這些都是我們可以合作的地方。
另外例如航空,我們一直在說要建造小飛機,但是市場在哪裡?沒有開放的內需市場,很難跟別人競爭。大陸現在有很多regional airports(區域機場),可以飛那種二、三小時的小型飛機,如果我們能和大陸達成某種程度的協議,大陸可以部分採用這種飛機。這家公司一旦有了二百架至二百五十架飛機的製造經驗,很快就可以達到經濟規模,它就可以到世界上去競爭,去占這個市場。有這樣的機會,我們的航空工業就起來了。航空工業的政策必須要和航運政策配合。從nationalscope(民族視野)來看,的確有大規模的機會。
再以核廢料處理為例,台灣馬上有第四個核能廠,是不是應該把高濃度的廢料,用濃縮的技術、或用精密陶瓷的技術,把它變成一個個tube(筒),放在沙漠底下?或是利用核物理或核化學的方法,把其中的放射性改成半衰期,變成比較少傷害?這裡頭有很多科學、技術可以合作的地方。在這個領域如果有所創新的話,在世界上也可以揚眉吐氣。
上述提到的各方面,我覺得都可以勾畫出具體的遠景。希望兩岸從這個立場找出特別的課題來,由有實務經驗的人來深人探討,我相信一兩年後就會有結果。
表面交流頻繁
李亦園:兩岸科技的交流和兩岸分別跟不同國家的科技交流,基本性質上比較接近。但是兩岸的人文社會交流跟其他國家絕對不一樣。從同一個母體發展出的兩種文化,互相交流,我的感覺是相當特別的。從前以台灣為基礎所做的研究,換到大陸去做,非常有感觸。
一般來說,在人文領域裡,大陸水準高,尤其是歷史、科技史、語言學、文學經典。但是在社會科學方面,因為大陸在三0年代碰到一些困難,所以這個領域裡台灣較領先。這兩門學問不一樣,更顯得交流有意義。
雖然這四、五年頻繁地交流,但是很多地方還是非常表面,互相不怎麼清楚,實際上不能找到很對等的單位。人文學方面,我們的確應該多邀請大陸學者過來,做長久的講學。會議假如能對得很好的話,也會很有效果。
今天社科院有十二位歷史學家跟考古學家來,跟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的考古學家一起座談,會名叫做「考古學與歷史學的整合交流會」,這是自有交流以來第一等的會。
三個模式
人文學方面雖然交流多,但有系統的交流較少。社會科學方面,目前有三個模式已經開始在做。
第一個就是兩岸的研究整合,在一起組成一個team(團隊)做研究。這是互補最好的例子。實際的例子是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經過美國史丹福大學的介紹,在八九年和廈門大學社會學、歷史學、人類學及台灣研究所,合在一起,在福建選了十個縣做調查,台灣也有十個縣做調查,比較這兩省鄉村、農民之間的差異。三年中要完成二十本報告,研究的內容完全一樣。
經過史丹福大學的聯繫,這個計晝今年馬上會延伸到上海社科院和師範大學,把研究的範圍延伸到江浙。除了得到結果外,研究方法上的互相影響,台灣在社會科學的調查方法上比較強,大陸廈門大學在蒐集地方史資料上很好。兩方面配合起來結果很好。
.第二個模型是清華大學的一位教授研究大陸十省的「儺戲」--即面具戲,是所有戲劇的老祖宗。這位教授在研究技巧、方法上很強,在大陸選了十個地區,經過文化部同意,中國藝術研究院幫忙,在十個地區由大陸學者協助做研究。每一年都有聚會,第一年在廣州,第二年在香港,今年在台北,互相討論研究結果。不僅研究資料非常好,也學習到更好的研究方法。可以把埋在中國文化底下的東西慢慢挖掘出來。
第三個模式是非常特別的模式。楊國樞教授現在在北京的別號是「現代的武訓」,他替社科院社會科學研究所辦了一個「社會心理學」研究班,每年暑假在大陸開班,招收全國的學生講社會心理學的課,學成後頒給證書。
社科院第一年經費較充足,第二年沒錢了,楊教授就自己出錢,到處募捐,連講義都自己帶去。這也是另一種模式,把台灣比較強的社會科學傳播過去。
社會科學方面,如果照上述三個模式擴大發展,我想這個交流更有意義。
困難猶多
沈君山:兩岸學術交流碰到的困難,有三方面,一是技術面,另一是行政面,最後是政治面。
技術方面彼此互補很多;行政面雙方有很多困擾,一位台灣的教授要進口一部望遠鏡至大陸做研究,跑海關跑了五十次。
在政治方面,台灣這幾年有三個變化:本土化、民主化、現實化。
現在絕大部分在台灣從事科學工作的人和領導的人,都是成長於台灣,當然把台灣當一個主體,而不會從一個中國為主體來看問題。
另外,民主化以後,選票出政權。由於本土化,很多人為了維持目前的政治地位,不管他內心如何想,都要表現出「腳步不能太快」的心態。譬如現在很多人擔心台灣的產業空洞化的問題,這就是非常政治面的看法。此外,選舉時一旦背上「賣台」的名義,就非常不容易當選。
第三個變化是現實化,現在台灣幾乎沒有意識形態,也沒有民族心態。大部分台灣手上握有選票和政權的人,已經很少有「中國心」,現在只有現實主義可以解決上面的問題。
兩岸要談「雙贏」的問題,光嘴巴講是不夠的,還要克服「不安全」的心理因素。台灣和大陸相比,大小、人口都很懸殊,因為不安全感,所以必然產生一些現象。
民主化要有幾個條件,第一是要有共識,「一個中國」如何使得一般人能接受?這是高度政治化的,一個中國若是中共統一台灣,中央政府在北京,中共是唯一合法政府,台灣就被統一掉了。
第二是共信,有共識不一定有共信,就是比進黨和國民黨有共識的話,雙方還會猜疑。共信之外,還有最不相信共產黨。
台灣提出三個條件:放棄武力、對等政治實體、國際活動空間,其中以對等政治實體最重要。
假如完全從主權的立場談一個中國,這很難在台灣行得通。台灣和福建完全不一樣,在歷史上台灣有一百年不和大陸在一塊,三代思想完全不一樣。大陸講一個中國,主體必須在北京,他們認為已經讓步讓到最後,台灣會受不了,這個問題要等到下一代才能解決。
名稱傷感情
林垂宙:在科技交流上,雙方先要互相尊重,才能談合作。很傷感情的是,在純粹科學、工程或技術的會議中,大陸的代表,常常不許台灣去的學會代表用「中國」(chinese)這個名字,我個人就碰到好些例子。我常跟人家解釋,我們學會完全是學術性、專業性,亦不代表政府。
我們所用的「中國」(Chinese),是指團體的「包容性」(generic)、「文化性」(Cultural)及會員的種族「屬性」(ethnic),沒有政治意義,為什麼一定要改用「台灣」或「中華台北」等可笑的字眼呢?就如我們去吃「中國飯」(Chinese dinner),難道也要把它政治化說明是ROC或PRC嗎?
其實「中國」這個名稱,誰都沒有獨占的權利。如果大陸的同仁堅持要台灣同仁用「中華台北」或「台灣」,除了刺傷對方感情外,無形中不是助長了「一中一台」或「台獨」的說法嗎?這豈不是與原意背道而馳?
我希望政治領導階層能夠從大處、遠處考慮,凡是專業性、學術性的會議,所有相關名稱的爭議,一概擱置,讓兩方先談科技,先談學術,「延期清理」政治議題。這樣一來,對雙方科技學術交流、人員的互信,一定有實際的貢獻。
有句話叫「以大事小」,做大哥的必須要犧牲多一點,多給人家一點包容。台灣和福建、廣東不大一樣,中間有台灣海峽隔著,又和大陸分離那麼多年,需要特別包容。
這十幾年是很重要的關頭,再過幾年,我們都退休了,四十歲的人都在這裡長大,在這裡生的,就不像在福建生的,對中國有感覺。如果我們沒有把握這個時機,將來更困難。
各讓一步打破伍局
突破兩岸關係的瓶頸,需要無比的耐心、務實的做法和高度的智慧。我想起一個故事,說不定可做一個註腳。
十九世紀英國有一位重要的政治家,叫格萊斯東(William Gladstone),他在政壇上有一位敵手,叫做狄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兩個人常常針鋒相對,互不相讓。傳說有一次格氏在鄉下訪問,在一條羊腸小徑上正好碰上了戴氏的來車,路窄車大,很難並行而過,戴氏讓人放話說,「我絕不讓路給不講理的人」;格氏想了一想,斟酌情況,今車夫稍退一步,讓對方過去,他也讓人說「我遇到不講理的人,經常都會讓路」,一場僵局,就此解決。這個故事,說不定有一些啟發性。
周光召:兩岸名稱問題的確困擾我們很久,八四年就開始困擾。我們也希望能找到更好的辦法,因為這個對科學家來講,特別傷感情。現在問題的難處是:按照國際法,一個主權國家只有一個中央政府,有這個基本的邏輯在裡面,就使得所有問題都有問題了。
到目前為止,我還想不出用什麼辦法來解決問題,最好是雙方先承認一個中國,然後民間團體去談。假如不談,我提要「一國兩制」,你提要「一國兩府」,那就完了,僵死了。
我總是感覺到,現在是到了中華民族可以在世界上站起來的時刻。我覺得大家還是要共同把這些事情弄好,怎樣雙方能夠多對話,政府對話就是兩個政府,國際不容許,就不好辦了;也許是民間對話,民間最大的還是黨。
現在我們這樣做,對雙方都不利,強調本土利益也不一定最有利,如果直接有個場合談的話,可以增進雙方的瞭解,然後大家再慢慢解決問題,「非零和」的情況就是雙方要做出讓步。
民族主義是有不好的地方,但是民族主義是民族的文化、歷史、認同感,這還是重要的。我覺得台北的故宮博物院做得很好,進去以後對這個民族感到驕傲。
歷史問題
很多兩岸的事,不涉到國際,不會發生問題。一牽涉到國際,又牽涉到兩個中國、誰來代表中國等等複雜的問題。這是長期的歷史形成的,需要有很高的智慧才能克服。雙方都要跳出來,站在對方立場想一想,才能想出解決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