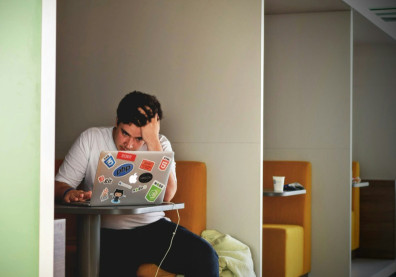民國四十二年(一九五三年)九月成立的工業委員會,對國家或對我個人,我都認為具有重大的意義。
就國家言,它是締造台灣經濟發展奇蹟的最核心機構之一,特別是對工業建設的策畫和推動,產生了最關鍵作用,因此我們稱工業委員會召集人尹仲容先生為「台灣工業之父」並不為過。就我個人言,從那一年我踏入工業委員會開始,幾乎一生都和台灣經濟發展糾結在一起,前後四十年,綜括了我一生的職業生涯。
在寫工業委員會之前,必須先略述經濟安定委員會。政府遷台初期,大部分政務都還委託台灣省政府代管,財經事務亦復如此。記得多年前嚴靜波(家淦)先生在閒聊時曾說:當時的台灣省財政廳長要比財政部長神氣多了「絕大部分的財政收入都掌握在省財政廳手中,中央的財政部要錢,須向財政廳長叩頭,連一向由中央直接管理的海關,當時的省主席陳誠先生曾下過條子由台灣省接管,還是嚴先生勸阻才未成為事實,由此可知當時省和中央地位的關係。
因此,經濟事務(包括金融、貿易等等)都由省府掌管,省設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簡稱生管會,掌一切經濟事務的生殺大權。主任委員由省主席兼任,實際業務由常務委員主持,徐柏園和尹仲容先生先後擔任了常務委員。另外省政府還設有一個外匯貿易小組,由財政廳兼理。到了民國四十二年,中央政府在台灣漸漸站穩了腳跟,當時政治的強人也由省主席而行政院長,原來掌財經大權的省級機構也轉至中央來了。
首先是行政院裁撤生管會,於四十二年七月二日成立經濟安定委員會,賦與財經事務參謀總部的權限,在經安會之內設立五個單位,中文名稱為第一組(討論金融外匯)、第二組(討論物資供應計畫)、第三組(討論經援與軍援的配合)、第四組(討論農業政策與計畫)及工業委員會(討論工業政策與計畫)。
財經參謀總部
由於當時政府財政和經濟發展都十分依賴美援,經安會及其所屬組、會開會時,都請美援官員列席,所以各個機構都配以英文名稱,經安會稱ESB(Economic Stablization Board),第一組至第四組稱為ComissionA、B、C、D,工業委員會為IDC(Industry Development Commission)。
為什麼其他各組稱「組」而掌理工業的單位叫「委員會」呢?據說各組的性質為內部幕僚,討論的結果送給各主管機關執行,農業部分因為有農村復興委員會(蔣夢麟為主委,蔣彥士為秘書長),所以不再另設委員會,以第四組的名稱和有關機關協調聯繫;工業部分則一面要和美援機關商討美援運用於工業部門的計畫,一面要為這些計畫找投資人並追蹤其執行,另外還要研議推動工業發展所需的各項政策,就特別以委員會的方式來設立。
四十一年的夏天,我在立法院服務,在偶然的情況下,為朋友介紹去應徵中央信託局局長室祕書工作,那時的中央信託局局長正是尹仲容先生,經過面試後獲選,可是我一時不能離開立法院,就約定每星期一次到局長室擔任局長口述紀錄的工作,挑定的時間是下午五時半以後。
這樣經過一年,工作量不斷增加,除了口述文件的紀錄外,有時還要參加局長主持的會議,擔任紀錄,甚至為他撰寫一些文稿。在我來說,工作覺得太重,時間分配不來,在尹先生來說,常因找我不著而焦急地等待。
到了四十二年八月間,有一天他忽然找我詢問我的待遇狀況,旋即表示如果為我找到一個待遇較優的工作,可否辭去立法院的差事。我和他共事已經一年多,對他的瞭解也增進了不少,覺得仲容先生無論在學識、才能、品德以及對國家的忠誠方面,都是可敬的人才,同時一年相處,在工作中對台灣經濟的認識加深許多,從而培養起對經濟建設工作的熱忱。就這樣於四十二年九月踏入了工業委員會,一直工作到四十七年八月底經安會和工業委員會歸併美援會為止,前後歷時五個年頭。
現在回想起來,工業委員會對我國經濟的安定和發展,具有不可磨滅的貢獻。在介紹其業務和成就之前,先簡要地介紹一下這個機構的組織。
效率特高
工業委員會設召集人一人(尹仲容),委員由各有關機關的首長兼任(如經濟部長、交通部長等等),另外置專任委員三人、負實際工作責任,這三位委員是李國鼎先生(主管一般工業)、嚴演存先生(主管化學工業)、費驊先生(主管交通計畫),另外還設一個財經組,由潘甲先生領導,擔任經濟研究和財務分析的工作,此外還有個秘書室。
委員會的人員約三十餘人,絕大多數是理工科的技術專才,各就專長負責一門工業。例如一般工業組延攬的多為紡織、機械、電機、木材加工、金屬、礦冶等工程師;化學工業組則分為有機與無機化學兩大部門;交通組分別有公路、鐵路、港埠、通信等專家;學社會科學的則多集中在財經組;行政管理只設一個秘書室,掌握總務、文書、會計、人事等等,一個人要辦二種以上不同的事務,根本沒有今日各機關所設的人事室、會計室、總務處之類,可以說是中華民國有史以來最精簡而又效率特高的一個機構。
這個機構的人員後來不少都成為台灣經濟發展中的傑出人物,除了尹仲容先生外,李國鼎先生和費驊先生曾在政府中擔任部長級職務,為時甚久,嚴演存先生是一位專家型的人物,很早就應美國史丹福研究所之聘擔任客座教授,並不時為台灣工業發展擔任顧問的工作。
在一般工業組服務的張繼正先生,後來擔任交通、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總裁;另外當時在財經組工作的王作榮先生已成為台灣極知名的經濟學家並擔任考選部長;另外一位在財經組工作的錢純先生,後來成金融界的重要人物並曾出任財政部長;其他擔任財經兩部次長、經建會副主委和有關部會局長、司長級人物的還不在少。可以說,這個機構為國家培育了不少人才,在民國五0年代至七0年代為經濟建設的關鍵人物。
資金、外匯奇缺
工業委員會存在的五年中,到底做了些什麼事,在說明之前還須先介紹一下當時台灣的經濟背景。
台灣於光復之初,一方面由於二次世界大戰原因,人力大量被徵召赴外作戰,加上戰爭末期美軍轟炸的摧殘,農業生產力銳降;另一方面台灣在日本統治期中,本來就以「農業台灣、工業日本」為基本經濟策略,因此台灣只是提供原料到日本加工,本身無現代工業可言。在此種情況下,當時的台灣經濟自然物資、資金、外匯各方面都極端缺乏。
處在這一經濟背景之下,政府最急迫的工作是設法取得更多的物資供應,其次便是如何增加生產能力。這兩個工作在一個落後又貧窮的社會,都是大難題。幸好在一九五0年(民國三十九年)發生的韓戰,給了我們一個機會。
在韓戰發生後,至少我國在經濟上得到兩個力量的支援,一個是美援恢復了,除了軍援還有經援;另一個是美國注意到利用台灣有限的工業,可以為美軍從事若干物資的生產,這方面最顯著的恐怕是石油煉製。本來中油的高雄廠陷於外匯短絀、油源困難的境地,此時透過美國的關係,使中油和海灣石油公司建立了合作關係,由海灣提供原油交中油煉製。
善用美援
由於美援的恢復,我國運用美援於兩個主要方面,一是利用美援資金購買各種物資,填補我國物資的不足。對在今日台灣的人民而言,恐怕很難體會物資缺乏時的生活艱困狀況,因為今天國民儲蓄、外匯都非常豐沛,既有足夠的能力進口所需的一切物資,國內又有強韌的工業產力,可以滿足消費者的需要;另一方面便是如何運用美援來幫助國內工業的興起,以逐漸擺脫對進口的倚賴。
關於前者,很多進口物資的審核和分配工作,便落在工業委員會身上,這包括棉花、小麥、黃豆、牛油、馬口鐵……等等,甚至連國內生產的水泥也由政府來決定配售的對象和數額。這在今天看來,是種非常主觀的落伍做法,不但極易引發有權者濫用權力圖利的流弊,而且也嚴重地違背了市場法則,可是在物資、外匯奇缺的狀態下,又不得不出此下策,好在當時的主持官員都期望這種人為管制只是過渡時期的階段性做法,後來由民國四十七、八年起便陸續予以放棄,逐漸恢復了市場機能。
關於後者,就是如何培養國內的工業能力,以達到減少對進口倚賴的目的,這尤和美援有密切關係。首先是美國援外機構希望我國有一套經濟逐漸自立自足的計畫,做為運用美援的依據,在這個要求下,我國在民國四十二年制訂了第一個四年計畫,我還清楚地記得這個計晝原由台灣省政府草擬,標題為「台灣經濟自足自給計畫」,內容甚為粗略,只包含農、工、交通三部分若干計畫,和今日的經濟計畫之涉及社會各部門的配合條件相比,算是原始多了。這個四年計畫再由工業委員會和經安會第四組逐年檢討修訂補充,就成為國家經濟發展的藍圖。
當時在這個計畫下,先後推動建立的工業有紡織工業、麵粉工業、榨油工業、玻璃工業、造紙工業、塑膠工業、人造纖維工業、肥料工業等等,另外並對電力事業大力支援,使工業用電逐漸無虞匱乏。我們今日回溯當年經濟發展的經過,可說這一時期建立工業的工作,是為今日台灣強盛經濟力奠定了基礎,但在推動的過程中,也曾飽經爭議,才把握了幾項正確重要原則,才能導致後來的成果。
堅定掌握原則
所謂幾項重要原則,我的瞭解是:
(一)民營化:在我國傳統的歷史背景中,「發達國家資本」常被解釋為建立更多的公營事業,因為在過去數十年深入當政者的腦海中,認為民營事業的基本目標在追求個人的利益,易於罔顧社會整體的利益,因此而有「節制私人資本」的主張。
在這個背景下,當時運用美援發展工業,能夠建立優先鼓勵民營事業發展的策略,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這至少要歸因於以下兩個因素:一、美援當局的堅持。美國是個以民營事業為主幹的經濟結構。美國援外機構在運用美援時,自然要求受援國家優先發展民營事業;二、當時主持國家經濟建設的官員認為引導社會資金投入國家經濟建設,可以匯集更大的力量,加速經濟的發展;在這內外相互呼應之下,終於成為攻府的重要決策。
在今天看來,這一決策對以後經濟發展的確有極為深遠的影響,這包括民營事業建立獲利後,幾乎都將獲得的盈餘全數用於再投資,使產業能力不斷增加(公營事業盈餘的很大部分都被視為政府的財政收入來源繳交公庫,因此他們的再發展能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其次則是因為民營事業的勃起,培養了眾多企業人才,成為經濟再發展的生力軍。
(二)建立健全的財務制度:這一點特別適用於若干具有公用性質的產業,包括電力、自來水和電信事業,施行比較成功的是電力和電信,自來水則是失敗的例子。
一念之失,成就有別
記得在四0年代初期,美援提出援助電力發展的條件之一,便是電力費率必須有一個客觀的計價公式,當報酬低於一定標準時,便應加價,反之則應降價。他們的理由認為,只有這樣,電力公司才能保有健全的財務結構、才有能力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獲得資金的融通、才能使電力公司能夠獲得財源,不斷地增加投資、增加供電能力。可是國內一般人的想法則南轅北轍,以為電力是民生最基本的需求,也是工業的動力,應當不惜工本,以最低價格供應。
在這兩種思想相互激盪之下,電力費率的訂定便在經濟的考慮和政治的考慮之,徘徊不決,於是美援方面施出撒手間,要停止對電力援款的支持,而電力投資龐大,是資本密集的產業,且投資回收慢,如無美援支持,以當時國家經濟能力和國際債信,根本借不到擴充所需的資金,而當時電力供應極端不足,經常要實施限制用電,問題甚為嚴重,執政最高當局在聽取經建官員的剴切陳詞後,終於發出堅定的要求,要立法部門迅即通過電力計價公式。
那時我正在立法院行將離職,有機會目睹那次立法院院會討論電價案的情況,起先是一面倒地反對電價公式,當時的經濟部長鄭道儒先生毫無招架之力(其實對電價公式用力最多的是尹仲容先生),討論終日毫無結果,忽然主持會議的張道藩院長宣布休息,原來他接到電話,奉召面謁國民黨蔣總裁,匆匆離開會場,回來時已是傍晚,繼續開會,並且改開秘密會議,張院長在會場中報告總裁強烈指示這個案子必須今天通過,講話時表情嚴肅,於是會場一片靜默,通過了電價公式案。
做法務宜
在今天看來,這個議案對台電公司的健全發展,提供了最關鍵的條件,也為台灣社會進步所需的電力提供了發展的契機。相反的,自來水計價公式在地方議會遭杯葛,陷自來水公司財務於不健全狀況,嚴重地影響自來水事業的發展,造成大眾的損失,謀國者的一得一失,歷史自會給予正確的評價。
(三)確定了工業發展的順序和目標:記得經濟發展計畫寫得很漂亮的國家中,印度要算是一個,可是印度的經濟發展成就欠佳。其致力於重工業的發展,以為有了重工業就是進步的國家。另外也很易使我們想到清末我國遭列強侵略,幾次戰敗,看到列強的「船堅砲利」,便以為建幾個造船廠、機器廠,便是現代化的國家,可以說都犯了皮毛觀察的毛病。
政府遷台以後,主持經濟建設的人,放棄了那種好高驚遠的做法,利用美援物資和美援小額貸款,建立國內急需的消費品加工業,可以說是最務實、最低調的做法,也是最實在、最有效的做法。有了這些工業,雖產品的品質不是很好,產品的價格在嚴格的貿易管制和極高的關稅保護下也相當偏高,對消費者是比較不利的,可是為了節省國家外匯的負擔(那時外匯極為缺乏,國際收支靠美援幫助才能勉強平衡),為了增加國內的就業機會;這樣做是必須的,後來我們把這一階段的工業發展稱為「進口替代時期」。
可是我們不能長期維持此種狀況,必須使我國產業在保護的溫床中破繭而出,做到有能力出口、在國際市場上與他國產品爭衡的地步,接著就展開了各項鼓勵出口的措施。但在工業委員會時期,已注意到這個目標而且開始孕育產業的能力,思考如何建立達到這一目的所需的各種條件,在以後的年度中陸續採行。(這一部分的改革主要在民國四十七年以後,後文再敘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