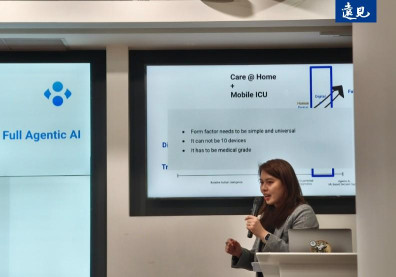「《親愛的》是我這麼多電影中拍的最好的一部。」香港導演陳可辛在接受搜狐視頻訪問時這麼說。
訪問過許多創作者,通常他們很難評價自己的作品何為「最好」。然而,遇上了《親愛的》,陳可辛卻難得為此片給了一個肯定句。
以中國拐賣兒童為主題的《親愛的》, 去年在大陸上映,就創下了將近3.5億(台幣17.5億)人民幣的好票房, 此片亦同時獲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及「最佳編劇」等提名。美國《時代》雜誌甚至將此片列為去年舉辦的威尼斯與多倫多兩個電影節的最推薦電影之一。

飾演農婦的趙薇,也曾在訪問中表示這是她生平最難演、也最滿意的一次的演出。一直都在城市生活的她,為了飾演農婦,不但素顏演出,還特地得使用陝西聽來「土味」極重的方言。一開始,她仍對說方言沒信心,本來要求仍使用普通話,陳可辛仍堅持要她以方言演出。她特地回老家去,把劇本中的台詞,一句句的將方言記下來。到了後來,她只要一說方言,就想哭,將中國農村婦人詮釋得入木三分。
好多個「最」。陳可辛來台宣傳,與他再確認,這部片究竟在他心中是「最……」的片?最好看?最滿意?最挑戰?最……?
陳可辛這次的答案是:這是「最不像我的一部片」。
《親愛的》乃是根據中國真實新聞事件改編。他說,過去的《金枝玉葉》、《甜蜜蜜》、 《如果愛》等,多半是虛構的愛情故事。然而,處理社會真實新聞題材卻是第一次。

陳可辛原先是看了一部深圳工人尋子的紀錄片,深受震動,因而決定改編成電影。劇情描述一對離婚夫妻田文軍(黃渤飾)與魯曉娟(郝蕾飾演)的兒子田鵬遺失,歷經數年艱辛尋找,終在偏遠的農村尋回兒子。但兒子已成為農村婦人李紅琴(趙薇飾)收養,小孩也認定的母親早已是李紅琴……。警方卻發現,李紅琴已經過世的丈夫有拐帶兒童的歷史,除了田鵬還帶回另一個小妹妹收養為女兒。然而,李紅琴的丈夫生前只告訴她這兩個小孩是與別的女人生與「撿」來的。只有單純母愛、毫無社會資源的她,希望爭取孩子的扶養權……。
紀錄片何其多,為什麼這部的故事特別打動陳可辛,讓他想改編成電影?他說,人到了一定年紀,就會發現人性的複雜,遠遠超越傳統電影中「正反派」的二元對立。
的確,《親愛的》之所以深刻,就在於它不單只是傳統千里尋子、描繪父母之痛的芭樂片,也不是僅是同情弱勢、意識先行的社會片。劇中人物的階級層次分明,有從深圳打工的夫妻、工人、農村婦人、城市中經濟條件較好的土豪、律師、代表公部門的福利院院長,每個角色皆有自己的立場,人人心中的「情、理、法」關係各不相同。
回觀當前許多的新聞事件,幾分鐘的新聞往往就論定一個人的善與惡。在我們的生活中,是不是對人也充滿這種片段式的了解?
以下為《遠見》專訪陳可辛摘要:
問:此片為真實故事改變。您應該看過無數的紀錄片,為什麼就是這個尋子的故事特別打動您?
答: 很多記者問我,是不是自己當了爸爸,才比較關注孩子的題材?其實不是。若只是單純父母去找小孩的故事,我就沒興趣。原本的故事原型紀錄片到了中間,小孩找到了,卻發現找到是另一個悲劇的開始,這我就想拍了。
在電影裡,趙薇飾演拐賣者的老婆,傳統來說是反派,看了以後就知道事情沒有那簡單,電影到了一個小時之後,這個主角才出現,逆轉了原先的觀點。我們不能永遠是正方的角度,看待反方為反方。在反方角度,反方才是正方。
「人性的雙面性」,是我近十年來一直關注的題材,這個真實故事正好說明了這件事,才是這個故事最吸引我的地方。
問:此部戲的一大亮點,是所有的演員演得非常逼真。您怎麼引導演員完全進入這個故事?
答:選角非常重要,對後來的結果至少占50%以上。選錯了,怎麼弄都弄不出來。然而,這一半是直覺,一半是靠運氣,畢竟這些大明星不可能都試完戲才來演。
然而,這次從題材到劇本,是最好的一次,每個演員都想把戲弄好,我們每天晚上吃飯都聊,聊的時候不只是為了自己的角色,也會為對方的角色加戲。我也非常開放,讓整個片子有點像紀錄片的感覺,任何人有好的提議我們都可以來試,可以說是與演員的集體創作。
例如,趙薇坐公車中途跑下來,本來本來有台詞要與黃渤講,但那些尋子的父母要打趙薇,我要求他們儘管真打,拿著兩部機器對拍,一打起來,場面混亂得根本無法聽到任何人講話,原本劇本寫的台詞根本沒有機會講,連叫停都停不來。最後,趙薇只有抓著黃渤的手,說了一聲對不起,那是依照現場真實情形的表現,沒有都照著劇本演。

另一場戲,是趙薇去偷看小孩,黃渤抱著小孩倒垃圾,我們一開始一直想不到兩人該講什麼。吃晚飯時就和演員們討論,大家就說不如就說「別給他吃桃子」那句話。結果,那句是我最喜歡的台詞,也是片中最有感染力的一句話。那意味著侵略者講了一個只有你以為自己才知道的事,非親生的母親可能與你兒子的比你更親,那是很痛很痛的事。片中,有很多這些演員加的「神來之筆」。
(註:許多年前,陳可辛拍戲已經儘量不畫分鏡,讓戲完全呈現最自然的樣貌。)
問:電影一旦賺人熱淚,很容易被批評為「煽情」。您怎麼看待「感動」與「煽情」的界線?創作上如何拿捏?
答:雖然,這個故事我拍的時候哭,看的時候也哭。但是,也有很多觀眾告訴我,他們完全沒有哭。一部電影看到什麼,一百個人有一百個不同的答案,只要自己覺得不是煽情就不是。其實,這個題材本身,還可以煽情得更多倍,我從頭到尾都在克制,不停地做減法,例如,我刻意不使用太多音樂,這些都是一些抑制。
問:此部片觸及當代中國的社會議題,包括城鄉差距、農村受到的歧視等,您有特殊階級關懷的意識嗎?作為一個香港導演,您怎麼拍出中國的味道?即所謂的「接地氣」?
答:這戲雖然表面上是一個拐賣的戲,卻也浮現了許多中國當代的問題:包括城鄉歧視、外地人到城市打工導致婚姻破裂等,像中國社會的一面鏡子。
要拍出接地氣的作品,第一,要尊重細節,要找非常多的資料。第二,「要走心」。做的時候,自己覺得「走心」的態度很重要。其實,大陸農村的生活、外地人到城市打工的生活,很多大陸年輕的導演也一樣沒有經歷。或像我早期拍《甜蜜蜜》,其實我也沒有中國移民的經歷。有人說,是不是要到當地去住一陣子才能真正體驗當地生活?其實沒有。每一部電影,都要靠導演自己進入那個世界,我只會問自己,是不是每個過程中都有讓我「走心」?也讓人覺得「走心」?
問:片末,你放入了演員去拜訪原來新聞事件中主角的片段。可否談談你們與事件「本尊」會面的情形?他們看完電影後的反應如何?
答:在拍攝過中,我沒有讓演員與真實事件的主角接觸,免得給演員很大的壓力,我怕演員看了就會模仿。戲拍完時,我們邀請到了丟失孩子的父親、尋子會的會長、福利院院長角色本尊來看片,他們都很感動。至於趙薇飾演的農村婦人,我們則一直聯絡不上。
不過,此片一出,引起一些失蹤小孩的家庭不滿,在他們的眼中,對於拐賣孩子者,有很多怨恨與憤怒,覺得這件事沒有雙面性的可能。他們希望這是社會關注的話題,但沒想到你拍到農村媽媽的雙面性。但是,人性是複雜的,就算不是劇情片,好一點的記錄片也都應該拍出人性中的不絕對。
問:您一直提到人性與道德的「雙面性」。這不只是創作題材,也是你的人生觀?
答:年紀大了自然就會這樣看事情。我發現,若不這樣看事情,所有的事情都解決不了。 因為,當你覺得一個人是反派,那個人通常也覺得你是反派,因此,世界上其實沒有絕對的反派。若我不理解你為什麼覺得我是反派,是永遠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若我們沒有把自己心中 的反派變成有血有肉的人,這世界最後解決的方法只有打架或打仗。 因此,「雙面性」是唯一解決問題的方法。

(圖片提供:甲上娛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