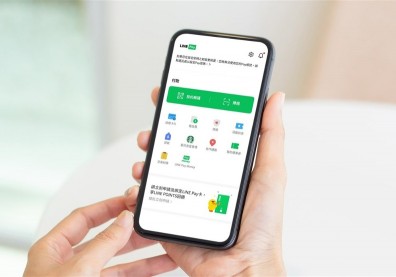在人民所得、縣政預算等財經統計上,宜蘭始終在國內各項平均值以下;在才情素質深度上,宜蘭人卻是風雲際會,群英競起。
在政界,在藝文圈,宜蘭幫舉足輕重。
組織全台灣第一個反對黨「台灣民眾黨」的,是宜蘭人蔣渭水;第一個公開撤人二、焚忠誠資料的地方首長,是宜蘭人陳定南;研究台灣鄉土文學,不能略過的是宜蘭作家黃春明;把歌仔戲唱到各個角落的,是宜蘭名伶楊麗花。
有人曾比喻,宜蘭人的性格就像宜蘭名產「糕楂」與「芋泥」,外冷內熱,硬要急急一口吞下,會被它毫不容情地燙傷。
外表純樸溫順的宜蘭人,就曾這樣燙傷原本以為志在必得的國民黨與王永慶。十一年前國民黨從未想到會在選戰中失陷宜蘭,並且愈輸愈多;而台塑企業董事長王永慶的利澤六輕夢,也在宜蘭人滾烈的抗拒中,熔成宜蘭人驕傲的歷史。
自然地理、歷史背景與社會人文相互激盪,捏塑出宜蘭人獨特的性格。
夾在雪山山脈與中央山脈間,俗稱「後山」的宜蘭,既不屬於北部,也不被視為東部。
由於地理上的阻絕,宜蘭人保存了較完整的傳統性格,迥異於其他地方人。濃重的宜蘭腔,「酸酸軟軟,吃飯配滷蛋」,便是宜蘭人特有的標籤。在縣史館工作的潘寶珠笑說,她到台北只要一開口,就立刻有人指認她是宜蘭人,「想逃也逃不掉,」她對宜蘭腔引以為榮。
清朝時,宜蘭對外陸路交通僅有草嶺古道一條,人煙難至,文明因此也只能氣喘噓噓地翻山越嶺到達宜蘭。是以,宜蘭在資訊文明競賽上,永遠慢幾步。
我群觀念強烈
攝影家阮義忠仍記得,三十年前他生長的頭城鎮有了第一台電視,全村的人圍在電器行前等著看;等了一早上,電視機還是收不到畫面。他慶幸宜蘭對外交通封閉,使得電視污染比外面晚了十幾年,宜蘭人得以繼續過他們古樸而悠閑的生活。
「宜蘭人是因禍得福,」復興國中邱水金老師也有感而發地說。
宜蘭的形狀,宛如一個大竹圍;宜蘭人就像住在一個大社區內,人和人很親近,無形中培養出一種集體意識。研究社會人類學的邱水金,用專業術語形容這種意識,就是宜蘭人的「我群觀念」較強。學都市計畫的林旺根觀察,當一個地區有完整清晰的地標時,這地區的人較容易形成深厚的地緣認同感。
濃得化不開的鄉情,變成宜蘭人的共同話題。
對鄉土的熱愛,滲進每個宜蘭人的潛意識中。在大學社團裡,蘭友會是出了名的活躍。負責規畫冬山河的象集團設計師陳永興接觸工地工人後發現,工人們只要想到是替宜蘭做事,就會更拚命。有些宜蘭人甚至不計時間、金錢地投入;生長在冬山河畔的邱水金就是一例。他利用課餘時間做象集團顧問,並訓練冬山河解說員,至今仍未領任何薪水。
「要是在別的地方,這工作可能早就結束了。」自稱是宜蘭的長工,象集團規畫師郭中端對宜蘭人的愛鄉印象深刻。
反六輕運動是宜蘭人團結護土最具體的例證。在調查各地區環保運動結構後,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員蕭新煌總結,宜蘭人的反六輕是全國第一次的全縣性運動。後勁、鹿港的環保抗爭是以地區性為主,而宜蘭人卻做到了全縣政府、民眾一體抗爭。
雨的孩子
蘭雨霆窪。從北宜公路下眺蘭陽平原,霧濛一片。一百多年前,傳教士馬偕來到宜蘭,在他的「台灣遙寄」中提到宜蘭,「此地天氣潮溼……不僅使旅人感到不快,且常無法做旅行。」連綿不止的蘭雨的確帶給外地人鬱悶不開的情緒。
然而,蘭雨卻滴答打進宜蘭人的感性中。黃春明曾說過,「別人是太陽的孩子,宜蘭人則是雨的小孩」。對宜蘭人,下雨是如魚得水,既不怕雨淋,也不會跑去躲雨。據統計,宜蘭一年中有二二六個下雨天;發霉的青苔味,遂成宜蘭人淡淡的嗅覺記憶。
阮義忠童年最震撼的印象是,有一年秋天,當他到外面去上廁所,抬頭看天空時,他訝異地自問:「怎麼天空是藍色的?」
有「台灣史懷哲」之稱的陳五福醫師評析,多雨造成宜蘭人自省、內斂的文靜性格。宜蘭人有雨的性格--惜情、浪漫且容易激動,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宜蘭人從事廣告、藝文工作的人特別多,
從宜蘭人對龜山島的依戀,可以看出他們的感性。很少宜蘭人上過龜山島,但是,如久居宜蘭的作家李漳比擬,當宜蘭人坐火車離鄉時,龜山島是送別最遠的親人;遊子還鄉時,它又是第一個迎接的親人。連異鄉人陳才發也感染到宜蘭人的浪漫,每當他從南部老家返回工作地宜蘭時,看到龜山島,竟也有投向母親懷抱的感動。
歷史背景也影響到宜蘭人的性格。從歷史發展的座標看,宜蘭的開發比西部遲了一百五十年。宜蘭的晚開發與其地勢險峻有關,諺語「爬過三貂嶺,忘記厝某子(妻與子)」道出開發宜蘭的辛酸。一七九六年吳沙率一千多流民強渡山嶺來開墾蘭陽,帶給蛤仔難(宜蘭)莫大衝擊,因此游錫 用「拓荒者後裔」來定義宜蘭人。
治台難、治宜蘭更難
吳沙開蘭至今只一九六年,傳宗約僅八、九代,所以宜蘭人多少仍保有祖先闢荒墾地強悍不屈的性格。在清朝,宜蘭人常讓清廷頭痛,因宜蘭多聚匪徒,叛亂頻仍,流傳「治台難,治宜蘭更難」,曾有十五年之久,宜蘭不屬於清朝版圖。噶瑪蘭廳志上記載:「自昔不隸中華,實則日本、荷蘭及鄭氏竊踞所不及之區也。」宜蘭人強悍難管的性格因此可見一斑。
叛逆的血液代代流傳,執著、固執、是非分明的拓荒性格也香火相承下來。再加上宜蘭人大多到外地討生活,更需要拚命鬥爭的性格,否則難以衣錦還鄉。反六輕、重環保,若不是宜蘭人的執著,一切或許歸於烏有。在假日到冬山河撿垃圾的義工王秋薇肯定,宜蘭人對理想很堅持,除非是自己放棄,否則「要污染宜蘭蠻難的。」
自台北返鄉開業的建築師張仲堅描述,宜蘭人不喜歡被高壓統御,愈要他往東,他偏偏不往東,「宜蘭人很九怪(刁),」瘦小的張仲堅戲謔地說。
做飼料生意的陳茂憲體會,宜蘭人很容易相信人,但只要發現被騙,一定反抗得很厲害。民國七十年底,宜蘭人因懷疑前任縣長的操守,難再相信國民黨提名的候選人,逐將所有激憤昇華,傾力支持當時名不見經傳的陳定南。
宜蘭是鄉民社會,多是大家族共居,大半沾親帶故,還保有雞犬相聞的純樸生活。
專注於建立蜜餞形象的橘之鄉董事長林枝漫,住在林家村裡,全村都是林氏宗親,村子各戶都沒有門,大家進進出出,沒有人介意。他笑著回憶,小時候爸爸要打他的時候,他就鑽到別人家,躲去父親的追趕。他弟弟林旺根至今仍住在村子裡,白天上班也不鎖門,任何人只要拉開紗門就可以進去。
拍攝記錄片「月亮的小孩」聞名的吳乙峰,談起在宜蘭的童年,眼睛像玻璃珠一樣地目明亮起來。黃昏時,號角響起,吳家村大大小小到海邊牽罟(拉網)、分魚,「人和人的關係很讓我感動。」談起甜甜的童年記憶,吳乙峰難忍激動的情緒。
正因為人和人之間沒有距離,社會隱秘性低,傳統價值觀的約束力相形增強。宜蘭人在宜蘭不敢做壞事,一旦被查覺,「XXX的兒子做壞事」,風快地傳開。甚至男人去礁溪辦事也提心吊膽,怕碰到熟人誤以為是去「溫泉鄉」。
傳統價值觀的張力,也擴散到男女相處上。結婚幾年後,三十五歲的林旺根,至今走路時也是他走前面,太太走後面,兩人不敢手牽手,怕給村子的人看到會不好意思。
農民性格
從人口組成結構,也可以解構出宜蘭人的部分性格。
宜蘭社會基本上由老一代農民組成,典型農民性格是「見食相呼,闖然入座」的樸質好客精神。宜蘭女婿梁坤華最難忘懷宜蘭人的好客天性,拜拜時把陌生人連請帶拖進家吃,吃完一家又被拉到另一家。畫家吳炫三清楚記得,家裡請客時一定有三十六道菜,小孩子不准和客人同桌吃飯,只能坐「桌仔腳」。
「阮宜蘭人就是沒錢,也會當棉被來請人客。」年過四十的農夫林金風比著手勢說。
從前宜蘭人被喚做「宜蘭番仔」,贛直、草根而又聳(土),「連穿西裝也是聳聳的,」民俗專家邱坤良笑著回想,他們小時候根本沒有現代語彙,到高中之前,他還不知道游泳這兩個字,他們單叫那「到海邊洗渾軀(洗澡)」。
據台大地理系教授張長義分析,農民性格較容易接受好的領導,對是非很堅持。在軍中,宜蘭兵最好帶,會做會吃又好領導。
宜蘭人的善良古意可從一件事看出。羅東運動公園工地裡的「歐吉桑」林福山談起光復後,台灣各地農民報復日本農業指導員的情形,縱使他們再苛刻,宜蘭人最激烈的報復手段也只是把農業指導員按在尿池內,不會傷害他們的身體、性命。「宜蘭人真古意又真能忍耐。」戴一頂工頭帽、退而不休的福山伯說。
生活就是教育,宜蘭性格在生活中一點一滴流進下一代的價值體系中,蘭陽孩子在長輩耳濡目染下,自小即養成勤儉負責的習慣。
長輩們做事時不說話、認真的態度,是子孫的榜樣。林枝漫家族共六十七人,他從小看媽媽每天煮一千多碗飯給全家吃,即使身體不適,她仍把該做的事做好,沒有抱怨、拖延。而小孩也是生產單位,不能閒著;五歲大,家裡就交給林枝漫一條牛看管,六歲時一天要割十八斤草。
「不工作就沒飯吃。」林枝漫相信,今天他會努力打拚事業,與從小養成的工作態度絕對有關。
勤奮觀念也在阮義忠身上形成。小時候村民最討厭的就是懶惰的人,至今他還是認為懶惰就是罪惡。
農業社會就這樣自給自足,自由自在,宜蘭的小孩沒有升學壓力,只要四百多分就可以考進高中。即使讀不好書,家人也不會責備,只要不生病、不花錢,書讀得好不好沒關係。
「風水」特殊
宜蘭多颱風、水災,養成宜蘭人順天的性格。學術交流基金會執行長吳靜吉分析,宜蘭「風水」特別多,要生存就得特別努力,與大自然取得和諧。在財政部次長賴英照的記憶中,他們家屋頂每年照例要被颱風掀走一次,一年家裡的積蓄就全花在這一次修屋頂上。
從小跟著做獸醫的父親深入鄉間,吳乙峰看到因雞瘟傳染,歐吉桑對著辛苦飼養的死雞流淚,歐吉桑並不怪天,只是請媽祖,祈福消災。
從後山到希望之鄉,宜蘭走了好長一段路。住在宜蘭五年的羅東高工教師楊欽年點破,宜蘭能有今天,是宜蘭人有意識地凸顯宜蘭意識。生於宜蘭的張長義也認為,近十年來宜蘭出了好的領導人,宜蘭人也能接受好的領導,領導者有心彰顯宜蘭精神,才是宜蘭受青睞真正的關鍵點。
宜蘭是台灣農村社會的縮影,工商發展,農村解體,宜蘭當然也面臨改變的抉擇。但是,和其他地方相比,宜蘭人或許對家鄉發展的走向更有自覺,正如宜蘭媳婦田秋蓳所說:「宜蘭人更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
以文化、環保、觀光立縣,是宜蘭人共同清晰的大目標。宜蘭人反污染性工業,在別人眼裡看來自然是過於自私,但「如果孩子的志願是唸觀光、文化,為什麼一定要強迫他唸工商?」吳炫三反問。
當北宜快速道路宣布緩建時,曾引起宜蘭人強烈反彈;但這條使宜蘭通向繁榮開發的捷徑,卻有部分希望保留家鄉原貌的宜蘭人未雨綢繆地提出相反見解。
「只要北宜一建,宜蘭三十分鐘內就被台北污染了。」邱水金憂心忡忡地預言。
「我們不希望宜蘭變成第二個三重或桃園,」以畫山岳聞名的藝術工作者李讚成堅定地說,宜蘭精神對台灣社會是一種正面的呼召。
宜蘭人精沖證明的是,只要有心有情,即使在起跑點慢了幾十年,依然可以追上早出發的競賽者。
噶瑪蘭之歌
「我來唸歌囉……阮祖先仔從那裡來、來多久,我也不知影……」七十四歲的陳秋香,抱著自已做的琵琶琴,用「七字仔」唱出從他阿祖到他兒子一百七十多年的家族歷史。
目深、黝黑的陳秋香,是過去宜蘭的主人--噶瑪蘭人。
在漢人屯墾之前,蘭陽平原住著平埔族的一支噶瑪蘭人,有三十六番社。和所有原住民一樣,在漢人移墾後,噶瑪蘭人不是退到後山(花蓮),就是漢化,逐漸消失。至今只有在五結鄉才能找到幾個完整的噶瑪蘭聚落。
冬山河畔的留留社,住有七、八戶人家,全是噶瑪蘭人。七十八高齡的林彭菊在此渡過她的大半生。十六歲時奉父母之命,嫁給留留社的林金發;那時她還不知道,林家有五十口人等著她。
她記得林家飯桶很大,一餐要煮二十五斤米。她每天早上三點,就得起床煮一大家子的早餐。不煮飯的時候,她必須搓草席、編草鞋。
熱情純真的林彭菊喜歡告訴人客,她在冬山河畔丟魚的故事。有一次她奉婆婆之命到河邊殺魚,當她剖完魚肚洗魚時,魚竟神奇地跳進河裡游走了。年輕的她怕回家被公婆打,傷心地在河邊哭起來。「我哭彼尾魚仔哭得真厲害,」談至此,坐在沙發喝紅露酒的丈夫林金發,也快樂得笑起來。
莫可奈何的命運
林家外面種二許多大葉山楠(橄欖樹);去年噶瑪蘭人返鄉尋根,從後山來的兩百多名族人看到林家橄欖樹時,感動得就在樹下跳起舞來。林彭菊就在狹小的家裡忙進忙出,招待久違的族人。
像大多數噶瑪蘭人,育有三子八女的林彭菊也信上帝,她經常用噶瑪蘭文唱平埔調的「上帝創造天和地」給訪客聽。
像她這樣會說母語的噶瑪蘭人已不多見,噶瑪蘭語幾乎已成死語。據統計,現今宜蘭人約有四分之一有噶瑪蘭血統,但願意承認流有平埔仔血液的人卻少之又少。
「阮噶瑪蘭也是人,又不是鬼,」住在加禮遠社的陳秋香對此感觸良多。
從做醫生的阿祖、捕魚的阿公、種田的他,一直唱到他的四子一女,陳秋香的歌裡,縈繞的不只是家族辛酸的過程,更是噶瑪蘭人莫可奈何的歷史命運。
面對歷史文化即將消失的噶瑪蘭人,挾吳沙屯墾成功庇蔭,能哀矜而勿喜的漢人又有多少?
二龍村的龍舟故事
從阡陌遠遠看去,攀在社區大門的是兩條栩栩如生的青龍。二龍河龍一樣蜿蜒繞過,流著游魚,也流過二龍村轟轟烈烈的歷史。
提起划龍船,沒有一個宜蘭人可以漏掉這個礁溪鄉的小社區。以賴姓、林姓宗親組成的二龍村,雖只有一百六十幾戶,卻延續了一百九十五年激烈的龍舟比賽。
七十八歲的賴艷樹,談起划龍船,目光炯炯,彷彿跳進年輕時不服輸的拚鬥往事中。
吳沙開蘭後,他的曾祖父從彰化跑到宜蘭,從此在二龍村落腳生根。上二龍、下二龍村的龍舟賽也就從那時點燃戰火。
百年只停辦一次比賽
「以前比賽真結怨,」五十年前划左舵的賴艷樹,熱心地為外來客解說,上下二龍每年會為這場比賽,鬧得彼此不說話,甚至大打出手。在比賽期間,小孩們儘量繞路走田梗,以免狹路相逢起衝突。
二龍村民堅信,龍船有龍神,如果划輸了,會帶來惡運;為求平安,上下村對比賽都志在必得。三十二歲的林洪蛟嚴肅地說,如果不辦此賽,那一年村子一定會出問題,二龍河也一定會淹死人。至今,只有一年因為在日據時躲警報,被迫停賽。
林洪蛟更言之鑿鑿地指著手說,村裡很多老人都在放龍船的艙屋裡,看過龍神睡覺。
上下二龍各有兩艘船,每年由做頭的人照顧。船下水的前一晚,任何人不得靠近,要等到隔天拜拜謝恩後才可接近。因為有龍神在,所以嚴禁女人靠近龍船;當龍船過橋時,橋上也不可以站人。
比賽時,二龍河岸擠滿圍觀的人群。村人敲鑼表示競渡開始,加油嘶吼聲,喊急寧靜的社區。以前比賽要花六天,現在縮短成一天。比賽時要放水燈,請戲班演平安戲,全村拜拜請客。二龍村一年只在這幾天沸騰。
傳統力量畢竟敵不過都市誘惑,年輕人外流,二龍村龍舟賽再也燒不起過去的火熱;二龍河也從大河淤積成一彎小溪。
「少年仔顧賺錢,誰要睬這個?」曾為龍舟開目的賴艷樹,發亮的雙眼逐漸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