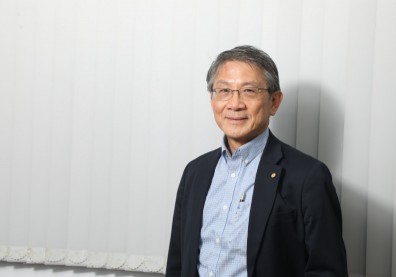以色列是沙漠中的仙人掌,在惡劣的生存條件折磨下,它的刺鋒利剛強;但在剿悍的外殼裡,卻包藏著多汁而柔弱的內在。
為生存而時時備戰,是日常作息的一部分,沒有一個國家像以色列如此警覺;即使在溫暖、燦爛的陽光下,似乎總有不祥的陰影跟隨著。
在耶路撒冷的觀光區裡,青春歡笑聲穿梭著;花樣年華的少女,T恤、布鞋、牛仔褲打扮,身旁摟著情人;卻斜背一隻M16步槍。她們正在服役,槍不離身,睡覺時也一樣。
精神武裝
他們時時聽收音機,就怕最不想聽到的新聞發生。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們的精神武裝。黎賓(Zipporah Liben)太太放棄在美國紐約十四個房間的華廈,回到以色列協助新移入的各地猶太人。「你問我為什麼回來,你應該去問那些留在美國的人為什麼不回來?變的人是他們,不是我。」
一談起讓還占領區(約旦河西岸、迦薩走廊)以換取和平,許多猶太人立刻賁張「仙人掌」之刺。他們說,這都是西方國家坐在沙龍般會議桌邊的遐想,要生要死的,可是遠遠隔著地中海的以色列。
一個三十歲出頭的新聞局官員,激昂地批評,西方國家根本不瞭解專制、反覆無常、封閉的阿拉伯人,尤其是「膚淺的」美國人:「他們總以為全世界的人都跟他們一樣,喜歡蘋果派、媽媽、講笑話;什麼事只要坐下來談,就可以解決。」
有意思的是,隨便問一個猶太人,他絕對不會用「共識強」、「步伐一致」來形容自己的社會。相反的,十之八九聽到的回答是--「分歧」。在以色列航空工業公司(IAI)工作三十年的高級主管說:「在這裡,我們絕對不會為了生活枯燥而自殺,因為意見太多了。」
這是一個真正的純移民社會,在面積不到台灣三分之二的地方,除了巴勒斯坦人之外,還湧進來自七十多個不同國家的猶太人(包括長相一如黑人的衣索匹亞猶太人),所講的母語超過一百種。
活得尊嚴而清楚
生活背景不同,宗教派中有派,政治主張更是從左到右。乍看之下,這些變數似乎要把以色列切得粉碎。這是以色列柔弱、拿不出辦法的一面。
他們花了二十年,爭論能不能在聖城蓋游泳池;國會議員捲起舌花,激辯誰是「猶太人」;各派宗教熱列生商討,該不該依聖經所示,全國農地每七年休耕一次……。
當然,最能引起口沫橫飛、臉紅脖子粗的場面,是怎麼得到和平,怎麼解決巴勒斯坦問題。
有些人認為猶太人與眾不同(因為他們是上帝的「選民」);而阿拉伯人又與別的民族不同,難以捉摸。「六日戰爭」後的民意調查顯示,八成以上的猶太人相信,「所有的河拉伯人都憎恨猶太人」。
另外一種看法,是巴勒斯坦人跟猶太人沒有兩漾,大家都是期望和平的。
離開爭鬧不休的耶路撒冷,沿著公路穿越約旦河西岸,走上戈蘭高地,暮色漸沈,車聲寂寂。在加利利海邊,令人想起講愛與寬容的耶穌,空氣中一如教堂的肅穆。一轉頭,戴著麥卡瓦坦克的運輸車,刷地一聲經過。
卡發布隆農場(Kfar Blum)就在戈蘭高地下面,矮胖的可登(Judith Criden)快步走在農莊的小徑上,皺著眉頭,說出最令她憂心的危機。「現在大家漸漸覺得,我們比巴勒斯坦人優秀,我們的宗教、生活方式都好過他們,以前不是這樣的。」
跟台灣一樣吵吵鬧鬧,但以色列人似乎活得更有尊嚴;跟台灣一樣面對一個不可知未來,但以色列更清楚自己該做什麼。
第一次就做對
翻閱報紙,有種族衝突,卻沒有拿槍殺人搶劫;有致見的辯論,卻少見權術遊戲;他們世討論國防預算削減,卻從沒聽人談起官員貪污、腐化。
以色列人的生活過得比台灣窮,(一位從英國移入的老人說,他發現自己比以前少吃肉了,要省著點用);但他們沒有坑坑洞洞的馬路,更不會看見被丟棄的塑膠袋隨風飛揚。以色列表現出來的決心,不過是簡單的道理,資源有限,機會、時間更有限,他們第一次就要做對,不允許失敗。
是一種融合歷史傳統、教育、服役制度的力量,把猶太人緊緊黏在一起。這種強力膠,使他們打贏五次大戰,忍受百分之一千的通貨膨脹(一九八四年),和長年一0%以上的失業率。
星期五下午,以色列的馬路邊常當可以看到想搭順風車回家的軍人。戴著軟帽,袖子捲起,敞開領口扣子,這是善戰聞名的以色列士兵的典型模樣。其實,在餐廳、在學校、在馬路上的猶太人,即便穿便服,有各種職業,但內心的軍人本色,是這個社會的基調。
心理學家蓋爾(Reuven Gal)回憶,六日戰爭時,他報到的戰場,離家只有兩英哩。戍守在小山丘上,他只要一回頭,就可以看到他的家,當時,他太太正懷著身孕。
「活在以色列很難,不死在以色列也難。」蓋爾現在主持一個專門研究軍人心理的機構,他說,這種心情,他的父親經歷過,他的兒子如今也是,三代之間因此有共同的信念。
三歲開始教育
蓋爾的故事,在這個受過連串征伐洗禮的國家裡,不是特例。透過戰事表達求生的意志,不僅凝聚了幾代人的力量,連帶也使社會減少階級意識。
上至部長,下至洗衣機技工,除了十八歲服役三年(女人兩年),每年還有平均四十天左右的後備役。「在這裡,教授最要好的朋友,可能是公車司機。」曾做過記者,現在是自由作家的哈達里(Amton Hedary)說。
兩(三)年的軍事洗禮,年輕人普遍認為,最大的收穫是成熟了(而不是變成老油條、煙槍、嗜酒者)。
跟大部分青年一樣,蓄著絡腮鬍的納達利(Aharon M. Naftali)服完年期較長的軍官役,順著時尚出國遊歷一年,理工學院工業工程管理系唸到三年級時,已經三十歲了。他是備役上尉,服役時,他跟一個軍官掌管一艘價值三百萬美金的潛水艇。
他回想,當年他不遇二十出頭,就領著十幾個弟兄出海潛航,在高度授權下負起重責。一夜之間,他不得不快點長大。納達利對著身邊那個一切以事業至上的同學說:「等你服完兵役,就會明自國家才是最重要的。」
國家意識的灌輸,不只限於成年後的軍事磨鍊;而是從小的教育,就不斷融入傳統、歷史和團隊精神。
猶太人對子女教育的要求,絕不輸給中國父母。即使在中世紀,猶太社區裡沒有一個男孩子不上學,家裡付不出束脩,社區必須負擔費用。
這種傳統在建國時,由第一任教育部長(以色列第二任總統)進一步發揚。他上任當天,就叫祕書拿著破打字機,草擬教育法,強迫三歲到十五歲的新生代,接受免費教育。他的秘書驚愕不已,經費拮据不提,當時整個教育部,就只有他們兩個人。
這套義務教育法,第二年就通過了,比中華民國整整早十年。
以色列對知識的尊重,也不僅是嘴巴說說而已,連建築也表露無遺。以色列的外交部,是接收英軍當年的營房改建的,牆上看得到裂縫。由於經費有限,整個亞洲司也只有兩個人。
離外交部不到半小時車程的希伯來大學,絕對看不出一點寒酸相。一個研究中心主任兼教授,不但有自己的辦公室,門口還坐著一個秘書。
由歷史統治
一株株幼苗就在這種氣氛成長。小學生二年級開始學猶太聖經(阿拉伯人唸可蘭經),三年級再加本國地理。
「我們是用腳認識以色列的。」希伯來大學社會及教育教授文德勒(Chaim Adler)指出,地理課上課的重心是遠足。
這種徒步健行、露營的活動持續到高中,他們踏遍南部沙漠,繞耶路撒冷一圈又一圈,到北方邊境看約旦河及河對面的敵境。
參觀博物館,也是不可或缺的。當法國小孩躺在羅浮宮裡,看裸體的維納斯;美國小孩尖叫著跑在迪斯奈樂園時;這裡的孩子,看的是耶路撒冷歷史博物館,想像三千年前聖殿被羅馬人毀掉的悲愁;當然還有紀錄二次世界大戰,猶太人被屠殺的博物館,煤氣、骷髏、希特勒……。
於是,「這裡是全世界我們可以自衛的地方。」「這塊土地是我們的,我們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去了。」這幾句話,變成了老老少少不能挑戰的真理。
「這是一個由歷史統治的國家。」駐以色列兩年後,美國科學箴言報資深記者莫斐(George D. Moffett)觀察,以色列處處提醒人民,記取歷史教訓。
陰雨後、陽光乍現。衛蓋體育學院(Wingate Institute),是屬於肌肉與汗水的。但就在一片綠柔柔的草地旁,豎著一個紀念碑,為的是十幾年前在西德慕尼黑被殺的奧運選手。
「大家時時提起他們,就好像昨天才發生一樣。」衛蓋學院的副主任謝門(Atara Sherman)傷感地說。
而十歲的少年,幾乎都會參加「青年運動」(Youth Movement,類似童子軍的活動),整個社會都以自己家少男少女穿上象徵會員的藍色制服為榮。
這些小「運動者」,也必定會到集體農場(Kibbutz),體驗建國精神。
從小坡上回望卡發布隆農場,田園井然有序。老農何佛(Sam Halpher)追憶,這裡原是水窪地,長不出什麼作物,倒是百病叢生;從蘇俄、東歐大量湧入的移民,三個人之中注定要死一個。
跟建國者一樣,這些移民深受上半個世紀社會主義理想的呼喚,加上屯墾衛國的軍事需要,他們過集體生活,幾百人一起種田,一起吃飯,沒有薪水,就像台灣小學教科書上形容的人民公社。不同的是,這個人民公社,至今仍是民主以色列的精神堡壘。
從本古里昂、梅爾夫人、以色列第一號情報頭子到許多優秀的空軍飛行員,都出身集體農場。雖然,目前兩百三十多個農場,共負債十億美金,但卡發布隆的老農何佛堅信,集體農場會變,卻絕不可能消失。
它不會消失,因為在以色列沒有軍隊,沒有工業,沒有政府之前,農場是唯一也是最重要的生存命脈,這片與大自然搏鬥的田地上,留著猶太人今天的性格--再困難的環境,也只有勇往直前;個人的享樂次於團體的生存。
憑著這股氣勢,以色列數度贏得關鍵戰爭;但猶太人剽悍的作風,似乎也難抵擋巴勒斯坦問題的撕裂。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九日,一個猶太人到西岸巴勒斯坦人開的商店買東西,不料突然頸後被插一刀,當場斃命。雙方互以流血報復,對峙升高,接著巴勒斯坦人罷市、罷課、示威、丟石頭、開始為求建國的長期抗爭。猶太人軍隊也以牙還牙,各有死傷。
這就是intifada。
軍中開始有不同的聲音,已經有六十多件拒絕到西岸服役的案子。在耶路撒冷回教金頂寺遇到一位守寺衛兵。正想興奮地展示他的中國功夫,一聽到「是否願意受命到西岸」的問題,立刻變臉說:「我很滿意現狀,我不想改變。」他們寧願和武裝的敵人正規軍作戰,但要在占領區對付街頭向他們辱罵、丟石頭的巴勒斯坦平民,卻完全是兩回事。
讓路給貨櫃輪
宗教的力量,更在中間扮演舉足輕重的地位。現在第一、二大的自由黨(Likud)和勞工黨(Labour),都未贏得國會多數席次,因此宗教小黨派的意見,變成左右政策的關鍵。
以色列的主流教派,是正教(Orthordox),占人口的三成,他們大多數不但堅持女人手肘不應外露;更相信約旦河西岸和邇薩走廊占領區都是聖經裡上帝「應許之地」的範圍,絕對不能讓給巴勒斯坦人,否則便違背了上帝意旨,以色列人將被懲罰。
一個宗教領袖把宗教形容為充滿五千年傳統寶藏的貨櫃輪;而只有四十年歷史的政黨,不過是艘空船,在海上行駛,兩船相遇,「空船當然要讓路給貨櫃輪。」
就算贊成跟巴勒斯坦人談判的人,也派中有派;有人贊成跟PLO(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談,有人反對。「絕不,絕不跟那些恐怖分了談判。」一位四十多歲的家庭主婦說。
沈的不信任感。在「六日戰爭」裡,有些家庭已經挖好墳墓,深恐大屠殺再度來臨。
而溫和的人則說:「巴勒斯坦人最後還是會建國的,讓我們談吧,不要再殺戮了。」他們希望的,也是歷史悲劇不要重演。
一八九七年,一心鼓吹猶太人不要再等救世主,要自力建國的赫宙(Theodore Herzl),在巴塞爾(Basle)召開第一次猶太人建國大會,他說:「我在這裡宣布猶太人建國,你們一定要笑我;但我相信以色列在五年內有機會復國,五十年內心定建國。」
果然,以色列在五十年後建國,成千上萬的猶太人回到上帝與他們約定的土地。
如今,建國的榮耀、驕傲與自信,就在種種矛盾中褪色了,猶太人建國了,但他們到底要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呢?
三月開始,以色列又將有個無雨、永遠陽光普照的長夏。這些惱人的結,就像日日東升的太陽或猶太人周而復始的安息日一樣,看不到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