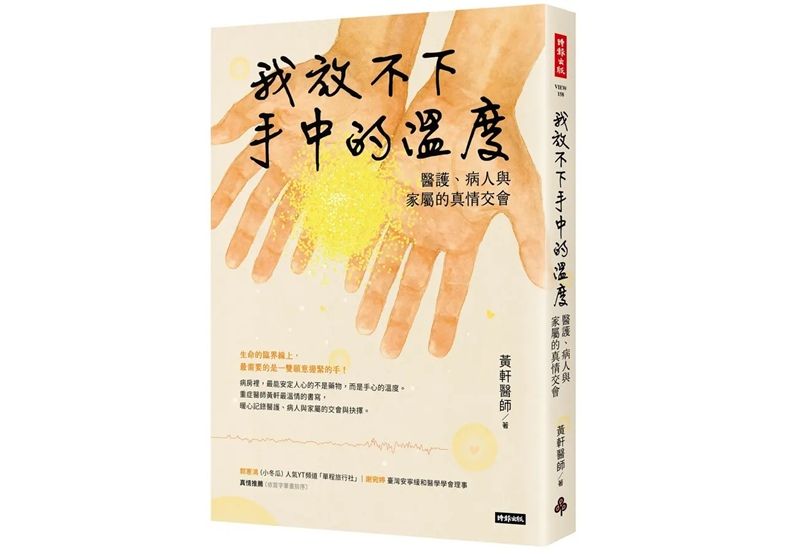那天,我再次被一個病人的決定深深觸動。他叫阿哲,一個清醒、理智、卻也無比堅定的人。當他平靜地對我說:「請讓我好好離開。」那一刻,我知道他早已想清楚了。身為醫生,我的職責是救人,但我也清楚——不是每一條生命都該被強行挽回。醫療不只是延長呼吸的長度,更是讓生命能有尊嚴地落幕。(本文節錄自《我放不下手中的溫度》一書,作者:黃軒,時報出版,以下為摘文。)
診間的陰影
我的診間裡,氣氛沉重而靜謐。窗外的陽光透過百葉窗,投射在淡藍色的牆壁上,映照出斑駁的光影。阿哲,一名23歲的年輕男子,坐在診桌前,穿著休閒的T恤和牛仔褲,神色看似輕鬆,但他的手卻無意識地緊抓著椅子扶手,彷彿在尋求某種支撐。
我低頭看著X光片,眉頭微微蹙起。腫瘤的陰影清晰可見,就貼在縱膈腔上,像一個不速之客,悄悄地侵入這個年輕人的生命。
「阿哲,你最近有沒有覺得夜間盜汗、體重減輕?」我的聲音平穩,但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沉重。
「有吧……最近比較累,體重掉了幾公斤,還以為是壓力大。」
阿哲的語氣輕描淡寫,試圖掩飾內心的不安。
我深吸一口氣,闔上病例說:「我們需要進一步檢查,我懷疑可能是淋巴瘤。」
阿哲楞了一下,露出一抹輕笑:「醫生,應該不會吧?我才23歲耶……」
「年齡不是問題,現在最重要的是確診。」我的眼神堅定,沒有迴避。
三天後,切片報告出來了——淋巴癌。
阿哲被轉到血液腫瘤科治療,病情在幾次化療後曾一度好轉,但只是短暫的勝利,半年後,癌細胞復發,病情惡化。
病房裡,阿哲照樣和護理人員有說有笑,但當夜晚降臨,他一個人靜靜坐在窗前,看著夜空沉思。
那天夜診結束後,我在醫院地下室的長椅上看到他——他低著頭,帽子壓得很低,當我走近時,他抬頭,眼淚瞬間落下,在黑暗的地板上不著痕跡地消失。
「怎麼了?」我輕聲問道。
阿哲抿著嘴,嗓音顫抖:「病情變糟了……今天看到媽媽在病房裡偷偷哭,我……不知道怎麼辦。」他仰起頭,深吸一口氣:「我一直說很快就會好……但我知道自己快不行了,可是我一定崩潰……」
我沉默良久,輕拍他的肩膀:「阿哲,我來幫你。」
我決定召開住院全人整合醫療會議——不只是針對病情,更是為了讓這個家庭,能夠在真正的「生死溝通平台」上,坦然面對即將到來的結局。
這不是普通的病患會診,而是一次完整的「跨科整合醫療會議」——血液腫瘤科、重症醫學科、呼吸治療科、安寧緩和科、營養師、藥師、社工師、專科護理師,全部聚集在同一個會議室。
阿哲的母親也來了,坐在會議桌前,雙手不安地繞著手帕,眼神閃爍,彷彿害怕聽見某個殘酷的事實。
當醫療團隊開始分析阿哲的病情時,他卻忽然舉起手,語氣堅定:
「我有一個要求,請安排讓我好好離開。」
現場瞬間安靜,只有心電監測器的滴滴聲在背景響起。
安寧緩和醫師輕聲開口:「你願意選擇安寧照護嗎?」
「是。」阿哲點頭,「我不要最後的急救,我不要插管,不要讓自己在痛苦和電擊中離開……」
他的母親驚恐地睜大眼睛,聲音顫抖:「阿哲,你怎麼這樣,媽媽還在啊!」
阿哲低下頭,拳頭緊握:「媽,這是我最後的請求……妳願意讓我選擇嗎?」
整個房間的氣氛沉重到讓人無法呼吸,這不只是一場會議,更是一場生死的對話,一場親情的掙扎。
最終,母親流淚點頭。
後來阿哲躺在病床上,透過窗戶看著夕陽,母親坐在床邊,緊握著他的手,沒有再哭了,只是靜靜地陪伴著他。
「媽,我這一生最遺憾的就是不能陪妳更久。」阿哲的聲音微弱,但充滿了深情。
「傻孩子,媽媽最遺憾的是不能讓你活下去……」母親的聲音哽咽,但她努力保持平靜。
他微微一笑,視線逐漸模糊,聲音輕得像一陣微風:「我好累……可以睡了嗎?」
母親紅著眼,點了點頭。
他終於閉上眼睛,在睡夢中安靜地離開。
(延伸閱讀│「可以告訴我還剩多少時間能完成心願嗎?」從容離世前的3個準備)
隔天早上,我推開病房的門,卻只見一張白色的病床,已經空無一人。
「醫師,你來看阿哲嗎?」護理師輕聲說:「他昨晚在睡夢中往生了……對了,他留了一本書給你。」
我低頭,那是我之前寫的書《生命在呼吸之間》,我打開書,裡面夾著一張便條紙,只有簡單的一句話——「黃醫師,記得幫我簽名喔!」
我的手微微顫抖,因為這是答應過的事,但我竟然忘記了!
簽下自己的名字時,我發現這是人生中最沉重的一筆簽名。
護理師輕聲說:「他媽媽來電,說正往花蓮路上,因為阿哲捐出了大體。」
我深吸一口氣,抬頭望向窗外。太陽緩緩升起,一切都還在繼續。
我喜歡站在長廊上,靜靜地望著病房的燈光,並在內心對阿哲說:「謝謝你,讓我見證了一場真正的『好好死亡』。」這一天,我更堅信——醫療不只是治療疾病,更是幫助病人選擇自己想要的結局。
醫者筆記
那天,我再次被一個病人的決定深深觸動。他叫阿哲,一個清醒、理智、卻也無比堅定的人。當他平靜地對我說:「請讓我好好離開。」那一刻,我知道他早已想清楚了。
身為醫生,我的職責是救人,但我也清楚——不是每一條生命都該被強行挽回。醫療不只是延長呼吸的長度,更是讓生命能有尊嚴地落幕。
「我的死亡,誰來作主?」這句話在我腦中揮之不去。這不只是阿哲的疑問,而是每個人都終將面對的課題。
阿哲走得很平靜,沒有痛苦,沒有掙扎,只有一種近乎莊嚴的寧靜。在他的病歷最後一頁,我寫下:「病人依自主意願拒絕急救,安詳離世。」那一刻,我心裡湧上一種奇怪的感動——那不是失落,而是釋然。
我對他說:「謝謝你,讓我見證了一場真正的『好好死亡』。」他讓我明白,死亡不是失敗,而是一種選擇。醫療的極限,不代表醫者的無能;相反,那是生命教會我們的謙卑。
醫生的角色不只是治療疾病,而是陪著病人走完最後一程。每一場離別,對我們而言,都是一次成長。我在一次又一次的生死交界中學會溫柔,也學會尊重——尊重病人的選擇,尊重家屬的愛,尊重生命自然的節奏。
(延伸閱讀│病人自主權利與預立醫療決定:簽下一個名字,把分離的遺憾變圓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