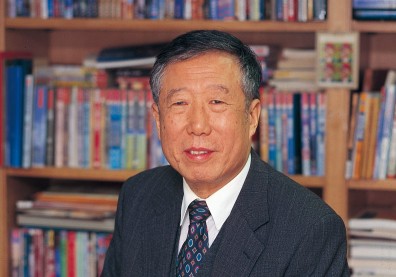2025年7月12日,星期六,上午9時,親友們聚集在台北市新生南路天主教聖家堂,送彭歌遠行。他早在1958年7月30日就皈依天主,聖名依納爵(Ignatius)。他於7月1日辭世,享壽100歲。
彭歌是作家姚朋的筆名,但是他的文名太盛,一般人多記得彭歌,知道姚朋的人反而比較少了。
教堂裡莊嚴肅穆。神職人員主持了宗教儀式之後,親友們個別行禮。我坐在輪椅上鞠了三個躬。想到與他的多年交往,想到從此永別,不禁淚潸潸下。
我和彭歌第一次見面可是久遠以前的事了。1954年我從政工幹部學校第三期新聞系結業,派到《新生報》實習,實習一個月結束,報館指派當時第一版主編姚朋給我們講話,做一些講評和勉勵。姚朋就是後來更為人所知的彭歌。
1960年我又到政治大學新聞系讀書,知道彭歌早在政大新聞研究所取得碩士學位。我高攀,可稱他「學長」。他在美國伊利諾大學也讀了一個新聞碩士。他這一生,從學校到報館,一直浸淫在新聞學術和新聞事業中。但他本質上是一位作家,文學才是他生命的依歸。我曾做一統計,他生平寫小說、散文、評論和傳記的作品,集結成書,一共出了83本書,說他「著作等身」,一點也不為過。不僅創作,彭歌也是翻譯能手,他翻譯的《天地一沙鷗》,是當年非常暢銷的暢銷書。那天陪我去教堂的是《聯合報》同事沈珮君,她在彰化讀中學時買了《天地一沙鷗》這本書,一直念念不忘。

文壇一輪明月,長照人間
作為一位作家,彭歌自然會參加有關文學問題的討論。1977年4月開始,文學界關於台灣文學的寫作方向和路線問題有所探討。有人把討論當前台灣社會現實問題的文章稱為「鄉土文學」,有人則指出這樣的文字「氣度不夠恢弘活潑」。8月,姚朋在聯合副刊發表「不談人性,何有文學?」連載三天,後被稱為「鄉土文學論戰」。
1960年彭歌去美國留學,回國後升任《新生報》總編輯兼副社長。1968年開始在聯合副刊寫「三三草」專欄,每週一篇,非常受到讀者的注意。
1972年彭歌調《中央日報》服務,從總主筆做到社長兼發行人。1986年底,在美國的許信良從桃園機場闖關回國,鬧成一個「事件」。黨營的《中央日報》被認為新聞處理不當,社長姚朋被調任《香港時報》董事長,他在任內退休。
彭歌「無官一身輕」,我們見面的機會多了些。他常來中壢看我,我們在附近小餐館午餐,喝咖啡。我們談到年輕時共同看過的書,於是買了張恨水的《啼笑因緣》和《金粉世家》來「重溫舊夢」。
彭歌走了,想起他的著名作品之一《落月》。他自己是文壇一輪明月,長照人間,不會從讀者的心中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