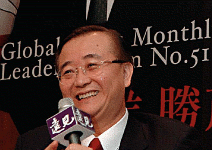其實我進入衛生署,完全都不在我的生涯規劃裡。念台大醫學院時,我只想要當一個很會開刀的外科醫生,又有人說我很會耍嘴皮子,應該當個教育家,我又去學教育。
當署長後我認為我應該要扮演一個領導者,而不是管理者。管理就是一直跟別人說什麼可以做,什麼不能做,但領導者應該要說出一個道理,讓大家來配合。我的願景可以分成四大塊,提升全民健康、健康人生的教育,參與國際衛生組織,並建立一個健康安全的台灣。
我也把扶植醫學生技產業當成我的願景。但是檢討醫療業這幾年對台灣的貢獻卻不高,2005年的「兩兆雙星」,半導體產能已達1兆1131億元、TFT-LCD(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則有9761億元。但「雙星」之一的生物技術——與醫療產業最為相關的,僅產出1585億元。想當初考大學時,醫學院分數比理工科還高,而現在產值卻只是半導體業的尾數,這值得我們深思。
善用優勢/走快不需闖紅燈
為何健康生技產業無法超越?有幾個限制。首先,生技產業必定是個知識經濟,才能有足夠的規模創新。台灣研發的經費比例雖然高,但總數卻比不上一個歐美的藥廠。
另外,價值鏈必須能夠延長,才能建立獲利模式,但新產品卻受到執照限制,以及價格規範。
其中,衛生署所能做的,是法令鬆綁和加速流程。最近推動的就是加速第一級醫療器材的查驗登記,15分鐘就可以發照。這和走路一樣,可以快,但不需要闖紅燈。
政府也有「生技製藥國家型科技計畫」,要振興生技產業,最重要的是要邁向世界性的分工。
很多世界級的藥廠,規模之大,台灣已經追不上了,必須想辦法找到機會點。比如,當研發出一個新產品時,如果只在台灣進行臨床試驗,沒有人會承認;但若賣給美國藥廠,並要求進行全球性的臨床試驗時,台灣一定要參與,才有可能邁向國際。
台灣的強項在哪裡?就臨床試驗來看,比台灣人口多的國家很多,但人權和品質則是我們的優勢。新加坡和香港的語言和政府單位比我們靈活,但人口少,蒐集資料就會比較慢。
建置平台/把資訊還給民眾
以前我在台大看診時,病患從榮總轉過來,病歷很複雜,台大也不一定相信榮總來的資料,反之亦然。中間產生了很多重複看診、資源的浪費,因此醫療資訊溝通平台一定要建置,把錢和時間還給病患,讓人民可以自己帶著資訊,到哪裡都能看病。
這個目標達成後,預期將減少重複檢驗的浪費,至少減少3%的醫療費用支出。
現在99%的台灣人手裡都有一張個人專屬的病歷卡——健保卡,全世界只有台灣做到。未來我希望推動台灣成為生技大國,健保就是個很大的資料庫,特別是用於防疫。例如我可以立刻調出在過去一個月內到東南亞的人數數據,給地方政府注意。但到目前為止,這些資料並沒有被產業界充分利用,像是服用高血壓藥物的人口數等。資料是有的,鼓勵大家利用。
政府機關也可以很親民,過去是「但求無過」,現在要主動思考如何「圖利」國民。也就是在(law)和愛(love)間求取平衡,政府不能違法,但必須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盡量為人民考量,那就是愛的表現。
以愛之名/認錯才能進步
在醫療失誤上,對很多人來說,發生一次都嫌太多。為了加強醫療安全,我要介紹三本書:第一本是《犯錯是人性》(To err is human),是1999年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醫學研究所的報告,文中指出美國每年因醫療疏失死亡的人數最高達9萬8000人,相對於同年國民主要死因中排名第八,遠高於因交通事故、乳癌及愛滋死亡的人數。
為了具體改善,同樣單位2001年又推出另一本書《跨越品質的鴻溝》(Crossing the quality chasm),其中提出六個方法,如以病人為中心、平等就醫等,但最重要的是,品質首重安全,而品質的提升,就要靠教育。
到了2003年又再發行《健康職業教育》(Health professions education),專業的教育就是把醫療提升到知識經濟的層級。
對我來說,醫療首重不傷害,一個真正的好老師是要教學生陷阱會在哪裡,書上只會告訴你如何開好刀,不會告訴你哪裡有陷阱。所以我持續推動醫院落實「手術前標示」,在開刀前畫個記號,等於向病患承諾手術將會開在哪、開多大的口徑等,可說是一個「愛的標示」。
加速聯結/謀定才動就死定
現在是資訊網路時代,每天都以10倍音速在改變,以往我們說「謀定而後動」,但現在是謀定就死定了。
即使是公部門也是這樣,以為每天都看最新的雜誌,就以為自己跟上時代,其實那只是「現在的假象」,這是非常殘酷的事情。沒有一個行業可以一直保持優勢,只有靠自己不斷進步。
但若要和別人做聯接,前提就是要培養無形資產。知識必須夠強、資訊觸角也要夠廣;公正、美德更必須被強調,因為建立信用後,人家才願意跟你連結。
在公共事務也要懂得聯結,我就很鼓勵衛生署同仁盡量和各部門發生關係。台灣有很多土地被污染了,作物當然也會受到影響,不能等食品送入消費者嘴後,衛生署才有所行動,所以我要求衛生署和環保署、農委會要發生關係。行動要一致,才不會把事情推來推去。
除了聯結之外,對內也要有所要求。我最近問衛生署醫院管理委員會執行長林水龍,問他說,有沒有什麼妙方可以改進署立醫院?他提出一個結論,就是「自己的醫院自己救」。所以,自己的工作要自己做,儘管台灣不是WHO的會員,但在防疫工作上也要有自保的能力,像是疫苗的自製能力,以及足夠的儲備劑量。
我是個外科醫生,外科醫生壞處是頭腦很簡單,一刀切下去就是兩半;但我也有內科醫生的性格,我也願意和人好好溝通。我很懷念以前能夠開刀的日子,在辦公室裡就放了一張我穿綠色開刀服的照片,每天看公文的閒暇,就看看照片,過過乾癮。
對我來說,我的人生哲學就是要去追求我能服務的人,最大的快樂與幸福,不管是病人、是藥界、署內同仁,還是全國國民,與各位分享。
現場問答
問:如何鼓勵國際藥廠以及廠商來台灣做臨床試驗?
答:和很多人的觀念不同,我認為能做臨床試驗不一定只能是大學教授。這應該是個資格認定,就像開飛機一樣,如果你很認真地完全依照標準完成,也能夠駕駛。放寬的原因也和我對醫院的政策有關,我認為台灣的大醫院太多,動輒就號稱醫學中心。未來真正國家級的醫學中心要比的是研究創新,和國際級服務的能力。比研發,讓台灣能有更多參與世界性臨床試驗的機會;比國際級服務,要對台灣外交有實質幫助,要想加入WHO,就必須將服務提升到國際標準。未來我會利用這種柔性標準、評鑑,來促進醫院達到這樣的目標。(洪綾襄整理)
侯勝茂小檔案
現職 :行政院衛生署署長
學歷 :台灣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衛碩士
經歷 :美國杜克大學研究員、台大醫院副院長、行政院衛生署副署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