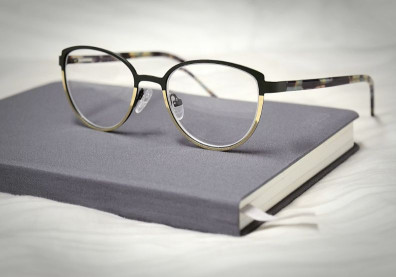對於無緣習佛的人,「生」和「死」是絕對的兩極,「生」是喜悅,「死」是哀傷;「生」是希望,「死」是絕望。看看醫院中,產房傳出嬰兒的第一聲啼哭,大家會向家屬道聲恭喜;病房傳來病人的死訊,朋友會安慰家屬節哀。
對於深諳佛法的人,「生」和「死」是連續的、循環的,是大自然的法則。因此,生不足喜,死不足憂。
印順導師一生多病,生病對他是生命的常態,他還自諛,「一點小小因緣,也會死去的」,然而在他的自傳《平凡的一生》中,他對生死卻有不凡的看法,「於法於人而沒有什麼用處,生存也未必是可樂的;死亡,如一位不太熟識的朋友,他來了,當然不會歡迎,但是也不用討厭。」
他更用做生意來比喻生死循環,「一年結束,一年開始」「年年如此,並不是結帳就完結」。
最近讀到王端正的新書《生命的承諾》,更體會佛家對生死另有一番詮釋。
王端正原是一位傑出的新聞人,他當過《中央日報》的總編輯,對這個社會有敏銳的觀察,這本《生命的承諾》就是他潛佛中對「生命」做了深刻的澈悟。他談的「生命」,是包括了:生命的法則、生存的意義和生活的價值。不僅如此,他還從個人的「生」推展到社會、國家的「生」。
生命中的緣起緣滅、變化無常固然重要,人的生存應該有什麼樣的意義?人究竟該過什麼樣的生活?恐怕是一個更值得深掘的本源。
《生命的承諾》一書中,作者對「取與捨」、對「天安」、對「未來」、對「承諾」等等的看法,讀來令人感慨:
——要看一個人的生活品味,就看他對食、衣、住、行、育樂的取捨;要看一個人的道德高低,就看他對仁與不仁、義與不義、廉與不廉、苛與不苛的取捨。
——天安不如國安,國安不如民安,民安不如心安。
——不要做個執著過去的痴人,不要做個坐等未來的愚人;把握能抓住的現在,我們就是智人。
——多愁善感是生命的浪費與精神的消耗,具慈悲與智慧的人都不會在感懷中蹉跎一生。
——小女孩背弟弟,不覺得重,因為她背的是愛;愛沒有重量,愛不是負擔。
在這個社會價值混亂、是非錯置的年代,人對自己的生命能許下什麼樣的承諾?人對自己的生存能總結什麼樣的意義?是不是如印順導師所說,「於法於人沒有什麼用處,生存也未必是可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