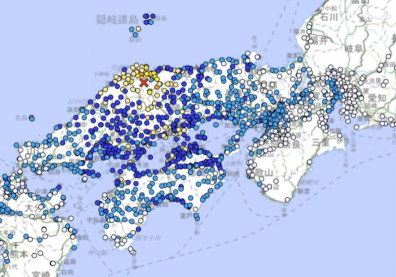光纖已存在二十餘年,以往因為技術不成熟,應用不廣,再加上生活中也無此需求,所以此行業並不熱門。然而近幾年來,由於網際網路的資料傳輸太多,傳輸管道必須一再加寬,所以被稱為「頭等艙」的光纖就成為資訊高速公路的最佳選擇。有了光纖,在電腦上聽歌、看電影之類的多媒體服務才可能實現。
光纖就和交通要道一樣,有長程網路(long haul,如跨海、跨國的),有都會網路(metro network,跨城市的)及企業網路,前兩者屬於公用幹線,後者為私有。長、短幹線之間要互相溝通無誤,需要許多技術及產品,光纖本身傳送速度的加快、加強,又有許多技術及產品,這些加起來,就形成光纖的龐大市場。
新一波的投資狂潮
這個市場到底多大?每家光纖公司都會拿出一大堆數字來證明它的高速成長。如果你不愛看數字,那麼只要想像:每個人都喜歡直接或間接使用光纖——就像每個人都喜歡直接或間接乘坐子彈列車到達目的地一樣。所以只要維持住這個美麗的遠景,那麼就可以讓各式各樣的光纖業者忙個好幾年了。
根據資料,美國創投業今年上半年已在舊金山灣區投入七億九千四百五十萬美元,共浥注了六十五家光纖有關的公司,而去年全年才投入六億八百一十一萬美元,浥注八十六家公司,面對這新一波投資狂潮,連創投業的人自己都說,「太過份了。」
許多光纖公司還在大賠特賠,就已隆重上市,股票還飛漲,這和一年多前的網路泡沬幾乎如出一轍,難道不怕歷史重演嗎 ?當然很可能,可是光纖比網際網路扎實,再怎麼樣,它都是真材實料,和網際網路的虛擬性比起來,它可算是「傳統行業」了。
不過話說回來,網路股破滅的原因,說穿了就是「華爾街的說法改變」,以前說可行的,現在說不可行,所以大家對網路股就沒興趣了。現在大家都說光纖有潛力,所以它就變得十分有潛力。
無論如何,這就是高科技的高風險,因為怕風險而不在當紅產業中一搏身手,那裡算矽谷的英雄好漢?下面是矽谷一些有關華人的光纖故事:
華人創投業者一樣熱衷光纖。VenGlobal今年已投入五千萬美元,分在四家公司內,三家在矽谷 ,一家在台灣,其中三家做元件,一家做系統 。五千萬美元還是早期投資,「今年底我們會再加碼,」VenGlobal Capital General Partner負責人程有威說。
對於光纖業的投資熱,程有威有同感。他說,「的確有人亂投,有些公司也不該上市。」然而精蕪夾雜,本來就是產業熱中不可避免的現象,創投業者置身其中,只能睜大眼睛看,並且認知它的風險。「將來每一種產業區隔中,必然只有前三名可以存活,」程有威表示,在出現「前三大」之前,必然有些公司會消失,有些會和其他公司合併。
光纖為何會熱門呢?程有威說 ,一來是華爾街支持,二來是需求真的存在。關於前者,今年九月份《紅魚》雜誌(Red Herring)報導如下:在四月股災後,光纖股反彈力量比那斯達克指數高,甚至七月份的股值還比三月高峰期 高 。
著名的光纖股及它們的那斯達克代號如下:Nortel Networks(NT),JDS Uniphase(JDSU), Corning(紐約指數GLW),Ciena(CIEN),Sycamore Networks(SCMR),Juniper Networks(JNPR)。關於需求問題,一般老百姓或許不覺得迫切(有多少人會說,我真的需要一條光纖),真正感到需求的 ,是想提供光纖服務的大公司,如長途電話公司或電訊設備公司。
「以AT&T(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為例,長途電話一直在降價,所以他們必須提供加值服務,即可傳送多種媒體的服務,要達此目的,只有利用寬頻——即光纖,」程有威表示。大公司要建光纖網路 ,需要各式各樣的零件來使光纖發生功效 ,而目前這種零件大缺貨,所以造成光纖創業熱潮。有的公司甚至說,產品還沒做出來都可把公司賣掉。
換言之,光纖是大規模的基礎建設,這個大建設有如一個帶動經濟的火車頭,使相關行業跟著蓬勃。據估計,需要光纖零件的火車頭在美國大約有一千五百家,這包括六、七家長途電話公司,數家大型設備公司,數十家中型電話公司如Qwest,及上千家和傳訊有關的小公司。
中華開發創投兩、三年前至美國開辦業務時,就看準網際網路及電訊市場,中華開發創投美國子公司總經理陳漪釧說,「 講到寬頻,大家就會想到光纖。」該公司已投入六家光纖有關公司,已投入的金額約一千六百萬美元,占該公司總投資金額的四○%,無論在時機及比重來說,中華開發對光纖的重視,可謂儘得天時。
由於光纖屬於新技術,所以一向偏於二、三期投資的中華開發也稍微改變方針,改投資光纖初創公司,由於初創期即投入,預計中華開發日後還會對這些公司加碼投資。
這六家公司中,只有兩家是中國人創辦的,其餘都是美國公司。在陳漪釧的帶領下,中華開發很專注地走美國路線,並且也耕耘出結果,這對來美國不過幾年的陳漪釧來說,是很不容易辦到的。
針對光纖熱潮,陳漪釧表示,因為光纖有技術上的突破性,不像網際網路講求的是「商業模式」,所以它有很大的想像空間,「只要做得出來就可以賣。」中華開發投資的公司偏重於元件的研發,至於系統級的,她說那是大公司的領域,其他人難進入。
六家公司中已有一家上市,叫做Vina Technologies(那斯達克代號VINA),它的股價平穩,並未一飛沖天。
系統型的產品生命周期長
漢鼎亞太位於近一年快速形成的帕洛阿圖(Palo Alto)新興創投業區。此區在大學路上,離史丹佛大學才一街之隔,街小車多人多,對面還有一家電影院,怎麼看都不像創投金融區,不過反正它就是出名了,短短幾個街段間一下出現三、四十家創投。
漢鼎亞太占據了一個獨棟的兩層樓,很有氣派,現在正裝修,將來如有多餘空間,將進駐一些新公司。
漢鼎亞太董事長徐大麟說,他們並沒有特別投資光纖公司,不過在泰國曼谷投入兩千萬美元,和原海門(Seagate)總裁Tom Mitchell合作,買下海門的工廠,成立Fabrinet,做光纖零件的生產。「海門做磁碟機,和光纖的生產性質最近,屬於非常精密的製造,」徐大麟表示。
不過喜歡技術的徐大麟,自然不會忽略在技術上有很多突破潛力的光纖技術。最近他協助一位加州柏克萊大學小學弟雲維傑成立AIP(Advanced Integrated Photonics ),已募得許多錢,馬上就要大做一場了 。AIP做光的轉換器,除了採用較新的光學轉換(而非電轉換)外,其設計也能簡化原本繁複的製程。
對於投資熱潮,徐大麟表示,十年來已有兩度投資熱,一是一九九二、九三年間的生物科技,「產品不知何時做出,可是大家仍猛投,」他說。一是九六、九七年間的網際網路熱。如今回頭看,生物科技熱算是財務上的失敗,網際網路熱已有災情傳出,但總賬還不及結算。對於投資熱到底該怎麼看?他表示,浪潮來時,有時也沒有辦法以傳統的金科玉律去評估。
台灣創投業者是否參與這股熱潮呢?台灣一位市場分析家指出,台灣本身市場小,玩不起光纖這個大遊戲。若以投資來論,台灣創投家在美國也不容易找到好關係、好管道,「光纖基本上是美國大公司做的事,如朗訊(Lucent)、思科(Cisco) 、JDS Uniphase等,中國人大多是做零件,很難做到系統那一階層,而且光纖這一行很專門,很多投資人也不懂,」依照程有威所說,「系統級的產品,生命期才長。」陳漪釧也表示,「系統一旦被企業採用,就不會換,所以生命期長。」
光纖產業的創業家
談起光纖創業,不能不提知名矽谷華裔創業家陳五福,他懂科技,也懂錢,再加上二十多年在網路方面的經驗,正好在光纖方面大展鴻圖。
陳五福愈來愈受到美國主流的重視,九月號的《紅魚》雜誌就將他選為二○○○年十大創業家。對於光纖,他說,「需求是供應量的三、四倍,是一個可容忍犯錯的行業,只要做得不錯,都有機會。」下面是他的光纖版圖,預計明年開始會陸續看到成果:
Optimight(optimight.com):「這家公司鑽研新技術,有技術風險,」陳五福說。這家公司由史丹佛大學博士組成,增加光纖載量及再生的能量,以達長途傳送的目的。這家公司已有六十人,已募集三千七百五十萬美元,背後有許多有份量的美國創投支持,如Brentwood Venture Capital, Venrock Associates等。
Geyser Networks:利用現行的SONET(Synchronous Optical Network)架構,讓用戶共用光纖頻寬,屬於光纖管理方面的產品。
Zettacom:做網路處理器和光纖交換機的綜合體。
熱心公益的矽谷「好好先生」龔行憲也是光纖高手,八○年代曾參與創辦SDL(最近以天價賣給JDS Uniphase)。他新成立的公司是Pine Phonotics,做都會光纖網路中所需的光源、檢收器、放大器等,問他這一行業有多少競爭者時,他說,「很多」。
Optiwork可做為台灣廠商切入這個領域的代表。這家公司由台灣的茂聯分出來,專門做光纖設備中的隔離器、耦合器等,他們除了在美聘用研發人才,最有力的一點就是可利用茂聯在上海、廈門等地的製造廠。Optiwork總裁梁華哲說,「如沒有製造基地,要在這一行發展頗不容易。」 ,這一行業競爭者很多,無法計算,甚至在計算的當時,都會多出幾家來。
光纖產品的製造要求是精準。在Optiwork內,戴著工作帽的人員拿著細如白線的光纖在顯微鏡下仔細看,細心調。一般認為,亞洲人的細心及耐心才能做這樣的工作,如E-Tek內就有許多大陸來的工作員。所謂「細如白線」的光纖其實外面已加了兩層圓罩,肉眼才看得清楚,真正的光纖比頭髮還細很多,肉眼很難辨識。北美工研院經理何明彥說,光纖產品很多還是靠人工製造,所以亞洲人有機會,「也許因為手比較小吧!」
華人中做光纖最出名的,是由潘精中夫婦在一九三三年就成立的E-Tek,這家公司上市後就由美國人經營,如今已不算華人公司了,由E-Tek出來的曹小帆、蔣世琦、趙自強創辦Avanex,今年二月上市,股價當天衝至一百七十五美元,最高達三百美元,後來回降,而這家公司年營業額不過一千多萬美元,曹小帆已身列四十歲以下的富豪排行榜了。Kestrel Solutions七名創辦人中有兩名中國人,張曉本和余庭光,這家公司產品還沒出來,已籌得一億八千五百萬美元。另一家Amber Network最近第三期籌資共得九千一百萬美元,急著找人擴充業務。
華人很少去做鋪光纖的大事業(除了網上網AboveNet的執行長段曉雷,他正聯合亞洲諸國來舖設美國至亞洲之間的海底光纖),而多是做光纖傳送中所需要用的矽片、元件、模組、次系統等,光是這樣的關係就形成不小的生態鏈,最快的獲利了結方法,就是把產品做出來,賣給你的下游。如Pine Photonics做都會光纖網路中所需的光源、檢收器、放大器等,這些模組做好後就賣給系統公司。Optiwork做的產品雛型(prototype)都可賣,賣給誰呢?賣給那些仍在做產品雛型的公司。
由技術面看光纖產業
徐大麟六○年代在柏克萊唸書時,就做過光纖,技術是有了,但是沒有大用,他說,「就像汽車的安全氣囊,備而不用。」直至網際網路發達,光纖才找到貢獻人類的地方。何明彥也說,有關光學的知識早就有了,只是以前沒拿出來用。
DWDM(Dense Wave Division Multiplexing)是經常聽到的字眼,它是指波分複用,也就是在同一條光纖中打出不同波長的光,一波長就是一頻道,頻道越多,傳送量就越大。何明彥指出,現在DWDM通行的是40頻道,業界希望做到80頻道。在國際、長途光纖網路中,DWDM已很流行,在都會光纖網路中,因成本問題,應用還不普遍,原本的光纖通訊標準SONET仍是略勝一籌。
在技術人才方面,大家都同意最好回大陸找,來自大陸的雲維傑說,大陸基礎科學強,物理人才多,這些人做光纖都很適合。在美國的大學中,微機電(MEMS, Micro Electro-Mechanical Systems)這個字眼很紅,許多光纖零組件不全靠電子來解決,而要加入精密的機械作用。
就技術來說,光纖有很大的突破空間,就投資來說,許多公司價值都已過高,所以現在投入,風險跟著升高,那就看你敢不敢賭了。
不過據《紅魚》雜誌的判斷,光纖股還算比較「安全」的。光纖是傳輸管道的大加寬、大翻新,它已撞擊出科技人、投資人的大熱情,甚至還有光纖迷這樣說,「當地球的石油都用完時,光纖仍在。」(對光纖有興趣者,可上lightreading.com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