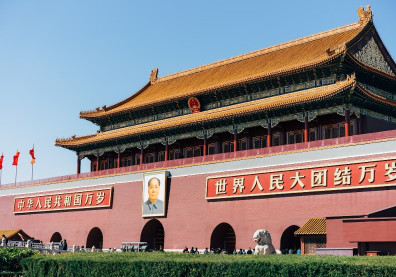子夜十二點,廣東省東莞市。
一○七國道旁,綿延不絕的現代化廠房,燈火通明如白晝,機器轟隆轟隆徹夜運轉。一些大型工廠的門牆外,攤販雲集成夜市,等著做夜班工人的生意。剛結束晚班的男工成群打著赤膊,在街頭擺設撞球桌取樂。這裡沒有夜晚,不眠不休。一雙雙歐美名牌的運動鞋,一顆顆台灣設計的電腦配件,二十四小時不停地從東莞的生產線,順著珠江這條大動脈出口到世界。
從行政位階來看,東莞只是個「地級市」,和台灣的縣轄市相去不遠;但去年東莞的外貿順差勇冠大陸各城市,今年的出口總值更超越老大哥上海。每年二六%的經濟成長率,使東莞成為「廣東四小虎」最生猛的虎頭。
「每次(經貿)政令推行,都選擇上海、深圳和東莞『試點』,」東莞台商協會副秘書長王柏齡解釋東莞的經濟地位。
台灣最大的海外生產基地
毫不誇張地說,東莞的經濟奇蹟不能不歸功於台灣經濟奇蹟的移植。這裡是大陸台商家數最多的所在,也是台灣最大的海外生產基地。三千七百多家台資企業,三、四萬名台商老闆和幹部,燃燒著當年創造台灣奇蹟的打拚精神,從傳統製造業到高科技產業,從上游原料到下游組裝廠,把完整的產業體系都帶過來。
有些經濟學家甚至擔心,東莞與台灣已從「互補」演變為「競爭」的關係。
「來東莞講台語嘛也通,」一名台商在「荔枝節」招商會上,推薦來東莞投資的優點。在台灣鞋廠密集的東莞厚街鎮,隨處可見台灣檳榔攤,滿地亂吐紅汁的景象,東莞市政府忍不住想取締,詢問東莞台商協會會長葉宏燈的意見。葉宏燈半開玩笑地說:「台灣經濟奇蹟發生的原因之一,就是每天工作十六到十八個小時。檳榔是提神的,代表台灣的競爭力,代表台灣的精神。千萬不要取締,否則海南島要跟你們打仗囉(檳榔是海南島的出口大宗)。」
葉宏燈引述資策會的統計指出,台灣有十項電腦資訊產品的市場占有率世界第一,包括主機板、掌上型掃描器、桌上型掃描器、電源供應器、鍵盤、滑鼠、視訊卡、監視器、數據機和機殼。除了主機板以外,其餘九項在東莞都有大型生產基地。最近技嘉也赴東莞設廠,最後這塊也補齊了。
「台灣上市電子公司,目前已有二、三十家在東莞設廠,」東莞市長佟星娓娓數來,族繁不及備載。台灣股市許多「中國概念股」,更精確的定義應該是「東莞概念股」。然而,當這些公司亮麗的EPS (每股盈餘)成為股市追逐炒作的題材時,從來沒人想過,這些抽象的數字是多少東莞台商挑燈夜戰換來的。
東莞市委書記李近維比喻說,珠江東西兩岸的經濟,百年來大戰了好幾回合。第一回合是香港對澳門,珠江西岸泥沙淤積,帶給澳門肥沃的沖積平原,卻把深水港留給香港,結果是東岸獲勝。第二回合是改革開放後,深圳與珠海兩大特區之爭;在香港做後盾下,東岸的深圳再度勝出。
現在戰況進入第三回合,由東岸的東莞迎戰中山、南海、順德這幾隻小老虎。「有台商幫我們一把,我們可以贏,」李近維發出豪語。
山非山,水非水
一騎紅塵妃子笑,楊貴妃垂涎的荔枝,產地就是東莞。從前這裡是百分之百的農業縣,典型的嶺南魚米之鄉,水田和魚塘阡陌相連,珠江河道密如蛛網,船與橋構成地景的元素。低矮的丘陵上,荔枝紅於二月花。東莞經濟的起飛,最明顯反映在自然景觀的巨變。
如今東莞「山非山,水非水」,視線所及的山丘無不被粗暴地橫劈直削,挖掘成各種奇形怪狀,土石賣給香港填海興建新機場,或用來填平魚塘。挖山填水的新生地上,工業區不停破土而出,河渠與舢舨也被筆直的公路取代。
大興模具公司經理曾煥祥記得,七年前他來設廠時,從東莞搭車到廣州,早上九點出發,下午三點才到得了,半路經常碰到騙徒或搶匪。如今行駛廣深高速公路,一個小時就能到。當時厚街鎮的地價每平方公尺不到兩百元人民幣,如今三萬元不見得能買到。
藉租售工業用地給外商,東莞各級政府和管理區賺翻了。許多鎮區居民每月在家坐領現金分紅即可,根本無需出外工作,工廠很難招募到本地勞工,都靠外省「打工仔」維持。東莞市政府還將義務教育延長為十二年,甚至全民健保和老人年金,部分鎮區也已開始試辦。
「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外地勞工,使台商脫掉擴充產能的緊身衣。「台灣有多少員工,來這裡就乘以十倍,」統順鞋業公司協理朱蔚紫說。要不是東莞有生產基地,製造電源供應器的台達電子,無法晉身全球龍頭;製造運動鞋的寶成鞋業也無法拿下世界第一,子公司(裕元)股票在香港上市。
台商在東莞發跡的故事,最常被提及的就是葉宏燈的致伸電子。十年前他銜命到東莞設廠時,只有二十五名員工,如今已擴展為九座工廠、四千多名員工,所生產的掃描器名列全美三大品牌。台灣母公司也「母以子貴」,從名不見經傳的貿易公司,躋身台灣百大製造業(排名第七十七),六年前股票上市。
「也就是來東莞投資,(致伸)才有機會股票上市,」葉宏燈說。走訪東莞台商,踏進作業現場方知何謂「勞力密集」。人山人海的勞工,擠滿面積有運動場大的廠房,乍看之下還會令人產生輕微的暈眩感。王柏齡開玩笑說,台灣流行的「面相管理」,在這裡或許能派上用場,因為所需勞工數量龐大,根本無從精挑細選。
不少台商為求省事,乾脆用「省籍篩選法」,騾子性格的湖南人成為黑名單榜首,許多招工海報直截註明「湖南省籍免問」。
無論西進南進,最重要是上進
如果對台商的印象還停留在「被淘汰的夕陽產業」的話,那就落伍了。轉戰東莞,一切都重新歸零,由全新的起跑點出發。台商的競爭力普遍更上層樓,已非吳下阿蒙。曾經有人說,台商西進也好,南進也罷,最重要的是「上進」。中小企業升格為中大企業,中大企業升格為世界級企業,只是東莞台商上進的表徵之一。
有經驗的台商都知道,在大陸的實際投資金額常超過原先預計的三倍。主要原因是,在大陸採購原料和零件不像台灣這麼方便,不少台商被迫往上游產業發展,形成更完整的生產體系。
以大新彩印紙品公司為例,原本在台灣是三級紙廠(一級廠生產紙漿,二級廠加工為紙板,三級廠製作紙箱),生產鞋類與電腦包裝紙箱。十年前,客戶紛紛移師東莞,生意流失了七成,只得跟著轉移陣地。但來到這裡才發現,所需紙板很難取得,唯有自行生產。就這樣趕鴨子上架,成為東莞第一家「一貫作業」的包裝紙器廠,從紙板到紙箱,從製版到彩印,全部一手包辦。
格局的開展,使台商有能力搞研發,不再連想都不敢奢想。在這裡,一家普通的鞋廠也可能有先進的實驗室,從事鞋材的測試開發;一家普通的高爾夫球用具廠,也可能聘雇好幾打研發設計人員,由OEM (原廠委託製造)轉為做ODM(原廠委託設計製造)。
「世界經濟發展過程中,上天很公平地給每個國家一次機會,唯獨對台商特別厚愛,給了兩次機會,」全球華人競爭力基金會董事長石滋宜在東莞的這段講詞,成為葉宏燈經常引用的格言。
就兩岸產業分工來說,台商雖然生產移到大陸,訂單仍然在台灣接。「我們把外匯留給台灣,利潤留給台灣,金雞蛋全部留在台灣,」葉宏燈說。「台灣的外匯存底,其實還不是台商賺的!」偉智電子董事長梁梅子說。
為何跟台灣沒有(閩南)族群淵源的東莞,成為台商最熱門的投資地點?從事玩具製造的翟索領的經驗談,可以解答部分的問題。
東莞取代雅加達
一九八八年台幣大幅升值後,和許多玩具廠商一樣,翟索領也轉赴印尼設廠。但是一九九四年,當政府吹起南進政策的號角時,「九○%的玩具廠都從印尼撤退了,」翟索領也轉往東莞落腳。
翟索領指出,印尼民族性懶散,每到發薪日隔天,工人就不見蹤影。平常每天只開工七小時,加班超過三小時就算違法;假日工人都不願意加班。因此,「薪資雖低,出貨卻少,固定設備成本分攤很高,反而不划算,」翟索領說。而在中國大陸,一聲號令全部加班,工人沒有不配合的。
更頭痛的是,印尼配套產業不發達,零配件都要從台灣進口,很容易耽誤出貨。而製成品外銷時,貨櫃必須從印尼港口先用子船送到新加坡,再轉運到歐美各地,更加不利於爭取時效。到了東莞,大部分零配件都能就地取得,水陸運輸的便利也沒話說。
翟索領說,外國客戶的遠東總部大部分在香港,東莞得地利之便,客戶容易就近造訪,「客戶看得愈多,訂單下得也愈多。」況且玩具的安全標準愈抓愈嚴,稍微變更材料或設計,客戶就要做安全檢驗。究竟往返香港與東莞省事,還是往返香港與雅加達省事,答案顯而易見。
葉宏燈分析,台灣經濟奇蹟的秘訣在於「產業網路」和「人脈網路」的集結。如今,這兩大網路也在東莞形成氣候。
產業網路方面,台灣企業做得「非常專、非常精」,形成完整的衛星工廠體系,所有材料都能現地採購,有利於節省時間和成本。
人脈網路方面,葉宏燈提出獨到的觀察:「同樣的訂單,下給美國廠商要四個月才能交貨,下給台灣廠商只要十五天,」而且,「一個產品有幾百個零件,美國廠商接到訂單,要跟這幾百家零件供應商逐一打契約,打完契約三個月就過去了。台灣廠商根本無需契約,只要花兩、三天的時間,打幾百通電話,零件商就會同時趕貨,三、五天內把東西送到組裝廠,組裝廠再花一、兩天組裝,只要七天貨就好了,再花一個星期運到美國西岸。」
為何台灣不用打契約呢?人脈網路的妙用就在此。葉宏燈認為,台灣的檳榔、卡拉OK、老人茶和飲酒文化是有學問的;商場默契就是這樣培養起來的。在速度就是財富的時代,台商用最傳統的方式,建立高度時效的商業關係,搶得市場先機。
移植產業,重建人脈
台商進駐東莞,不是「點」的進駐,而是整個產業網路都移植過來,電腦、製鞋和家具是典型代表。「東莞方圓五十公里內,可以買到組裝一台電腦的全部零組件,」李近維說。因此,IBM 、康柏、Packbell 等國際大廠紛紛在東莞設立採購中心。而宏?電腦的大陸廠雖然設在珠江對岸的中山,採購單位也擺在東莞。
在低價電腦的衝擊下,繼傳統勞力密集產業之後,台灣電腦業者掀起新的登「陸」浪潮。東莞挾著國外買主薈萃,以及零組件應有盡有的優勢,很快就幾乎把台灣大廠一網打盡。特別是今年初,康柏電腦的執行長換人後指示各地區採購主管,要求降低一五%的採購成本,不能達成目標就要撤換該地區採購主管與供應商,加深台灣電腦業者的憂患意識,西進的腳步也愈來愈快。
「改革開放我們東莞先走一步,升級轉型我們也要先走一步,從勞力密集型轉向技術密集型,提高我們的經濟檔次,」佟星說。在台灣高科技業者集體「灌頂」下,東莞與台灣的差距急劇縮小,甚至東莞新廠的設備技術還可能比台灣母廠更先進,而不是把淘汰過時的生產線移到東莞。許多台商估計,不出十年,勞力密集產業將從東莞「畢業」。
另方面,如何重建人脈網路,也對台商構成考驗。「大家從台灣各地來到東莞,三重幫打破了,新莊幫打破了,台中那些『黑手』也打破了,若彼此都不認識,怎麼做生意?」葉宏燈問道。
葉宏燈藉著台商協會,努力把「一盤散沙」的台商整合起來。參加協會的台商比率從他接任會長時的兩成邊緣,成長到接近九成。在台商協會之下,有二十四個聯誼會,十三個功能委員會,十四支高爾夫球隊,還有婦聯會。次級團體和聯誼活動無比「茂盛」,其用心就是要讓會員熟識彼此,重新搭建人脈網路。
勞動彈性強化台商生存韌性
台商在大陸生產的優勢,勞力便宜是其一,交貨迅速是其二,有時,「時效優勢」的重要性還超過「工資優勢」。
台商出貨效率如此神速,人脈網路因素固然重要,但加班趕工的無限彈性也功不可沒。台商協會副秘書長樓達人指出,無技術經驗的外地勞工在東莞的起薪行情僅約每天人民幣八元(新台幣三十二元)。在本薪低微和匯錢養家的壓力下,大陸勞工加班意願極高。
相對於台灣勞工的「老弱婦孺化」,大陸勞工的平均年齡大約在二十歲上下,體力正值顛峰期,能承受長期高強度的加班。在不計時間趕工的情況下,台商無需增添人手就能應付突如其來的大訂單,或景氣的強勁復甦,在好時機搶占更多生意。
穩健高爾夫球用品副總經理鄭玉環說:「台灣週休二日,一天能做多少事?這裡不一樣,沒有星期六,也沒有星期天。客戶晚上過來,一個訂單下給你,很急明天要用,工人馬上加班做出來。在台灣誰理你啊?這邊運作很快,效率真的很高。從前在台灣做兩萬台球車就滿檔了,現在(東莞)十萬台也是在做,十八萬台也照做,工人也增加不了多少。」
「以前在台灣,量根本放不出來,來這裡我才敢接大單,」穩健公司總經理陳明森補充說。
生意好,拚命加班;生意不好呢?「那就放假嘛,不然就勞動服務,叫工人割草、大掃除、刷牆壁,」樓達人苦笑。
在外有亞洲金融風暴、內有人民幣堅挺的重壓下,台商撐得相當辛苦,「從來沒看過景氣這麼差的」。有些台商的做法是給大陸工人兩個選擇:要麼辭職回老家,要麼就留下來,廠方供應食宿,但停發薪水。大陸工人唯恐找不到工作,多半選擇留下來,沒事可做就「勞動服務」。台商就這樣熬過谷底,「最近訂單又開始接不完了,」樓達人說。大陸伸縮自如的勞動彈性,強化台商的生存韌性。
「7- eleven 頭家」
從「工作倫理」的角度看,中小企業主的勤勞苦幹是台灣經濟奇蹟的原動力。他們來到大陸「二度創業」,不但延續從前在台灣的打拚精神,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儘管他們平均年齡超過五十歲,也不再是初次創業時的小伙子。
葉宏燈清楚記得,六年前他剛接手台商協會時,跑得最勤的地方就是殯儀館,經常有台商在交際應酬時莫名暴斃在KTV 包廂裡,每個月少則三起、多則五起。「主要原因在工作壓力太重,」葉宏燈解釋。
大陸的工廠規模比台灣大十倍,能從台灣派過來的幹部卻只有十分之一,老闆肩頭的重擔可想而知。台灣中小企業的特色是,老闆娘不僅扮演賢內助,更是頭家的最佳拍檔,撐起企業的半邊天。可惜這些「賢外助」們,大部分無法與丈夫隨行。而大陸勞工的刁鑽與海關的刁蠻,更是台灣所無法想像的。凡此種種無不使台商心力交瘁,「折損率」高也就不足為奇。
「像我們這種年齡,還在這裡賣命,感覺有點不值得,」大新彩印紙品副董事長林李素禎說。
有些台商笑稱自己是「7-eleven .頭家」,理由是「全年無休,全天待命」。台商幾乎都直接住在工廠,住家樓下就是廠房,打開窗戶就能隨時監視生產狀況。「我們根本沒有上下班時間,工廠二十四小時運轉,隨時有事要處理。在台灣,工作場所是工作場所,回家是回家,這裡全都以廠為家,(忙得)幾月幾號都不知道了,」鄭玉環說。
澳洲學者A. Sergeant 和S. Frenkel 曾經針對勞工管理問題訪查大陸外資企業主管,得到的結論是:「大陸勞工相當被動,缺乏時間觀念,對品質不甚注意,遇到問題不去解決,除非主管指示。總之,可以歸納為『工作倫理欠佳』與『工作習慣不良』。」
緊迫盯人為最高管理原則
「管理大陸員工,一定要從『人性本惡』出發,然後再去修正,」王柏齡說。於是「緊迫盯人」,就成為台商的管理守則。
佑興鞋業公司副理王林招治為了監督趕工,最高紀錄曾經連續二十四天,每天只睡兩個小時。她堅持在生產現場坐鎮,不肯窩在舒服的辦公室,「不然品質做得好不好誰知道?」
東莞台商婦聯會長朱蔚紫的統順鞋廠雇用多達一百五十名幹部,監督兩千名工人。「好多次明明可以出的貨,結果尾數差幾雙,貨櫃出不去的損失有多大!所以,現在出貨櫃我專門找人盯,盯的人後面還要有人盯,好像間諜對間諜,真的很辛苦,」她說。
穩健公司總經理陳明森也指出,大陸人工固然便宜,但是出貨品質差,非得雇用許多品管人員把關不可,因此總勞動成本不如想像那麼划算。
台商最感頭痛的是員工偷竊的問題:工作用的手套經常不翼而飛,拆成毛線織衣服;員工餐廳的大廚把剛煮好的飯菜偽充餿水賣給養豬的;課長代領組員薪水後佯稱上洗手間,跳牆落跑不見蹤影……。提到被「暗槓」的經驗,每個台商都有講不完的故事,講來既生氣、又好笑。
生產聖誕飾品的亞華公司,材料用到漂亮的緞帶和珠鍊,女工們時常順手牽羊,帶回宿舍改造成髮飾,害得公司沒辦法出貨,只好下令搜查宿舍。台商必須花很多心思抓內部弊端,無法全力在市場衝刺。「跟大陸員工鬥智真累,」亞華公司經理詹秀美抱怨。
大陸勞工「老鄉情結」的濃厚,也使台商匪夷所思。例如湖南省籍的員工甲,跟四川省籍的員工乙發生摩擦,很快就演變成兩省員工打群架。某家鞋廠任用一名安徽籍幹部管理生產線,結果他招募了九十八名工人,清一色是安徽老鄉,廠方知悉後全部解雇。
由於深夜趕工疲勞,大陸工傷事故特別多,而勞工的安全意識也明顯不足。東莞某家生產模具的台商刻意到市場買豬腳,當著大陸員工的面把豬腳靠近機器,「喀嚓」應聲切斷,提醒留神機器的可怕。沒想到示範完畢沒多久,一名工人的手就被切斷,起因是他想親手玩玩看,機器到底有多鋒利。
不久前,東莞台商的工傷糾紛驚動北京高層。一家台資企業在兩、三年內相繼有三十多名大陸工人的手被機器切斷,公司方面拒絕賠償不說,還恐嚇受傷工人,誰敢報案就打死誰。結果案情還是傳開,就在東莞官員和媒體眾目睽睽下,台籍幹部當眾毆打受傷工人,新聞登上報紙頭條,廣東民眾群情激憤。中共總理朱鎔基下條子,責令封廠查辦。
大陸幹部「可用不可信」
無論如何,從薪資成本考量,台商終究得「人力本土化」,起用更多大陸幹部以逐步取代台籍幹部。但台商私下評價,還是認為大陸幹部「可用而不可信」。
東莞台商協會副會長蔡俊宏表示,栽培的大陸幹部裡不能說沒有忠誠者,問題是他們若跟資方靠近會被同仁恐嚇,搞不好還要挨揍。「有些幹部話講得很明,在工廠有老闆保護我,出去誰保護我啊?叫我做工沒問題,千萬別叫我管人。勉強派他管理,也是睜隻眼閉隻眼,老闆若在就管得嚴些,老闆不在就管得鬆些,很難有得力的幹部。縱使他不變節,周遭同事也逼他變節,」蔡俊宏說。
葉宏燈指出:「由於台商規模龐大,必須把最新的管理技術移過來,因此訓練不少大陸幹部,學會什麼是JIT(即時供應系統),什麼是QCC(品管圈),什麼是ESP(提案制度),還有MIS(資訊管理系統)。」
大陸勞工的聰明好學,翟索領深有體會:「一些昂貴的機器設備,工人偷偷摸摸拆開來研究,有時拆了裝不回去。從前在印尼設廠,工人碰都懶得碰。」
然而,培養大陸幹部好比養虎為患;把該學的都學會後,他們就自立門戶,用低廉的報價跟台商搶訂單。尤其在製鞋和玩具業界,大陸本地企業的競爭,已嚴重威脅台商的生存。「最近東莞每個月都有好幾家廠oust(淘汰出局),」葉宏燈說。
頗為諷刺的是,從台資企業離職的大陸幹部自行開設的鞋廠,有數家聘用台籍幹部來管理。蔡俊宏告誡子女:「你父親這一輩是來大陸當老闆,你們若不努力,以後去大陸只有打工的份,能當課長就不錯了。」
台商進無路,退無步
今年元月份起,中共開放出口許可權證,私營企業也能取得出口資格,這意味將有更多大陸競爭對手跟台商搶占出口市場。
「前有壓縮,後有追兵,」葉宏燈概括台商的處境。在美國買主壓縮採購價格(如低價電腦),以及大陸企業急起直追的夾殺下,「有些產業即使移到大陸都很難生存,要被大陸私營企業取代,」葉宏燈指出。
不少東莞台資鞋廠去年前往越南探路,非常失望地發現,當地配套產業和官僚體系都落伍不堪,許多廠商再度退回東莞。「台商進無路,退無步!」偉智董事長梁梅子說。
對台商打擊更重的是,大陸當局自去年起,一再衝著加工出口業者端出不友善的法令政策,「每個政策都讓台商活不下去,」葉宏燈蹙著眉頭說。
東莞台商從事加工出口的,在大陸算是最多,反應也就最強烈。他們數度進京請願,引起兩岸政府重視。「我們面臨的是全球性的競爭,所以對政策因素特別敏感,」葉宏燈解釋。
追根究底,自亞洲金融風暴以來,大陸當局想盡辦法挽救疲軟的經濟,對外商也就顧不了那麼多。舉例來說,為了保護本身國營企業,大陸雷厲風行查緝走私。不幸的是,加工出口業,被視為走私的大本營,矯枉過正的防治手段使台商正常營運遭到池魚之殃。
對於大陸海關作風刁蠻,動不動就查驗貨櫃,台商無不抱怨。有時只是名稱的歧異,像是湯匙申報成調羹,或是報關員稍有筆誤,就會被卡關。急著要用的原料進不來,趕著裝船的貨櫃出不去。台商的核心競爭力——時效性,受到嚴重傷害。
一名鞋廠老闆說,有一次貨櫃通關時被攔住,理由是重量太輕。當他把整櫃的運動鞋卸下準備接受查驗時,忽然下起滂沱大雨。海關官員自行離去,任令這批貨在雨水浸泡到第二天,結果全部發霉報銷,他想到就心痛不已。
另一家台商,原料無緣無故被海關查扣半個月,好不容易到手的訂單,只得轉給別人代工。等到貨物裝櫃出關時,又被海關查驗個沒完。為了趕時間,海運改成走快船,貨價還抵不過運費。「這種損失再發生幾次,我工廠就得關門了,」他忿怒地說。
為刺激內需,中共投注數千億元,稅收遠不敷所需。於是財政部指示海關,無論如何都得徵收到八百億元。為達成目標,海關只好大肆查廠,藉取締違規之名,行斂取罰款之實。
從互補到競爭
東莞台商協會曾經反映,從合同備案到出口,大陸海關規定的手續中窒礙難行的多達十幾條。特別是「先轉廠,後送貨」的規定,甲零件廠送貨給乙組裝廠,必須先行辦理冗長的轉廠手續,否則視同走私,台商根本無法照辦。也因此,「海關查廠的結果,絕對每家台商都是千瘡百孔。海關伸手要幾百萬,你都得給他,否則就會被封廠,」葉宏燈說。
一名餘悸猶存的台商婦女說:「碰到海關來查廠,心都不知道嚇到哪裡去了。反正我們是鳥進籠子,任他宰割了。」驚悚劇還沒完。去年底大陸頒布新稅制,外商進口原料要被課徵高達一七%的增值稅,等產品出口核銷後再退還稅款九%。用意是遏止外商擅自內銷,並對外資企業「變相加稅」八%。
台商群情恐慌,紛紛提出質疑:「大陸做外銷的廠商,有幾家淨利超過八%的?賺的錢還不夠繳增值稅。」「誰敢保證能領到退稅?大陸企業本身的稅都退不下來。共產黨把錢拿去,你就別想拿回來。」
今年五月,中共投下威力更強的震撼彈,將依據海關違規紀錄以及出口規模大小,做為評核標準,對企業進行分類管理。東莞台商協會初步估計,可能有七成五的東莞台商因為違規超過兩次,而被列為C類企業,必須在進口原物料時繳納近四○%的保證金。
「台商的流動資金都被卡死了,」王柏齡說明嚴重性。
即使級別較高的B類台商,進口限制性原料時仍然要繳保證金。至於有走私前科的D類台商則根本別想再進口原料,除了撤廠,別無選擇。只有為數不多的大型優良企業才有機會列為A類,享有更寬鬆的優惠。
藉行政手段淘汰不適合者
中共的出發點是鼓勵企業守法,但落實到執行面,卻使海關的裁量權過大,足以判定企業生死。而海關的風紀如何,台商心裡都有數。廣東省主管經濟事務的副省長湯炳權便含蓄地批評說:「管理的手法和目的應該一致。」
這套措施的頒布,在台商耳朵聽來不啻一記警鐘。它所傳達的訊息是,大陸已不再無條件歡迎外商,而開始藉由行政手段把不適合的淘汰掉。傳統產業台商不禁懷疑,階段性的利用價值告罄後,也許不出幾年,自己也將接到逐客令。
歸結言之,在東莞這個前哨站,可清楚瞭望到台商正在重新洗牌。在大陸本地企業低價挑戰,和法令政策拖累經營成本下,台商傳統業者盛極而衰,甚至逐漸「淡出」大陸;高科技業者則爭相報到,蔚為台商的新主流。
而兩岸的經濟分工,現階段是生產放在大陸,採購、財務和研發留在台灣。但隨著台灣資訊電腦業在對岸形成完整的產業網路,「材料採購在地化」勢所難免。而香港成立「創業板」,爭取高科技台商股票上市,則使財務轉向香港。至於研發部分,大陸充沛、廉價的科技人力,台商更是不會放過。還有什麼留在台灣?這恐怕是值得深思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