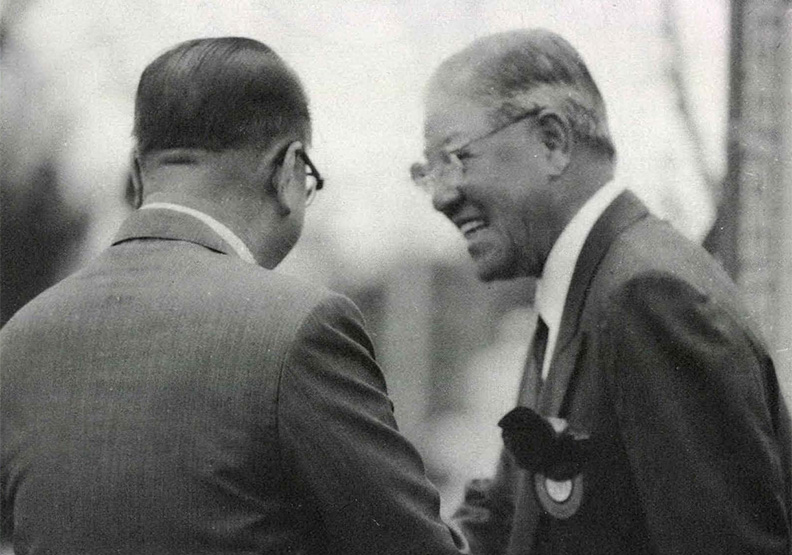李登輝、宋楚瑜十年分合,其實映照台灣走在歷史十字路口的迷惘和挫折。李登輝在世紀末以「不確定」創造他獨特的領導,下一個十年,台灣需要的是「模糊的策略」,還是「確定的方向」?
十年修憲,支離破碎,有兩個重大原因。
第一,政治人物缺乏「事件的連續感」。於是乎,1992年5月修憲民選省長,6月即有立委在立法院重提虛省;民選省長產生,即有政黨主張「廢省建國」。修憲、修法的時間邏輯,根本不存在多數政治人物心中。民進黨對政策主張,堅持中可以權變;國民黨的政策主張,則是毫無章法,跟著「李登輝意志」,一路迷茫。
第二,是特定政治人物強烈的歷史感,卻有迥然不同的終極方向。就像「台灣人的悲哀」一般,「台灣省的悲哀」更是深沈的歷史宿命。清廷建省,為的是衛戌沿海,當外侮入侵難擋,台灣還是第一個被犧牲掉。國民政府遷台,台灣省也沒有選擇的餘地。台灣省,始終在追尋自主、民主的過程中起起伏伏,曲折而痛苦。不論統、獨,台灣可以有主觀的意願,卻沒有促成的能力。
修憲凍省到底是否關乎統獨,一直有各種不同看法。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省,沒問題;台灣是中國的一省,有一點點問題。「中國」的定義到底是什麼?顯然有爭論。當中共以「中國只有一個,台灣是中國的一省」橫行國際時,「中華民國在台灣」創造一個新的論述空間,維持台灣的中華民國的獨立主權。
繼續演繹,打破台灣統治全中國的神話之後,台灣和中華民國之間,除了地理位置的描述,在政治、社會上,其實是一個等號。台獨論者基於對國民黨政權的厭惡,在這個等號關係中,不放棄努力更向台灣靠攏;國民黨政權則努力疏離純台灣化延伸的獨立聯想,保持「台灣省在中華民國之中」,以緩和台獨恐懼的象徵。
打破台灣統治全中國的虛象
李登輝特殊地採取一種刀鋒邊緣的策略,削弱「台灣省在中華民國之中」的聯結,一方面打破台灣統治全中國的假象,一方面也藉此衝出台灣是中國一省的迷思。他在統獨鋼索上,保持一種略傾斜而更靠向台灣的平衡,不破壞國民黨既有政權對統一中國的堅持,也成功地拉住民進黨對台灣意識的堅持。儘管隱然挑動傳統國民黨對他在統獨11索行走時,趨於獨的懷疑,卻還不致於明顯地遭致挑戰和反對。
分析李登輝歷次公開對修憲凍省的談話,從不觸及統獨話題,甚至根本對修憲是搞台獨的說法嗤之以鼻,談凍省、精省,一定強調行政效率、提升國家競爭力的重要。
但是,李登輝在接受日本媒體的訪問時,卻有另一套標準答案,「再度當選總統後的這兩年間,達成了競選期間所承諾的修憲目標,並進行精省工作,依據以往憲法之規定,台灣係立足於統治全中國之虛構中,所以中華民國與台灣省之管轄地域,事實上是重疊的,亦即疊床架屋之不合理結構……
排除這種虛構,精簡台灣省政府和省議會,以現實上能夠取得平衡之形式加以正常化,此種改革雖然亦遭到強烈反彈,但是我認為對台灣之末來發展,是絕對必要的,所以就付諸實行。」
真實的說法是,李登輝十年憲改的總體目標,就是「打破台灣統治全中國的虛象」;包括終止動員戡亂時期,放棄台灣(中華民國)對大陸的統治權。這個做法應該不致於被視為台獨,但卻是徹底而絕對地承認分離的現狀。
「獨」的遐想
即使宋楚瑜也只能私下幽微嘆問:「凍省是衝著宋某人而來?還是路線問題?」他隱約感覺,「路線問題」並不單純,甚至可能愈來愈嚴重,但卻有口難言。只能在不斷發出異議的同時,強調自己是「為台灣省負責,為歷史負責」。
李登輝亦復如是。在推動憲改的過程中,幾經波折、從不氣餒,同樣是基於歷史使命感的推促。他甚至已有充分的信心,十年主政,他的「歷史地位一已無庸置疑;儘管其最後的歷史定位和評價,可能是極具爭議性的。
從中國正統歷史詮釋的角度分析,在一個以中原一統為基本史觀的歷史評價,李登輝十年所做所為的終極方向究竟為何,左右對其評價的趨向。從人類自由民主的價值而言,李登輝開啟台灣真正的民主時代則是無庸置疑。人權與民主,在華人社會終於實現。
李登輝非常智慧地保持統獨的模糊,在所有官式文書和文稿中,絕對堅定統一立場,在政治運作和動作上,則對維持台灣主體地位絕不退讓;有一種「獨」的遐想,卻無法找到實證上的把柄。這使得十年來質疑李登輝的人士對其意識形態的批判,沒有絕對理論和實際依據。
李登輝在矛盾中,創造自己的政治價值與歷史地位;宋楚瑜在歷史的矛盾情境中,也得有不同的處置模式。他是外省子弟,又是唯一的民選省長,在統獨的光譜中,他是維持現狀趨向「統」;但在政治言論和動作上,絕對得標舉台灣優先論。
李、宋十年分合,其實映照台灣走在歷史十字路口的迷恫和挫折。李登輝在世紀末以「不確定」創造他獨特的領導,下一個十年,台灣需要的是「模糊的策略」,還是「確定的方向」?或許是領導精英在爭逐權力時,值得靜心思索的問題。
(本文作者為資深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