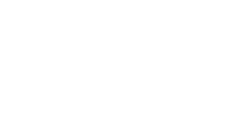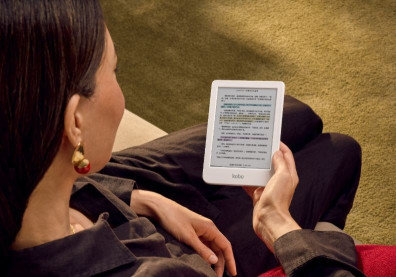自《借我一生》出版以來,知道我編了這本書的朋友最常問我的問題是:「余秋雨先生是個什麼樣的人呢?」或者是:「他是文學大師,應該不需要你這個小編太費心去校對編輯了吧?做他的書,你可輕鬆了!」
喜憂參半的第一類接觸
是啊,從事編輯工作能夠編到自己心儀作家的著作,進行「第一類接觸」, 用「美夢成真」四個字還不足以形容那種異常的興奮感:喜的是,從《文化苦旅》一書開始,我就是余先生的書迷了,沒想到竟然有機會編到他的新著作,喜悅自是不在話下。
但另一方面,我的壓力立時如潮水般「排山倒海」湧來,用「排山倒海」並不為過。近幾年來,任何人、事、物一與「余秋雨」三個字沾到邊,就會引發媒體的高度關注;也有人是以挑出余書錯誤而成為暢銷作家的。只要他一有任何活動或新作品,隨之而來的就是密集而猛烈的批判,從用字遣詞到內容、用典……甚至他的人格等等,無一不批。
這些批判中,有人要他「懺悔」,關於這部分,我尚可以用「和我的專業無甚相關」來自圓其說;但有人要為他「揪錯」, 這就是我的「編輯範圍」了;我可不願意自己編輯的書被揪出一堆錯誤,甚至還拿這些錯誤出書而大賣!
200張便利貼現大師風範
在這樣「一則以喜,一則以憂」的複雜情緒下,再加上得知要與大陸同步上市,我的編輯魂熊熊燃起(海峽兩岸編輯大競賽?)我決定「忘了他是誰」「見大人而藐之」,不管余先生是不是我景仰的作家,不管他是文學大師, 也不管「傳言」怎麼說……總之,我比平常更努力的查字典、上網查資料,對字的用法,到海峽兩岸用語的不同……問題無論大小、多麼枝微末節,我抱著「存心找碴」的念頭,化身為「揪錯大隊」,只要一發現疑問,就寫在黃色便利貼紙上,然後逐一貼在校稿上。等我整個看完,才發現600多頁的一校稿上,貼了200多張的黃色貼紙。
望著那一張張的黃色貼紙,摻雜在厚厚的校稿裡, 坦白說, 我的心情很忐忑, 我只是個小小編輯啊,面對文學大師,卻膽敢「太歲頭上動土」「關公門前耍大刀」「雞蛋裡挑骨頭」。懷著戒慎恐懼與惶恐不安,我硬著頭皮,送出了校稿,緊張的等待余先生的回覆。
隔幾天,同事從上海帶回了余先生修改超過50多次的校稿。我逐頁翻看著,幾乎每頁都留有余先生改過的筆跡,包括我所貼的那200多張黃色便條紙,他無一遺漏的看完,然後一一寫下解釋, 並多次寫著「謝謝指正」。這是大陸媒體長年批評「有錯不改」「驕傲」的那個余秋雨嗎?我完全感受不到任何一絲驕傲之氣,相反的,心中倍感溫暖!這是我對那些謠言第一次產生極大的質疑!
親賭大師崛文學奇峰
在這之後,隨著出版日期的迫近,許多事情需要討論、協調,我幾乎天天都與余先生的特助金克林先生聯絡。某次,余先生更是親自打電話來討論封面與確認書稿內容。一接起電話,他馬上就說:「我是余秋雨,這本書辛苦你了!」之前,本來還一直擔心自己在校稿上貼滿黃色紙條的舉動會讓他不高興呢,沒想到他不但沒有責備,反而讚許我存心找碴的舉措!這個人真的是那個謠傳中「驕傲」的余秋雨嗎?我再度對那些報導與批判極度質疑。
這期間,余先生為了讓文章讀起來更雋永精鍊,仍然時有修改, 有時僅僅只是更動一個字而已。終於深深體會到,「文章好到極致只是尋常」,這個「尋常」得來多麼不易,需要懂得割捨, 達到不露斧鑿痕跡的無技巧境界,才能造就如此千錘百鍊的「尋常」,就像王安石讚美唐人張籍寫的詩:「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我何其有幸,可以在成書之前,親自見證余先生的修改過程。
大師與小編的互證結構
余先生的《借我一生》裡提到:「謊言和謊言之間有一種『互證』關係, 誣陷和誣陷之間有一個『互撐』結構。當它們一次次快速地形成系統,受害者的任何抗議都變成「越描越黑」…… 」對於那些惡意的批判,也難怪余先生選擇了沉默, 所謂「橫眉冷對千夫指」,既然怎麼解釋都沒有用,甚至還會遭有心人扭曲,乾脆就對謠言徹底的相應不理吧!如果余先生真如報導中所說的驕傲、死不認錯……那麼,校稿上一張張寫滿余先生筆跡的黃色便條紙,還有寫著「謝謝指正」的字眼,又是從何而來呢?
對問我「余秋雨是個什麼樣的人」的朋友,我的回答是:「他是個謙謙君子!」當小編遇到文學大師余秋雨,沒有傲慢也沒有偏見,無論是書裡或真實的接觸經驗,我看到的是一個學富五車者謙遜的靈魂,還有面對文字時的斟酌再三與敬重!比起那些撲天蓋地、來
勢洶洶的流言蜚語,我當然更相信自己所經驗的一切,因為「眼見為憑」,也因為,這才是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