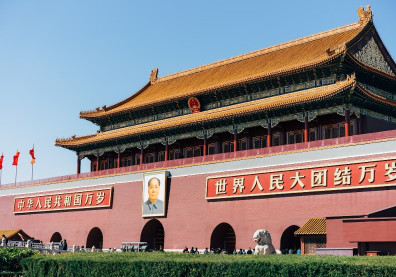「有沒有可能,在這一場可預見的、即將到來的電腦革命當中,我,李開復,能扮演一個重要角色?」1980年,當時還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律系二年級學生的李開復,忽然有了這樣的念頭。
「念頭」這玩意兒,不過就是電光石火之間的一個偶然,它像是一個來自現實之外的、帶著些許異想色彩的石子,投入腦海之後,激起小小波瀾,稍不留意,隨即就得淹沒於食衣住行的理性思維之中。只不過,李開復沒有讓異想的石子就此沉沒,他嚴肅端倪這個看似莞爾的念頭,認真傾聽心海裡的聲音,儘管只是小小波瀾,但已足夠喚醒李開復,「第一次,我有『真正找到自己』的感覺。」他說。
微軟的、Google的,科技的、人文的,我們所認識的每一個李開復,就從此刻開始。
找到自己前,先嘗試
「在此之前,我也是活在普世價值所形成的客觀標準框框裡。」兒時的李開復,和每個小男孩一樣,把自己的成功定位在成為太空人、科學家、總統...;稍長,追隨父親的典範身影,他以成為政治家為目標。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法律系,成績始終維持中上水準,眼看,這個目標不遠了。
「然而, 此時我才慢慢發現, 自己的興趣或許並不在此。」李開復仍然念書、仍然上課,但卻難以避免地感到枯燥乏味,「不過,討厭一種東西,並不代表就能立刻離開它,至少,你要找到『喜歡的事』,找到了,你也才能看到新的方向。」對李開復來說,喜歡的事、新的方向,就是電腦。
「即便如此, 我仍然花了一年的時間來嘗試『愛我所學』。」李開復先是給了自己一年的時間,試圖能在法律學系領域當中找到新的可能。一年過後,他決定傾聽自己的心,跟著它的聲音走,「這一年的時間並未浪費,因為,我終於能夠百分之百地確定,我的路,必須有所改變。」從法律系轉到電腦系,李開復要做真正的自己!
怎麼找到真正的自己?何以確定這是真正的自己?李開復提出解答:「問你的心,如果問不出來,不妨,試著想想自己所期待的墓誌銘吧!」理由很簡單,當你死的時候,你希望在喪禮上大家怎麼說你、怎麼緬懷你,你希望自己的墓碑上刻了什麼樣的事蹟,這些事蹟,就能代表當下你對自己的真正期待。
「各位女士先生,李開復在世時,把許多困難艱澀的電腦技術,轉換成為非常有用的產品,對這世界產生了莫大貢獻.....」在李開復決定扭轉人生方向、走入電腦領域之後,他對自己的墓誌銘也開始有了如上的初步想像,「我的終極目標,是把自己的影響力極大化。」李開復強調:「如果同時存在著『有我』和『沒有我』的兩個世界,那麼,『有我』的那個世界一定要更好。」李開復認為,透過電腦,他有機會能夠達到這個理想,「而我也十分確定,如果堅守在我沒有興趣的法律系,那麼我絕對無法達到目標。」
要得到前,先捨棄
改變需要一些衝動,但也絕對需要理智的制衡。「在追求自我價值的過程當中,理智扮演煞車的角色,透過理智的分析,才能確定這個改變並非純然只是衝動的結果,而是的確具有可行性。」李開復坦承,當年從法律系轉到電腦系,衝動的成分不小,然而,畢竟是場關乎未來人生方向的腦內革命,革命之前,仍然多少經過理智層面的分析辨證,「首先,我得想清楚,為了追求這個真正的自我,為了這個改變,我必須捨棄什麼?」
當然,兩年下來所累積的學分,至少就成績單上的「帳面」而論,從此歸零。然在帳面之外,李開復必須宣布放棄的,還有一個幾乎已可確定的、平穩安逸的未來。「我不敢保證我能把法律系讀得多好,但就一般來說,哥倫比亞大學法律系畢業的,找份好工作並不困難。」相對而言,當時的電腦系,尤其是哥倫比亞大學電腦系,並不算是職場主流。
平穩、安逸,甚至是富裕,難道不值得好好把握嗎?「這些當然都是好的,但對我來說,這還不夠,我的人生目標是影響這個世界,盡我所能地改善它。既然我對法律沒有興趣,不可能埋頭鑽研,當然,就更不可能藉此改善這個世界。」想到這裡,李開復清楚了解,在自己的目標之前,累積的學分、確定的未來,都不再是最重要的資產,而是必須捨棄的包袱。放膽丟下,才能了無牽絆地積極追求。
從法律系到電腦系,從確定的一生到不確定的未來,李開復必須思考衡量的,還有風險。一旦改變,他所要立即面對的,或許正是一片沒有足跡可循的漫漫黃沙路。「那麼,就來想一想吧!想想最壞的情況能有多糟。」李開復如此告訴自己。
凡事做最壞的打算
「我有信心能在電腦的世界裡發光發熱,然若事與願違,我想,最低限度我還能找到一個可以糊口的工作。」李開復想像,自己可能只是公家單位的一個小小技術員,抑或私人企業裡的程式工程師,「當然,這些工作同樣不能達到我的理想目標,但至少,我會愛我的工作,我會活得快樂。」
相對的, 如果李開復是個「法律人」,最糟的情況或許也能生活無虞,但是,「我就不會熱愛我的工作,我不會快樂。」於是,從世俗客觀的標準評估,兩者之間的風險相差不多,而從個人價值的主觀角度分析,改變的風險,顯然低於故步自封,因為故步自封的結果,恐怕會讓李開復鬱鬱一生。
事實上,這種悲觀思考的選擇邏輯,也在喧騰一時的「跳槽Google」事件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Google給我更充分的條件來實現理想,跟著心裡的聲音走,我必須轉換職場。不過,我沒有忘記可能遭遇的風險,而最大的風險,就是我將成為被告。」李開復回想,在做出決定之前,自己確實經過周嚴的理性分析,他檢視當年與微軟簽定的合約,自己看還不夠,找來律師一起審查,即便結論是「被告的可能性不高」,但他還是做了最壞打算:「如果真的被告,那麼,又會怎樣?」
李開復笑說:「我可能會失業一年、我的名聲可能受損、朋友可能離開。不過, 一年之後,我終究能夠在Google工作,這就夠了。」所謂的「夠了」,非指單純的工作而言,李開復強調:「雖然晚了一年,但只要能進入Google,就能朝向我的人生目標更進一步,想到這裡,我再無所懼。」
為墓誌銘添新章
「 各位先生女士,李開復在世時,把許多困難艱澀的電腦技術,轉換成為非常有用的產品,對這世界產生了莫大貢獻....不止如此,李開復同時也影響了中華民族的青年一代,在華人時代來臨之際,李先生做出了不可抹滅的貢獻。」
「是的,與多年之前相比,我所期望的墓誌銘,增加了一個新的段落,這是我會接下Google中國區總裁的重要原因。」李開復表示,他對自我的終極目標始終沒有改變,「把自己的影響力極大化」,但影響的層面與管道,卻隨著內心的聲音而開始延伸擴張。除了電腦領域的應用層面之外,李開復醒悟,自己所累積的思維、觀念、經驗,也正可對華人社會的青年學子帶來啟發意義,進而,能創造更多人才,讓世界更臻美好。
Google會是李開復的最後一站嗎?「我不敢肯定,至少,我現在沒有很大的欲望想去別處工作。不過,如果真有轉換跑道的可能,那麼,我多半會是轉戰教育界了。」
教育界!似乎,一枚異想的石子又投入了李開復的腦海,不過,這不會只是異想天開,李開復的書已寫成,教育者的形象正在醞釀,我們不必把李開復限制於狹隘的科技定位,「不只是我, 每個人都不必被旁人的眼光所限制,重要的是,多學習、多嘗試、創造更多機會,並且,跟著你的心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