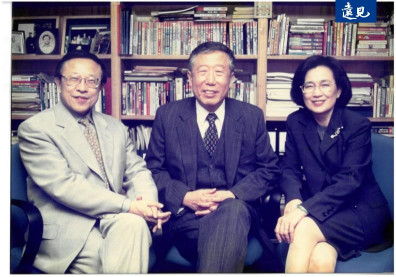誰是裴艷玲?據說是華人戲曲界的「裴帥」,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偶像明星,崇拜她的戲迷們,有的為她終日目瞪口呆,有的則是不知三月寒暑,只求追隨著裴帥戲班的腳步。她/ 他們說, 裴艷玲扮演的「鍾馗」,不僅出神入化,而且動人驚奇,根本是唱唸做打十項全能般難得的天王巨星。
看慣太多劇場中的真假扮演和好萊塢科幻動作電影的快節奏剪輯,很難教我再去相信或膜拜這種所謂「真人實境」的劇場傳說。「謠傳」了十二年,再如何有神功魅力的演員,總也敵不過歲月層層的堆積,總該是背也駝了,人也珠黃了吧?想想過去有幸面會過的中國大陸戲曲演員,許多經過「那個年代」的中年藝人們,儘管不像台灣演員對人生際遇來得那麼感嘆,但談話呼吸之間,總刻意壓抑自己的渴求,不敢張口大聲地要,都說:「認命了。」而現在,是戲曲復興的好日子,也是市場的壞時節,看戲的人就是少,難說自己還能撐上幾年。
超越年齡的劇場傳奇
然而, 裴艷玲看到的未來是:「欸!別看我是武生,我也會喜歡年輕的小生喲!」年近60的她,毫不掩飾地用成熟魅惑的眼神,打量著新一代的戲曲表演者。
別的老前輩打量後輩的時候,誰在放電?!
原來,她看別的演員的時候,也有戲迷的純真。對方那種「請前輩指導」的心情和情境,早被嚇退在她那般「我很想瞧瞧」的眼界之後了。
真的,被裴艷玲盯著的感覺,比被愛神的箭刺穿,還要叫人不知所措。雖然被盯著瞧的人不是我,但我真的親眼目睹一位年輕藝人在她面前那樣木訥的羞怯,真的叫我不可思議。
裴艷玲真的那麼「行」嗎?
說過了她是年近六旬,不過你若「有幸」能跟她面對面,她全身散發的能量和精力,也能讓你自然年輕。換個方式說──她曾經頂著她那頭短髮、穿著簡單的T恤短褲,在法國巴黎街頭騎著腳踏車,讓公園裡妓女流動車的馬夫把她當成年輕男子招呼。是的,說她已經快60歲,我也不可置信。
5歲登台、9歲擔綱主演,13、14歲的裴艷玲當年,早已隨著劇團走過大江南北。熟稔京劇、崑劇與河北梆子的她,即使經過文化大革命中輟了她的表演生命──那段時期她以擔任劇團字幕與道具的工作,自得其樂──她的表演藝術成就仍在90年代之後開始大放異彩。除了數度榮獲大陸戲曲界最高榮譽的梅花獎,裴艷玲也和百年前的梅蘭芳啟發了德國戲劇大師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一樣,對法國知名的太陽劇團和挪威、義大利的戲劇表演,有深遠的影響。
原來她是劇場傳奇的傳奇,但這不僅僅是裴艷玲而已。
文革也打壓不了的光芒
她能扮演花臉、老生和武生,跨越行當和劇種的侷限,出國教學的時候不靠翻譯,旅行度假的日子不用外語(可能她連打架都不用刀槍),台上、台下的生活都盡情運用她天生的表演能力。裴艷玲說:「我在國外的時候,日常生活缺什麼鹽糖醋茶和豬肉,我都能弄得來!」問她,那外國學生哪聽得懂串翻身、打旋和雲手呢?她回答,就是邊說邊做給他們看,大家自然就懂了。
這是比施魔法還要神奇的一種互動。
我問她:「為什麼文化大革命沒有把妳鬥垮?」當年那種人倫無常的悲劇,非但沒有壓抑了她表演的欲望,反而讓她更為「猖狂」。因為,聽說,即使上級派她去角落打字幕,怕她「搶了鋒頭」(或是要讓她難堪),散場叫好的戲迷,都是群聚在她身邊喝采,誇她「打字打得好」。然後,一次打壓不成,再派她坐到二樓,戲散了人還是往她二樓跑。
裴艷玲告訴我,那十年裡,不論是打字幕還是搬道具,她都要自己「樂在其中」。任何演出之前,都準備好一壺熱水熱茶,招待自己,大幕一拉,就緊緊地坐在舞台翼幕旁,不論負責哪幾場戲,都從頭到尾守在場邊。不像受不了屈辱之苦的那批戲曲演員,一個個哭瞎眼或上吊自殺,當年20歲左右、年輕的裴艷玲,享受沉潛,以閱讀西洋翻譯文學,幫助自己熬過黑暗孤苦的時間。
後來,她想了想說:「當年我不認命,可能是因為我比那些人都年輕吧?年輕的時候,不知道什麼是害怕。」所以,她硬是不讓自己順了敵人的意,再怎麼苦,都要過得開心。
說她是「活林沖」也好、「活武松」也罷,我心裡看見的是20歲的裴艷玲,早已超越了年齡的藩籬,那股熱愛藝術與生命的勁兒,讓我看懂了什麼是「年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