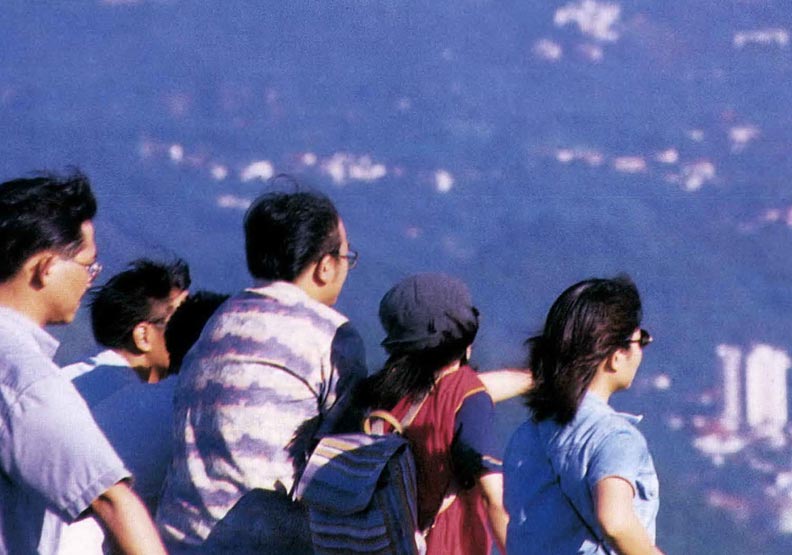西元五世紀中葉,中國出現長期對立的南北朝,但最後,為什麼是北方的隋統一大局。台大歷史系教授高明士在「族群關係與南北朝的分合」這篇文章中分析,當時南北雙方的社會,同時存在著複雜的族群(胡漢及少數民族)、階級(士庶)宗姓及僧俗的問題。但是,從文化、語言、戶籍,乃至通婚、用人政策上,北方的長安政權均較南方「開放」,例如周武帝五次下詔解放奴婢。高明士因此寫道:「北朝面對複雜的社會,他們總是在努力解決問題,這一點,南方是無法相比的。苟安、因循、疑忌,是南方長期以來的積弊,直至亡國。」「必須開創向心力的契機,有了向心力,族群融合才有可能。」高明士的這段文字,令人覺得若有所指。
今年,維也納建城100年。幾位世界頂尖男高音,將為此聚首獻唱。華燈水影,唯美靜穆的氣氛,難以想像半世紀前,這個觀光勝地曾陷於內戰烽火中。
奧匈帝國瓦解後,奧地利建國,但社會卻出現認同危機,一半以上的「奧地利人」,認為自己是日耳曼人。政治上也發展出以不同認同為標誌的兩大政黨,雙方互相批鬥,局勢尖銳而動盪,終於在1934年爆發內戰,血拚了四年,最後出現獨裁者收拾殘局。希特勒崛起後,奧地利又在納粹占領下,過了八年歲月。
戰後,奧地利宣布中立;在內部雖然人民對身分認同依舊紛歧,但兩大政黨決定合作,組成大聯合政府,推動「重建家園」運動;30年後,隨著政局、經濟上了軌道,國力增強,認同漸漸不是個話題。1950年代,一半人口自覺是日耳曼人;八0年代,已有八成的人覺得自己是奧地利人。
「他們見了棺材也掉了淚,」東吳大學政治系副教授游盈隆深為這段歷史感動,更心生警惕。他是民進黨「大和解」政策的堅定推動、支持者之一。他有感而發地說:「大和解,是要建立社會共同感情的基礎。」
想像2010年,鄧小平已死,兩岸代表展開多回合的談判,涉及台灣命脈的國家定位、政治體制,甚至資源互用、分配重大課題。那個時候,台灣社會是像1500年前的南朝,充滿「苟安、因循、疑忌」的氣氛,挑剔台灣代表的一言一行,懷疑他的動機;或是像本世紀的奧地利,因為「見了棺材,掉了淚」,內部凝聚了共同情感,化為向心力,成為談判代表堅強的後盾?
拉賓和阿拉法特握手言和了,但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心理衝擊,一時難以消化,即使遠在地球一邊的美國猶太人亦感同身受。
曾代表紐約時報採訪過李總統的傅利曼(Thomas Friedman),因以、阿問題的報導,得到美國最高新聞專業榮譽的普立茲獎。他是個猶太人,他也一向主張牌是在以色列手上,他們應主動解決以巴衝突。美國許多猶太社區常請他去演講,到最後,總是有不耐煩的猶太人發言:「你講這些有什麼用,阿拉伯人就是不喜歡我們,他要把我們全殺光。」
這時,傅利曼也總建議大家用整個肺的力量大叫:「阿拉伯人要把我們殺光。」然後他問,「這樣你會覺得舒服點嗎?你們要的是論證(make a point),我要的是改造(make a difference)。」
經過歷次選舉,幾次飛彈演習之後,基於族群不可能互「吃」的前提,這種務實、積極主動的改造精神,也慢慢在台灣嶄露鋒芒。
再走一趟高雄勞工公園,男女老少悠悠閒閒,前年九二五的群眾向新黨丟雞蛋、烏龍茶罐、冰磚,叫罵「中國豬滾回去」的音浪,好像從來沒發生過。
坐上台北艷黃色計程車,司機也許還熱中地下電台的叩應節目,可是再不會要乘客表態了。
表面上看,省市長、立委、總統大選的退潮,一併捲走大多數人的省籍糾結情緒,他們現在會理智地告訴媒體;「台灣沒有族群問題呀,日常生活都感覺不到啊,我的朋友什麼人都有……」。
但是,經歷過激烈的言語,肢體衝突洗禮後,台灣社會已經又跟三、四年前不同了。漸漸有一批人意識到,族群分歧雖然不似黑金、經濟成長問題那麼迫切,也不如塞車、污染那麼與民生習習相關,但它卻是台灣社會最核心的變數。尤其在面對大陸的挑戰時,台灣住民能否跳脫我族中心框架,是影響未來的一個關鍵。
尊重各自的認同
民進黨在這個月,將舉辦一次有關族群問題的研討會,新世代成員之一的田欣,為此寫了一份題綱,包括「族群問題是假問題(是唯心的投射與認同)」、「中國圖騰對外省人的意義(誰是台灣人)」、「沙文主義的意涵(什麼是台灣的)」、以及「戰鬥文藝與眷村文學都是台灣文學」等。這些簡略的筆記,充分反映民進黨新世代對族群問題的新思維。
這批政治新手普遍反對目前當權者的「新台灣人」說(凡是認同台灣的,就是台灣人)。他們認為所謂的認同,帶著強烈的攻擊性,因此主張,所有住在台灣的人,都是台灣人;而各族群之間,需要的是相互尊重各自的認同。
這個聲音透露出來的訊息,是接受多元化認同的價值,這樣的轉變毋寧是帶有戲劇化的效果。因為當族群分歧愈形尖銳時,「族群融合」立刻被端上檯面,因而又引發「誰融合誰」的敏感爭辯。這也正類似加拿大所走過的路。
儘管加拿大對愛斯基摩人的少數民族政策,贏得不少世人的肯定,但英裔和法裔的隔膜,卻周期性高潮低盪地反覆著。經過長年的辯論、司法判決的示範,加拿大目前正興起多元文化主義風潮。中研院中山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錢永祥,就對這股十萬八千里外的論述感興趣,正著手翻譯一本相關的著作。「族群差異是個優點,不要害怕不同。」身為蒙古人,錢永祥對族群問題有異於一般人的敏感。
他曾無意間翻閱他早逝父親的手記,發現裡面一句話:「同意合理的共榮,反對強制的同化」。這句話大約也成了錢永祥的信念;雖然目前學術界對於加拿大、紐西蘭等國家,為什麼可以發展出多元主義的理論,甚至形成政策,並無定論;但錢永祥指出,世界上多種族國家非常多,巴爾幹半島、以色列等地之所以還沒有發展到這個地步,恐怕跟生活條件脫不了關係。他表示,當資源相對(人口)豐厚,生存不是那麼迫切的時候,社會就比較有包容的空間。這似乎也暗示,台灣在族群問題上,是比過去有條件了。
就在李總統發表就職演說前夕,台北社教館一連三天公演「紅旗.白旗.阿罩霧」的閩南語舞台劇。這齣長達三小時、以霧峰林家起落為藍本的歷史劇,試圖揭露台灣先民開墾土地的真實,為了爭水源、搶地盤,宗祠、氏姓對內、對外慘烈地尋仇血鬥,及官家在矛盾中扮演的挑撥、運作角色;也表現許多大姓當時一時「紅」(反清)、一時白(護清),搖擺不定的投機與無奈(宗親血緣才是舉何色旗子的關鍵,非意識形態)。
聯宗結社,競奪資源,是移民社會的本質之一,從某個角度看,族群衝突,在過去可能不是個「問題」,而是爭取最大生存空間的儀式。
隨著遊戲規則改變,數人頭取代打人頭,台灣社會漢人之間,早已不是生存資源搶奪的問題;即使是僅有三十六萬的原住民,也開始有人呼籲,他們要的不是同情,是尊重;不必把他們看成弱勢團體,給予「福利政策」式的保障,他們寧願漢人看待他們如兩千一百萬裡的一分子。
面對21世紀,一如許多人的觀察,隨著政治、經濟各方面的多元發展,台灣的省籍情結,的確有淡化可能,尤其是在新、新新人類身上。但是,民進黨文宣部副主任王時思提醒,這也不表示掌握主流的人不做任何事,這個分裂上一代、困擾這一代的衝擊,不會換成另一個形態(統獨、階級優越感),影響下一代。
何時「出頭天」?
回顧族群優越/自卑感、刻板印象的形成(硬頸客家人、愛喝酒的原住民),有歷史條件,也有政策推波助瀾的因素存在;就政策而言,教育內容和語言,恐怕是當政主事者必須正視的首要改造工程。
仔細聽聽許多人不愉快的族群經驗不難發現,憤懣的情緒,大都源自被壓抑的自卑感。過去在單一價值、單一認同的教化下,十幾個不同文化根源的原住民變成只有一個族,講台灣國語會給人「沒水準」的印象。這也造成「吃台灣米四十年,還不會說台灣話」,成了福佬人(一稱河洛人)反彈初期最理所當然的控訴,也成了外省人(尤其是第二代)的原罪。
這似乎也說明,雖然政壇上芋仔已變成番薯,雖然介壽路改了一個不知有多少人背得出來的凱達格蘭大道;這些改變似乎只凸顯外省人的不安全感,卻絲毫末提升原住民,客家人和福佬人的自尊感,對許多和權力沾不上邊的人而言,他們更沒有「出頭天」的驕傲。
如果說族群問題是刻意被挑起的,它的釐清,無疑也需要一番刻意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