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裁蠻橫統治烏克蘭的維克多.亞努科維奇意外下台,使普丁得以實行懷藏心中已久的大膽計畫──併吞克里米亞。亞努科維奇下台,就跟普丁對一九九九年莫斯科住宅區炸彈事件的反應類似,製造出神奇的「短路效果」。普丁因此成為改寫後蘇聯歷史的人物,帶著勝利返回自一九九一年失去一肢後,幻肢痛從未平復的國家。貪腐,這僅僅兩年前的主流議題,頓時失色。
普丁的支持度從百分之六十躍升至百分之八十。許多數年前反對普丁的俄國富人,如今改站在他那一邊。象徵性的國家勝利,撫慰了未實現的個人成就期望。併吞克里米亞是現代化的代替品。人們獲得目標,而且無需為此出半分力。僅百分之三的俄國人不同意併吞行為。克里米亞久為俄羅斯帝國鄉愁的核心所在,自蘇聯末日以來,併吞克里米亞一直是俄羅斯國族主義者的執念。現在他們歡慶自己的想法獲得勝利。
二○一四年三月十八日,普丁置身克里姆林宮的金色聖喬治廳宣告併吞克里米亞,他幾乎逐字複述了二十年前國族主義報紙《每日報》上刊載的文字,作者是俄羅斯國族主義的其中一位思想家伊果.夏法維奇。
「克里米亞的一切事物都在訴說我們共有的歷史和驕傲。古老的克爾森斯位於此,即弗拉基米爾大公的受洗地……使克里米亞歸於俄羅斯帝國的英勇俄國軍士,他們的埋骨地也在克里米亞。」在克里米亞受洗的是弗拉基米爾大公,而使此事蹟重回俄國歷史皺摺的是弗拉基米爾總統。在一九九三年十月,俄羅斯國族主義者企圖襲擊奧斯坦基諾電視中心,把他們的理念播送出去。如今是由俄羅斯總統來陳述這些理念,透過所有的重要電視頻道播送,而且沒有一顆子彈為此發射。
事實上,根本很少有俄國人知道弗拉基米爾大公是在克里米亞受洗。對他們而言,克里米亞半島連結的是享樂,而非宗教信仰。那是度假、夏日羅曼戀情、國家療養院和夏日別墅的所在地,可是為了使併吞看似合法,普丁必須將基督教的神話附加其上。併吞克里米亞真正的象徵意義是普丁反轉了歷史進程,使俄國人重獲昔日帝國光榮──國族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僅能對此心懷夢想。
然而,一九九○年代初期建立的紅棕同盟已歷經轉變。一路走來,共產主義者遭到捨棄。撰寫遭人撻伐投書〈我不能放棄原則〉的妮娜.安卓娃,如今住在鄰近聖彼得堡大小有如鞋盒的套房裡,研讀列寧著作和全聯盟共產黨布爾什維克(All Union Communist Party of the Bolsheviks)中央委員會的「命令」──她跟其他幾位退休人士組成的政黨。率領眾人包圍奧斯坦基諾的老共產黨員維克多.安皮洛夫,落腳於莫斯科外圍的一間地下室,此處散發體味與發酸高麗菜混雜的惡臭,牆邊擺滿史達林肖像和蘇聯舊旗幟。
二○一三年興起的新結盟是由國族主義者和「騙子小偷」黨所建立。以出奇手法併吞克里米亞後,他們的同盟關係更加鞏固。一九九○年代亞歷山大.涅夫佐洛夫率先在電視上實驗俄羅斯法西斯主義,表現出高超技巧,隨後對此思想逐漸「幻滅」。這次連涅夫佐洛夫都為併吞克里米亞感到難堪:「如果克里米亞是從強盛、富裕且勇猛的國家手中拿回,那會是一場高尚且實在的勝利。然而奪取的對象是受傷、流血、失去行動能力的國家,那等同於掠奪。」他寫道。不過,正是涅夫佐洛夫於一九八○年代採用的電視手法,使俄國得以不經一戰就占領克里米亞。
實際事件根據電視創造的劇本開展,情節大致如下:烏克蘭革命將使美國支持的新納粹掌權。二戰期間希特勒同路人的後代子孫,如今蓄意破壞蘇聯時期的戰爭紀念碑,並威脅要徹底抹消克里米亞的俄羅斯語言及歷史。克里米亞的俄羅斯人向普丁求助,而他依照人民請求伸出援手。劇本於二月二十七日啟動後,俄軍在數小時內占領機場、政府建築物和廣播設施,封鎖烏克蘭軍隊基地,並在烏克蘭政府中安插傀儡。
俄國士兵被描述成解放者而非占領者。上傳至網路的影片顯示,克里米亞的俄國士兵臂彎裡抱著一個幼兒──參照了一九四九年豎立於柏林的巨大蘇維埃解放軍雕像。影片也拍攝俄軍黑海艦隊停泊的希巴斯托普,當地人正在慶祝獲得解放。只欠缺一件事:敵人。
軍隊完成部署之際,弗拉基斯拉夫.瑟科夫統籌協調莫斯科的公關團隊,把克里米亞當地的騙子和歹徒,變身成「爭取自由的政府」。其中一位公關人員是亞歷山大.波拉戴(Alexander Borodai);波拉戴是一位正統國族主義哲學家的兒子,曾於一九九三年加入反對葉爾欽的國族主義者陣營,當時他正在莫斯科國立大學讀哲學。波拉戴對於極右派國族主義者的思想特別感興趣,這群人在布爾什維克革命後逃出俄國,深深同情(且影響了)在歐洲興起的法西斯主義。
在一九九二年,時年十九歲的波拉戴前往外涅斯特里亞參戰,捍衛俄羅斯人對抗摩爾多瓦「法西斯主義者」,且於一年後現身莫斯科白宮。據稱他在一九九三年十月率領二十幾個武裝人士,參與包圍奧斯坦基諾電視中心。設法自奧斯坦基諾安然逃脫後,波拉戴繼續學業,並供稿給國族主義報紙《明日報》(Zavtra)。但是他的賺錢方式是提供私人石油公司諮詢,包括本地和國外企業。在他身上體現了「騙子小偷」黨與國族主義者結盟的縮影。普丁認為自己在利用國族主義者,國族主義者則深信是他們在利用普丁。克里米亞只是個開端。俄羅斯也計劃在烏克蘭東部劃出一塊領地,藉以阻止烏克蘭偏向歐洲和西方。
波拉戴的職責是激化東烏克蘭頓巴斯(Donbass)地區的情勢,期望引發連鎖反應,使烏克蘭東部興起分離主義。他們稱之為「俄羅斯之春」,拿來比擬阿拉伯之春。普丁提倡「俄羅斯世界」(Russian World)與新俄羅斯(Novorossiya)的概念,那是用來指稱俄羅斯帝國南部的歷史詞彙,地域囊括現代烏克蘭的領土,如敖德薩。儘管很諷刺的,區域首府頓巴斯不在上述範圍內。為了實現新俄羅斯,俄國在頓巴斯投入金錢、武器和專事煽動的特務人員,協助一幫無紀律的惡棍、機會主義者和失業者占領當地行政機關。這些地方很快就變得失序且散發臭味,看起來比較像遭擅自占用的房屋,而不是革命總部。
儘管頓巴斯在悶燒,卻未冒出火焰。為了放一把大火,需要汽油和火種的慨然相助。輪到波拉戴的舊識伊果.捷金(Igor Girkin)上場,他在併吞行動不久前去了克里米亞。捷金化名為史特爾科夫(Strelkov,俄文的意思是槍手),一九九○年代初期首度於外涅斯特里亞參戰,接著是波士尼亞(加入塞爾維亞軍陣營),最後到了車臣,負責讓好幾位遭指控的反叛分子「消失」(受到祕密處決)。史特爾科夫宣稱自己替俄羅斯國安機構工作,然而更重要的是他對重建過往戰爭的熱忱。畢業自歷史檔案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Archives),他跟一群狂熱者喜好穿上古裝,以演戲的方式重現著名戰役。史特爾科夫尤其熱衷於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二年間的俄國內戰,演這場戰爭時他會打扮成白軍官員??。他最近一齣軍事史遊戲的劇本,內容在描述一九二○年烏克蘭西南部俄羅斯志願軍的行動。二○一四年夏天,史特爾科夫有機會用真槍實彈重現俄國內戰。
史特爾科夫跟俄軍支持的一隊人馬,在二○一四年四月襲擊烏克蘭東部的城鎮斯里維揚斯克(Slavyansk)。首先他們占領電視訊號發送站。烏克蘭的電視頻道遭到停播,被俄羅斯國營頻道取代。在短短幾天內,此地區發生激烈交戰。
要不是俄國電視的關係,這場戰爭可能不會開打。將電視稱為武器的說法喪失其隱喻意義。電視正是造成實際破壞的真正武器。
戰爭曾經在電視上播出過。但是電視和政治宣傳從未成為指揮戰爭和奪取領土的主要手段。軍隊的角色是影像的輔助。俄國媒體不僅扭曲了真實,他們發明真實,手段包括採用假影片、竄改引述內容、僱用演員(有時同一位演員會在不同頻道分別扮演受害人和侵略者)。「以我們當前的心理狀態來看,只有採用藝術形式才能解釋(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恩斯特曾說。
二○一四年七月十二日,第一頻道「訪問」一位身懷揪心故事的烏克蘭女子。受訪女子說她目睹三歲男孩遭公開處決,烏克蘭軍奪回斯里維揚斯克大廣場後,那件憾事就發生在擠滿人的廣場上。她敘述暴力犯行的細節:那些烏克蘭「畜牲」,二戰法西斯分子同夥的後代,凌遲小男孩的肉體,折磨一小時後他才斷氣。女子補充說明,男孩的母親被綁在一輛坦克車上拖行至死。這件事是假的。藉由虛構孩童被烏克蘭人處死或施刑的事件,俄國政治宣傳採用歷來有效的仇恨激發機制,與俄國革命前屠殺猶太人??時用的是同一套方法。
俄國電視台的作用就像是精神藥品,像某種迷幻藥。如同涅夫佐洛夫所寫:「愛國的幻覺既激進、歇斯底里且持久……人們必須謹記,(愛國主義的)意識型態藥物只為了一個重要目的注入國家血液:只要有軍階的任何一個傻瓜彈一下手指頭,成群男孩就會自願獻身變成焦炭或腐肉。」
俄國發動資訊戰爭的目的不是要說服誰相信俄國觀點,而是要引起爭戰,並使平民百姓捲入衝突,而資訊戰確實達成了上述目的。參戰者之中有很多失業人士和遭褫奪公權者,有些原來在非法煤礦賺取微薄工資,還有許多前蘇聯士兵,他們在蘇聯解體時感到被蘇維埃祖國拋棄。俄國電視台利用這群人的弱點,引誘他們為近四分之一個世紀前就不存在的國家上戰場。俄國的「多重戰爭」把他們從悲慘、沒沒無名、失去希望的存在,提升成電視螢幕上的人物;對他們說你既是受害者也是英雄,供應武器讓他們去對付敵人。俄國政治宣傳也動員了數千名俄羅斯志願人士蜂擁而至,參與對抗烏克蘭「法西斯主義」的血腥戰役。
俄國政治宣傳的產製者不受「俄羅斯世界」或重建帝國的思想所驅使,他們太務實了,不會相信那些說法。他們採取行動並非出於信念或真實,而是蔑視信念與真實。他們塑造的幻象擁有了自己的生命,開始不按劇本演出,渾然不覺自身僅是電視節目的一部分。男孩遭處決事件播出五天後,俄羅斯支持的分離主義者擊落馬來西亞航空MH17班機,使飛機上的二百九十八人全數送命。
然而對大多數俄國人來說,烏克蘭戰爭只是電視上的一場秀。在二○一四年的大部分日子裡,新聞節目常延長成兩倍時間,講的全都是烏克蘭議題,彷彿俄國人的生活被凍結靜止。這場戰爭成為每集一小時的「連播」,內容充滿血腥、暴力和懸疑。新聞節目採用電影手法和特效:片段剪輯、富戲劇效果的回顧、影像拼貼和配樂。電視頻道販售自行排演的戰爭戲劇場面,競相追逐最多的收視占比(及廣告市場)。在俄國歷史上,新聞節目第一次持續排在收視排行榜首位,擊敗肥皂劇和影集。一如既往,第一頻道及其《時間》節目跑在最前頭。
對俄國觀眾來說,看這場秀幾乎不需代價。西方對俄羅斯施加的制裁並未影響多數人口,至少剛開始沒有。而派往烏克蘭打仗的俄國士兵死亡消息,遭到悉心掩飾隱瞞。戰爭秀的人氣轉為普丁的支持度,推升至近百分之九十。但是這也暗示戰爭秀一結束,支持度就會下降。因此動員成了普丁唯一可用的資源。
為了維繫觀眾的注意力,情節必須推進以塑造新的虛擬敵人,提升侵略與仇恨層級。戰爭敘事如今已超越烏克蘭,升級成跟泛西方開戰。宣稱俄國是在跟美國和西方打仗的說法,深植俄國普羅大眾心中。抗議戰爭的人被貼上國家叛徒的標籤,說成是西方資助的法西斯主義同路人。
所有的電視頻道都攻擊自由主義者,不過NTV的抨擊尤其狂烈,或許是為了補償或報復自身過去的作為。常成為攻擊目標的其中一人是鮑里斯.涅姆佐夫,此人曾代表俄國有希望變得正常、文明,且最重要的是成為一個自由的國家,而NTV理應是參與其中的推手。二○一四年五月,國家的狀態使涅姆佐夫滿心絕望:
我想不起何時有過莫斯科當今的普遍仇恨程度。一九九一年沒有,當時是八月政變,甚至一九九三年也不曾如此。電視煽動攻擊和殘暴行為,由略顯瘋魔的克里姆林宮主子提供關鍵定義。「國家叛徒」、「第五縱隊」、「法西斯軍政府」,這些詞彙全都來自克里姆林宮的同一間辦公室……克里姆林宮在餵養與鼓勵人們最低劣的本能,激發仇恨和鬥爭。人們彼此對付。這樣的地獄不可能和平收場。
不到一年後,涅姆佐夫在克里姆林宮附近遭到射殺身亡。涅姆佐夫被謀殺後,《商業人》的創辦者弗拉基米爾.亞可夫列夫對所有媒體工作者發表公開懇求。他不僅以自己的身分發言,還提及他的父親葉戈.亞可夫列夫。「停止教育人民如何去恨,因為仇恨已經把這個國家撕裂。人們活在瘋狂的幻覺裡,認為國家受到敵人包圍。男孩們在戰爭中送命,政治人物在克里姆林宮牆邊被處死。瀕臨社會災難邊緣的不是歐洲和美國。資訊戰首先摧毀的是我們自身。」
電視畫面的作用有如藥物,創造一種亢奮感,摧毀判斷力和智慧,降低道德標準並抑制顧慮與恐懼。把這些藥物注入國家血液的人使俄國蒙受重大傷害,那不是任何敵人所能辦到。
大多數俄國人如今認真思考跟美國打核子戰爭的可能性,百分之四十的年輕人相信俄國打得贏,彷彿那是玩家擁有備用生命的電動遊戲。鮮少俄國人準備為此付出生命或承受苦痛代價。
就像任何毒品買賣的情境,電視政治宣傳是在利用人們的弱點和渴望。俄國政治宣傳產生作用的主因,在於想要相信宣傳內容的人數充足。希冀如此的人大多既不貧窮也不無知,相反地,他們富有且資訊充分。人們蒙受欺瞞,是因為他們想要受騙。民意調查顯示,近半數俄國人知道克里姆林宮對世人撒謊,表示烏克蘭沒有俄國軍隊存在。但是他們默許這些謊言,且視為力量的展現。超過半數的人認為媒體為了國家利益而扭曲資訊是正確的事。
政治宣傳依附的主要對象不是無知,而是憎恨──嫉妒和敵意的混雜物。把美國當成想像中的強大敵人,使人們感覺崇高自滿;這補償了個人的軟弱與失敗,使人們不再需要向他人證明自我,更重要的是,不再需要向自己證明自我。俄羅斯的作為是在甘冒過量服用仇恨與攻擊心的風險。亢奮和國族主義狂熱不像電視機可以說關就關,能量不會憑空消失。歷史不能像卡帶般倒轉,俄國曾有過的抉擇無法重選。但是未來也還沒預先論定。
俄羅斯歷史的唯一共同特徵是不可預測性。見證蘇維埃帝國崩解的葉戈.蓋達曾說,重大改變來得比我們想像中晚,卻比我們預期得早。普丁在烏克蘭打的仗,槍口瞄準著現代性和未來。那場戰爭喚醒的力量並非帝國擴張(俄國不具備創建帝國所需的力量或視野),而是混亂和失序的力量。這股力量可能將導致國家沉入黑暗深淵,或是俄羅斯可能會擺脫掉後帝國症狀,以民族國家之姿再起。但是歷史並無自我意志,俄羅斯要變成什麼樣的國土,端視接手發明創建它的下一代人決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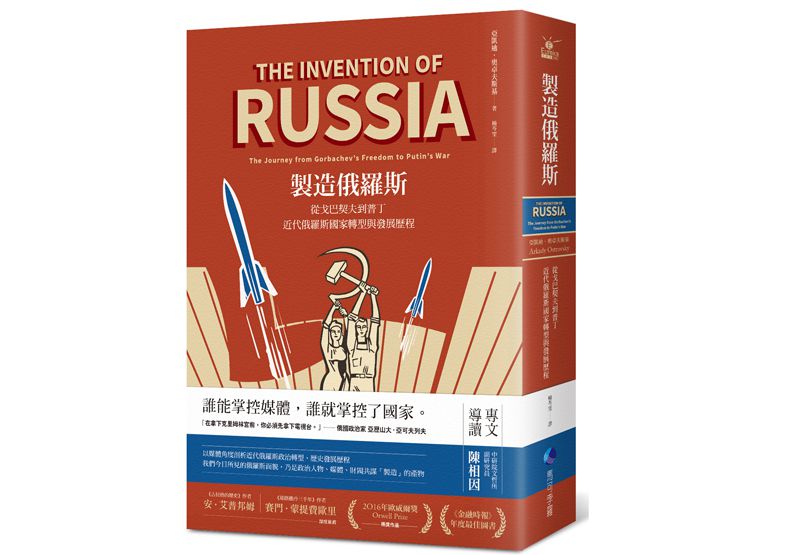
本文節錄自:《製造俄羅斯》一書,薇兒.亞凱迪.奧卓夫斯基(Arkady Ostrovsky)著,楊芩雯譯,馬可孛羅出版。
(圖片來源:kremlin.r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