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與社會學義合聘教授 唐文慧)
一位男性朋友告訴我:「如果你沒當爸爸,就不能算是男人;如果你不是好爸爸,也不能算是好男人。」我思索這句話背後的涵義,其實說明了這位中產階級的男性對「當爸爸」這件事情的高度認同,更期待自己能成為「好爸爸」,因為這與他的性別角色扮演與身分認同有著密切的關聯。然而,我不禁好奇,哪些男性能夠成為社會大眾公認的好爸爸,甚至成為政府表揚的「模範父親」呢?台灣社會對理想父親角色的期待與想像究竟為何?
好爸爸的典範轉移
大約五十年前,政府開始進行所謂的「模範父親」表揚。在一則新聞報導中指出,舉辦模範父親選拔的目的是為了「改良社會風氣復興中華文化,恢復我國固有倫理道德」,而參加模範父親選拔的條件是:「五十歲以上,思想純正,有子女四人以上,並注重家庭教育的父親,平時熱心公益又能敦親睦鄰,教育子女有成,且身心健康無不良嗜好。」(《中國時報》一九六八年七月八日)
看完這則新聞,相信大家都會莞爾一笑,一來當代家庭有四個孩子以上的應該很少吧,再者,模範父親為何與「恢復道德倫理」有關?五十年前的那個時代,好爸爸比較是一種「公共型」的角色,必須熱心參與公共事務,子女也得有一定的教育成就,這樣的父親才能成為社會認可的好爸爸。這與模範母親的邏輯相當類似,許多事業有成的男性,他們的母親經常成為政府表揚的「模範母親」,因為有成就的子女才能榮耀父母。因此,好爸爸與好媽媽一樣,經常都是「以子為貴」。然而歷經時代變遷,好爸爸有新的面貌了嗎?我發現,當代好爸爸的定義也開始要讓另一半感到滿意才行,男性面臨公私角色衝突的問題也開始浮現。大約在二十年前,有則新聞是這麼說的:
當選今年台南市模範父親的北區東興里里長吳錦明,有個得獎專家的封號。這次得獎太座蔡阿桂的評語是:當好爸爸是實至名歸,但不見得是好老公。因為老公太過於急公好義,自己家的事總是擺在最後,所以當太太的就得辛苦些。(《中國時報》一九九三年八月八日)
這位模範父親是里長,熱心公益不在話下,但是從太太的角度出發,丈夫把家事放在最後面,卻讓她非常辛苦。太太雖然肯定丈夫是好爸爸,但是話中還帶著一絲遺憾!可見,好爸爸角色開始從公共型轉到兼具家庭關係的面向,換言之,好爸爸也要家庭與事業平衡才行。時間又過了二十年,再看一下最近兩則新聞,一個是修紗窗的爸爸,一個是賣雞排的爸爸。這兩則新聞大幅改寫了社會大眾對好爸爸的像與期待,既沒有提到孩子的學業成就,也不強調父親的公共角色,重點反而是照顧幼兒與體貼太太的家庭面向,甚至是擔負起育兒的重任,這則新聞是這麼說的:
台南市最近出現一位身揹嬰兒、在街頭幫人修紗窗紗門的年輕男子,大家對他總是揹著孩子工作很好奇,一問之下才知他是個疼某的新好男人。因為老婆正忙於研究所實習課業,白天無暇顧嬰兒,他當起超級奶爸,餵奶、換尿布全包辦,不少民眾紛紛按讚還熱心幫忙介紹工作⋯⋯熱愛運動的陳建任渾身肌肉,他揹兒子在貨車旁修紗窗的身影,被網友拍照上傳臉書,不斷被轉載,稱讚他是新一代好男人,妻子也大讚老公「足感心」。(《中國時報》二○一五年五月一日)
有網友在臉書社團「嘉義市大小事」分享一張爸爸揹著兒子賣雞排的照片,直呼:「現在社會上越來越多父親讓人欽佩。」網友恩布魯表示,他經過嘉義市東門圓環這間雞排店時,偶爾會看到老闆揹著未滿一歲的兒子炸雞排,經詢問得知,小嬰兒的母親從事新娘祕書的作,無法把孩子帶在身邊,因此他才揹著孩子工作。許多網友看過紛紛表示:「好爸爸!」「原來不只台南有,嘉義也有喔!」還有網友讚賞:「這才是男人!」「認真的男人最帥!」(三立新聞網二○一五年五月二日)
以上這兩則新聞中的「好爸爸」都是勞工階級父親,並不強調他們急公好義或敦親睦鄰的形象,也不著重他們教育子女或以子為榮的面向,反而是強調他們「照顧幼小子女」與「幫助太太完成學業」,其中的轉變主要從公領域的男性角色轉變為私領域的家務分工,與較為平等的夫妻性別關係。此外,現在市面上更出現「野戰風格」的嬰兒背巾和爸爸包等育兒商品,這些都是好父親形象轉變的重大指標。對幼小子女身體的照顧與強調親子的親密關係,成為這個新時代的父職特色。
好爸爸形象認同的階級差異
除了世代,其實誰能成為社會大眾稱許的好爸爸還有階級的差異。每次見到住在漁村的阿榮,他總是嚼著檳榔,並不免夾帶幾句髒話來表達他對這個社會的不滿,特別是工頭對他的苛刻要求。阿榮不到三十歲,已有兩個上小學的孩子。這位年輕爸爸給我的第一印象是熱情、愛交朋友。因為家境貧窮不喜歡讀書,國中就輟學打工,雖然中文的聽和說沒有問題,讀寫卻有障礙。他學歷不高,在鐵工廠作工,月收入少則三萬,若加班更多。太太也工作,家庭經濟還算不錯,且夫妻的工時是正常的早八晚五。雖然工人的體力勞動累了一點,但能賺錢養家,他覺得自己的日子過得實實在在。他最喜歡說的一句話:「哼,大學生?還不是廿二K!」阿榮的太太阿蒂是從越南來台灣工作的外籍看護,後來認識阿榮才結婚,夫妻感情融洽,一家和樂融融。
阿榮的父職表現,是現代和傳統的交織,加上一點個人色彩。他對於孩子的課業沒有過多要求,這或許也是孩子和他相處沒有壓力的原因之一,每次我看到他與孩子在一起總是融洽自然,不小心會誤以為他們是兄弟或朋友。由於平日下班得早,又有固定週休二日,阿榮常常能和孩子一起玩手機遊戲,也和孩子分享網路有趣的影片,幾乎每天在臉書公開家庭生活的點滴,假日會帶著太太與孩子出遊。
然而,阿榮有時也會以較為權威的姿態來管教孩子,像是罰孩子半蹲來進行道德管教。其中最具個人特色的,還是操持著髒話的表達方式,一生氣就是「幹,XXX,你再這樣,我要揍下去了」,接著便出手朝兒子頭上揮過去。他的言語動作經常讓外人目瞪口呆,但過了一會,你又會看到他跟女兒、太太摟摟抱抱,跟兒子稱兄道弟的畫面,久了我也習慣了他們一家人的互動模式。朋友或太太經常會糾正他的三字經,也告訴他不能體罰孩子,但不可否認,不論在陪伴孩子或是經濟供應,他的照顧與養家角色都可說達到了標準,旁人若還要批評他,似乎就顯得太苛刻。
當今社會對「真男人」的定義已與現代性的父職高度相連。搜尋二○一五年模範父親選拔活動,結果發現,與前兩個世代不同的是,有越來越多不同類型、族群、階級的父親逐漸被看見,如新竹市社會處的選拔,就將模範父親代表分為六類,為「家庭照顧、力爭上游、新移民、原住民、自強、另類與熱力爸爸」(《自由時報》二○一五年七月十八日)。雖然這些選拔的標準仍意圖塑造公領域的社會標竿,但與過去相比,弱勢家庭的父親開始被看見,象徵著好爸爸不僅只有中產階級傳統的那一套文化腳本。
而相較於公部門的選拔,NGO的兒福組織則持續訴求回到私領域來進行父職意義的探討,他們多深切期待男性做個高度參與家庭的「好爸爸」。例如在「二○一五年父子互動關係調查報告」中,針對國小五、六年級及國中七、八年級的學生進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台灣父子互動關係狀況出現三大警訊,即「不多話、晚回家、常神隱」,更有高達五成四的孩子一天與父親聊天不到半小時,甚至四分之一的孩子和父親共進晚餐的頻率不到一週三天等(《聯合報》二○一五年八月五日),因此批判這些「缺席的父親」,意味著他們不是「好爸爸」。此外,還有民眾組成社區關懷協會,該協會祕書長指出,台灣已經進入「無父的世代」,他認為現代父親多忙著工作賺錢,因而錯過孩子的成長及與妻子的溝通。他鼓勵父親扮演正向角色,凝聚家庭力量、給孩子安全感,因此號召志工父親成立「好爸爸聯盟」,藉此推動爸爸愛家的活動(《聯合報》二○一五年八月六日)。
然而,我們也發現,爸爸對孩子的照顧可從質與量兩方面來觀察,也可從身體照顧與心理的支持來探討。根據二○一五年父子互動關係調查報告指出:「父子除了相處時間不多,互動品質也差強人意。當問到孩子最常和父親一起做的事,超過六成是吃飯(六十三.二%)和看電視(六十一.四%),甚至一起玩3C產品的也有近兩成二(廿一.七%),然而和父親一起運動的比率卻只有一成九(十八.八%)。」結論中並認為:「現代爸爸似乎還是難以完全擺脫傳統父親忙於工作、不善表達的形象。」從以上的調查我們發現,社會期待父親除了跟孩子在一起,也要注意在一起時所進行的活動內容與互動品質,並強調運動健身的活動是較被認可的,但這也可能與都市生活的活動空間不足有關。此外,不同工作性質的父親會有不同的父職實踐,例如忙碌的中上階級父親可能可以提供較好的物質、較好的金錢,且多半會強調照顧子女的重點是品質,例如心理的支持,而不是時間的長短。
誰能成為「好爸爸」聯盟的成員呢?或許我們會認為就是那些有錢有閒的中上階級父親,但現在台灣社會的中產階級,很多也陷入以長工時來換取工資的景況。許多白領階級的家庭都經歷著假性單親,反倒是上述案例中勞工階級的阿榮能陪伴子女成長。經濟弱勢家庭在扮演父職過程中可能面臨的困難與掙扎,也都出現在白領階級家庭。
從政府與NGO的倡議來看,兩者各針對不同的面向來判定何謂「好爸爸」,但也需避免落入盲點。例如政府的選拔雖注意到多元的父職型態,但忽略了「世代」差異,且大多依然企圖形塑特定的父職典範。在NGO方面,雖然要求回到家庭私領域來塑造理想的父,但卻忽略階級的面向,忽略家庭的型態差異,也看不見經濟弱勢家庭的父親在扮演父職過程可能面臨的困難與掙扎。
「缺席的父親」在過去被大量討論,通常批判父親將養家的經濟角色放置在第一順位,缺乏照顧的角色,然而這樣的批判卻忽略了勞動階級父親的無能為力。我們不能僅僅以「都會區」、「高教育程度」、「白領工作」的父親作為理想父職的典範,我不能簡化父親在不同世代與區域脈絡中所展現的複雜圖像與型態,在討論誰是「好爸爸」時,也不能不看見世代與階級是時常被忽略或刻意迴避的重要面向,那些其實都是形塑與影響父職實踐差異的重大因素。
所謂「好爸爸」的理想父職圖像會因地域和世代而異,且正如學者霍布森(John MontaguHobson)抱持「社會建構論」的觀點,男人會成為父親是「做成的」(making men intofathers),而不是「生成的」。強調父親角色是鑲嵌在社會文化與制度脈絡當中運作的結果,除了個人意願和選擇的偏好,社會文化與制度往往影響父親的樣貌,也定義何謂稱職的「好爸爸」。我們不應忽略不同時代與階級地位的男性對於當爸爸這件事會有不同的想像與實作如果一個社會多數的男性都期待自己成為受人讚揚的「好爸爸」,是否正如「好媽媽」的迷思一樣,應該更仔細地被檢視與反思,究竟成為好爸爸的個人和社會條件是什麼?為什麼相較之下有些人似乎輕而易舉就可以成為好爸爸,而有些人雖窮盡心力努力朝向這樣的目標,仍然遙不可及。我們鼓勵大家成為好爸爸,卻也不能忽視社會文化如何定義好爸爸,以及個人和社會條件的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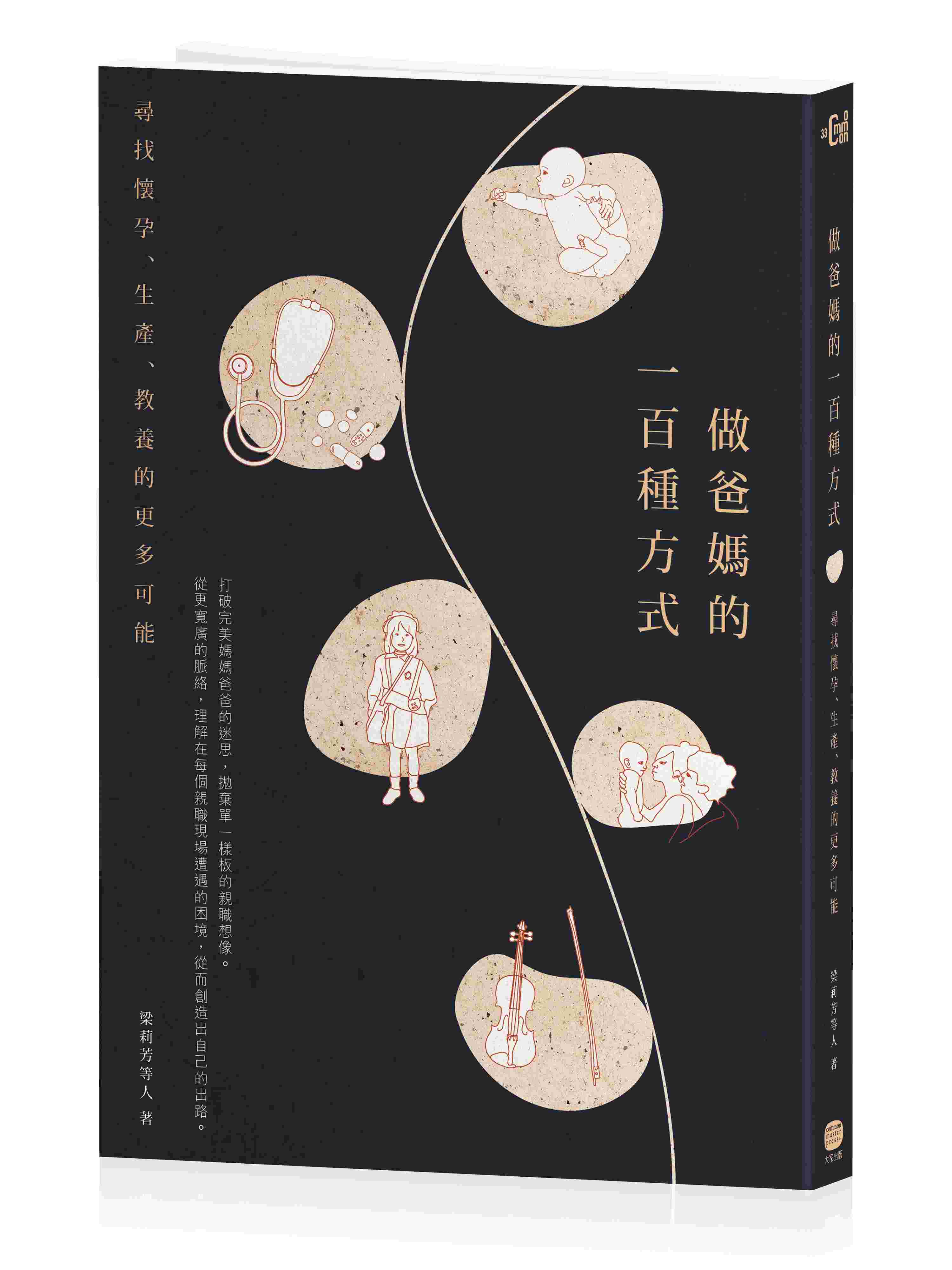
繪者:蔡芳琪
本文節錄自:《做爸媽的一百種方式:尋找懷孕、生產、教養的更多可能》一書,梁莉芳/等著,大家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