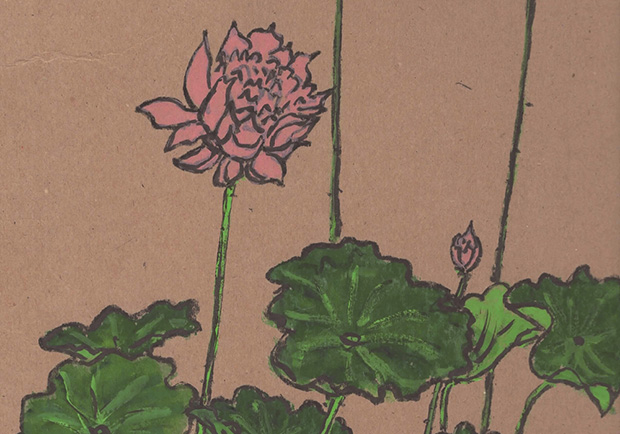小學二年級時,平生第一次被指派參與朗讀比賽。因為得失心太重,緊張到吃不下飯,比賽的前幾天,我跑去跟老師表明自己一想到上臺就雙腿發抖,顯然無法勝任,請她陣前換將。老師微笑著拍拍我的肩膀對我說:「不用緊張,老師選派你就是知道你可以的,要有信心,不管輸贏,盡力就行。」那回,我帶著老師的信任上場,得了第二名。從那以後的幾十年,我參與無數的比賽,雖然每回都還不免忐忑,但逐漸明白所有人生的競賽都必然有輸有贏,不必太過計較,真的只要盡力就行。
初中時,貪看課外書,不知在哪個環節出了差錯,數學由是一敗塗地,高中聯考慘遭滑鐵盧。我惶惶終日,不知如何是好。幸賴二次聯招,才進了郊區高中。其後,輾轉才又轉學回到臺中女中。雖然不敢再掉以輕心,但大學聯考時的一場高燒,竟讓我在考場上睡了一大覺,又和公立大學錯身而過,只好懷抱著抑鬱的心情奔赴外雙溪。
大三那年,我代表東吳大學參與「全國編輯人研習會」,和全國大專院校的校刊主編相互切磋編輯知識,居然得到當時《幼獅文藝》主編詩人弦的青睞,從眾多才俊中脫穎而出,被挑選成為雜誌的兼任編輯。主編約見時,我惶惑不安,自卑出身私校,怎可能打敗群倫?主編說:「沒錯!就是你!我們觀察很久,覺得你很敬業也很精采。」我才知道,人生的比賽原來不止於鳴槍起始的那刻或在打扮光鮮的舞臺上;走在人生行道上,隨時隨地都有可能接受無預警的默默檢驗,臺下的一言一行常常才是決勝負的關鍵。
念完碩士後,我走上講臺,在大學裡擔任教職,認真教書、勤於研究,成績還算不錯。但升等得先佔缺,佔缺常繫乎人脈,我以一介平民進入軍事體系,素無淵源,始終未能如願。我憤懣嫉世,埋怨世道不公,龍困淺灘。一日靜坐冥思,忽然想到與其坐困愁城,不如另謀出路,山不轉人轉,於是,重拾書本攻讀博士去。這一轉念堪稱我人生中逆轉勝的關鍵。從那之後,我學會對荒謬微笑,和遺憾握手,承認「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我得設法隨時為自己解圍、脫困。而從種種轉危為安的歷程中,我也頓悟人生真的沒有絕對的順遂,偶爾的挫敗,也是人生的常態。
國中課本裡,有一篇取材自吳敬梓《儒林外史》的〈王冕的少年時代〉是很好的人生教材。身世坎坷的王冕被迫須輟學放牛,求取家用。好學的王冕心中想必不能無恨,但他轉念安慰母親:「我在學堂坐著,心裡也悶,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假如要讀書,依舊可以帶幾本書去讀。」不止於此,放下執念的王冕還從天光雲影照耀下的荷花上看出了希望,認定:「天下哪有個學不會的事?我何不自畫他幾枝?」他開啟了潛能、成就了新事業,從此展開繪畫的第二春。
少年王冕並沒有因為學堂教育上的挫折而灰心喪志,他坦然接受坎坷的命運,也許羨慕同儕能繼續在學堂讀書,卻不因此怨恨母親的無能或自己命運的乖舛。他接受不能繼續在學堂受教的現實,卻沒有一刻放棄喜愛的書本,仍舊千方百計和書本保持聯繫,攢錢購買較便宜的舊書。雖接受現實,卻絕不向現實低頭,他將孜孜求知的課堂搬到柳樹蔭下、綠草地上,沒有什麼困難能阻攔他求學的心願。王冕雖然年紀輕輕的,卻清楚知道得趕緊收拾沮喪的情緒,才能心平氣和地繼續前行,也才有機會看到人生其他美麗的風景。我當年的轉念,也許正是不自覺的受到王冕啟發的結果。
如今,我兢兢業業克服困難走過人生的大段途程,從一場朗讀比賽開始,幸運地持續走到文學教育與文學創作的道路上,教學、演講和寫作遂成為我一生的寄託。我深感人生無論短長,一逕悲喜交織。不管多難走的路,也還是得直直走下去。因為教書,和學生持續接觸,我得以隨時保持年輕的心情;因為找到了寫作的興趣,可以在字裡行間盡情驅策馳騁,再大的苦,轉念之間,都能成就美好的信念;因為寫作與教書所連帶衍生出的演講活動,引發我對社會議題的關懷,對人群的關注,讓我得以下定決心在專業所及的領域裡無怨無尤地投注心力。
我感謝生活裡密織的羅網中所有繁瑣的際遇,無論開心或傷痛,因為有它,我的人生因而變得寬闊無邊。我理解到興趣一旦和志業緊密結合,所有的困頓與辛勞都將成為不足掛齒的小疵,不掩大瑜。因此,衷心期待年輕的朋友,越早找到志趣與寄託,然後全力以赴,如此,就能越早成就生命的美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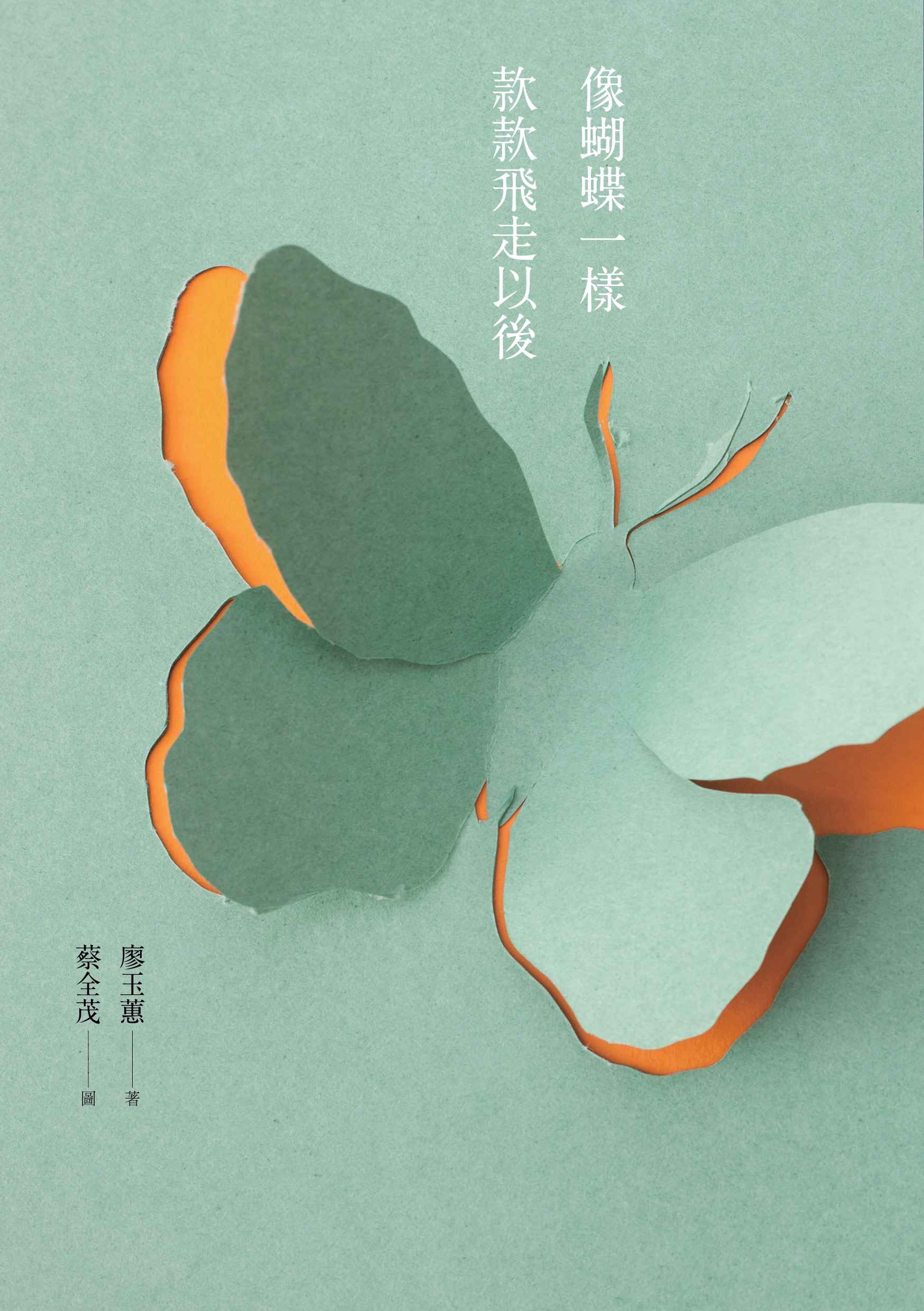
本文節錄自:《像蝴蝶一樣款款飛走以後》一書,廖玉蕙著,九歌出版。
圖片來源:蔡全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