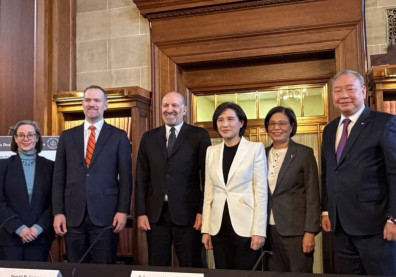針對《臥虎藏龍》,張建德訪問了詹姆斯‧夏慕斯(James Schamus),這篇訪談名為〈我們把成龍打得落花流水!〉(“We kicked Jackie Chan’s Ass”),從標題不難看出雀躍的心情。夏慕斯在訪談中興奮地說,《臥虎藏龍》的票房成績,遠遠超過了成龍演的《特務迷城》(2001,全球票房大約2,100 萬美元)。除了票房之外,《臥虎藏龍》還大幅改寫了中國動作片,此片的成功無異於給了成龍一記當頭棒喝。從此之後,武俠片不再是青少年次文化娛樂、邪典(cult)電影的同義詞,李安的電影打造了新的觀影感受,賦予武俠片和傳統中國文化一種好萊塢的光環。此外,此片的幕後操作方式也成功「現代化」了中國的拍片環境,下一部達到同樣影響力的影片是哥倫比亞(亞洲)製作、陳國富導演的《雙瞳》。哥倫比亞的資金挹注表示「高級」資本主義及好萊塢的運作方式也成為接下來香港、澳洲、好萊塢工作團隊遵行的準則。以《雙瞳》而言,雖然本地團隊和外國技術專家之間有些摩擦,但它的成果還是遠遠超過了遠在洛杉磯的哥倫比亞公司經理的期待(更多關於本片的討論請見後記)。在台灣海峽另一端,中國大陸導演張藝謀將整套模式應用在《英雄》上,撐起幾乎完全相同的公式:好萊塢片商發行、武俠片類型、跨國拍攝團隊和明星卡司,以及在中國當地取景。多虧中國大陸政府的全面參與和協助,《英雄》在國內市場賣出了極為亮眼的成績,但在國外市場上,此片還是被發行商米拉麥克斯(Miramax)冷凍了長達兩年,直到2004年才在美國發行,獲得廣泛成功。在主題上,此片毫不遮掩的帝國主義使某些華人評論者感到很不舒服,尤其在當時中國統一仍然是一個極為敏感的話題。
李安的《臥虎藏龍》拍的並不是美國電影或華語電影,而是好萊塢/華語電影,他創造了一種新的、不是那麼渾然天成的混合電影。但是,這種電影同時也被認為是在刻意迎合西方觀眾的期待,助長東方主義的刻板印象。由於多方考慮計算,此片最後把中華元素包裝在好萊塢式的外衣底下,使李安被指為自我東方主義化。事實上,這種指控並不讓人意外,但這類批評無助於深入了解國族電影和類型混合後的多重層次,以及跨國操作的手法和跨文化機制。尤其,這種說法無法處理一些更有趣的議題,比如說導演本身因為深陷不同文化框架,而產生的衝突、認同的經驗。問題在於,如果李安代表了晚近美國夢的實現,我們是否需要看清,李安的成就本身是不是一種成功的文化融合?李安和華語電影的連結在哪裡?而身為一個台灣人/華人,他在好萊塢的位置又在哪裡?
轉換國界,轉換類別
一部成為全球大熱門的華語電影,無可避免會被認為是一種東方主義情調的再現。德瑞克‧厄利(Derek Elley)在電影雜誌Variety中便撰文評論,認為《臥虎藏龍》呈現的並不是「真的亞洲」,他認為此片是一個被迫融合的文化混種。李安承認,在拍攝之初,便刻意讓《臥虎藏龍》適合全世界的電影觀眾。李安的說法牽涉到他本身的雙重身份,即華人與好萊塢導演。此外,他也試圖改變迂腐陳舊、「封建」的中國拍片環境,還有西方對華語電影的刻板印象。毫無疑問地,比起其他類型,武俠片更適合作為李安一石二鳥的舞台。
要邀請全球觀眾觀賞武俠片,需要先從華語電影中的服飾、器具進行文化上的區分。對李安而言,這是自1960 年代以來就確立的流行電影傳統。對他來說,華語電影歷史的指標就是服裝類型、動作片、家庭通俗片,這些電影都由當時的片場導演一手打造,如李翰祥、胡金銓、張徹、李行和白景瑞等人(詳見第一章)。李安認為,我們對中華歷史與文化的理解大部分是來自於這些類型片的場面調度(mise-enscène),而上述的離散(diasporic)電影導演不只在戰後時期一手塑造了觀眾對中華文化的想像,也建立了敘事模式、視覺表現手法、港台華語電影製作的標準化方法。李安對華語電影歷史的整體看法,明確地反駁了《臥虎藏龍》是「不真實」的中國的說法。
李安指出了華語電影的缺陷,他的看法具有雙重意義:在製作方面,李安利用《臥虎藏龍》將「高品質」工作方式介紹進華語電影產業,亦即工作團隊和導演可以互相獨立工作。這意味著,在每個技術領域,工作人員和技術專家都會有更清楚的分工。為了讓工作人員理解整個計劃的目的和企圖,李安將工作時間與精神集中在他們身上,而不是以指示、對待勞工的方式看待團隊和演員。因此,他們可以獨立解決問題,而非空等導演的指示。對於習慣遵守秩序、仿效標準程序的中國、台灣工作人員來說,李安的西式方法很陌生。但李安相信,好的攝影過程必需仰賴製作團隊的效率、專業化,以及協力合作的過程。
懷著尊敬華語電影傳統的心態,李安以《臥虎藏龍》挑戰觀眾過去對武俠片的刻板看法,並向西方觀眾提供了另一種華語電影的選擇。這麼一來,就必須要偏離原本標準化的製作方法。李安希望將《臥虎藏龍》和香港1980年代的武打動作片區別開來,也企圖將武俠片從第五代導演過於強調服裝的傳統中解放出來。
為了拍攝這部現代武俠電影,李安面臨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武術指導。由於李安希望突破數十年不變的武術指導方法和規則,因此和出身香港派的武術大師袁和平的意見有很大不同。從李小龍、張徹的時代開始,香港派就主宰了華語片中的武俠動作,充滿了腿腳、拳頭、防禦等動作。炫目的速度和致命的力道構成了大眾對武俠片的既定印象,這也是近期成龍、李連杰、袁和平的好萊塢作品之所以賣座的重要元素。但是,對李安來說,這種老式的方法塑造了刻板印象,似乎主角都是「超人」(李小龍和成龍),或者是一種驚世駭俗的平面化英雄人物(campheroic,如張徹和徐克作品中的角色)。
李安刻意尋找空靈、沒有方向感、較抽象的打鬥場景,而非複製袁和平在《駭客任務》(The Matrix)中那種硬梆梆的武打動作,這些特質在竹林打鬥一景中都可以清楚看到。導演要求袁和平設計這種具流動感的糾纏動作,但袁和平一開始只覺得這根本是文人的癡心妄想。李安堅持要一種「意亂情迷」的感覺,而非乒乒乓乓的衝擊力;更重要的是,李安打算將以前重視動作勝於氣氛的武俠片傳統,替換成更中性的場景調度。他強調,為了「回歸」武俠片類型,他要恢復虛構的特質,而這是中國傳統敘事中的重要資源,例如儒家思想和道家的神祕主義。李安認為,過去的電影大多忽略了道家思想,而他要以《臥虎藏龍》來介紹其虛構、烏托邦式的幻想,為了要模擬此種幻想的、受道家思想啟發的氛圍,如何呈現打鬥場景就變得非常重要。李安為此安排了柔軟、輕盈、充滿自然觸感的場景,例如水、樹葉、風等。
《臥虎藏龍》試圖召喚武俠片的歷史,並創造一塊新興的主流華語電影市場。這部電影之後,開始有很多誘因重新製作、發行華語電影,而且不只是為了參加國際影展。《臥虎藏龍》參照了過去的電影,因此開啟一座過去大眾不熟悉的歷史資料庫,從這層意義來看,《臥虎藏龍》的意義非比尋常。這個電影類型本身已經重新修改,採取較為主流、正常化的節奏。但是,要使武俠片在國際上受到歡迎,這條路顯然並不好走,因為華人觀眾和評論者有時會嘲笑電影中為了妥協而導致的一些後果,比如語言和口音。對非華人觀眾而言,由於配有字幕,因此演員的口音和方言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角色說和做了什麼。但是,不同演員使用的語言和口音卻有一些細微的差別,這些部分有時超出了原本的預期之外。
當編劇夏慕斯聽到俞秀蓮(楊紫瓊飾演的俠女)呆板、誇張的說話方式,他跑去質問李安,但李安不服氣地爭辯:「我們中國人就是這樣講話的。」夏慕斯則反駁他的說法,認為這部電影一開始就注定失敗,因為俞秀蓮的說話方式將會成為一個笑柄。但是,對李安而言,俞秀蓮是一個倍受禮教束縛的中年未婚女子,又是一個擁有專業技能的護衛,她尊崇儒家的教導,將自己對愛情的渴望昇華為對劍器本身的嚮往。她的一切說話方式、行為舉止、衣著、動作、態度都應該要受到儒家理想中的「禮教」約束。俞秀蓮也相信,驕縱又野蠻的玉嬌龍應該要明白她的立場,追隨長者的教訓。李安說:「中國人很能理解、接受這種傳統價值。」然而,俞秀蓮的台詞聽起來像是由一個極右派頑固份子的口中說出來的,李安開始覺得不安,想更改俞秀蓮的台詞。最後,李安要求夏慕斯重寫所有俞秀蓮的對白,加入美國偵探電影和通俗劇的元素,使這個角色更自然、更容易讓西方觀眾理解。
夏慕斯亦負責編寫沙漠中的愛情這個重要場景,而且要考慮到沙漠中的流星這類具異國情調的景色。這一回,換成土匪羅小虎的語言有問題。電影上映後,亞洲的觀眾頻頻抱怨羅小虎(張震飾演),覺得他的說話方式聽起來太現代,而他的措辭和絕對錯不了的台灣口音與那個年代和西域的場景設定也不相符。羅小虎和玉嬌龍之間的愛情有一種神話、幻想的特質,兩人的熱烈感情完全不同於玉嬌龍在城裡的生活,也違背了儒家的禮教。有些觀者會認為,這段如夢似幻的插曲背叛了中國武俠的精神。但是,這種調性上的變化與玉嬌龍內心的渴望相符,部分是來自於她閱讀和理解的武俠世界。總體而言,李安早就決定他會調整、修改若干武俠片的傳統,以符合外語史詩電影的條件。部分華語影評人和觀眾認為,這樣的修改過於大膽,直接刪去了某些他們認為屬於武俠片古典本質的風格和元素。
在電影配樂上,李安的操作是以戲劇性和情緒衝擊為主。傳統中國武俠電影造成了兩極化的評論,部分原因便是一成不變的配音方式,它會抹除語言、口音的細微差別和聲音設計,使武俠片感覺上有些粗糙。這種配音方式的出現可追溯至張徹;1960年代初期,他說服邵式片廠以不同步錄音的方式拍攝武打場景,認為這樣可以提升畫面上的動作效果。不同步錄音使得武打動作更具發揮空間,也讓選角更具彈性,可使用粵語演員,再配音成為國語發音,這種影片成了邵式片廠的主要產品。為尋求經濟效益,邵式片廠答應了張徹的要求,讓他全權負責管理配音部分。從此以後,配音和字幕就成為華語電影、電視不可缺少的部分。雖然成功擴展市場範圍,但也造成做假的感覺,甚至給人劣質的印象,使得武俠片(至少)在西方成為邪典電影的類型之一。
李安摒棄了邵式、嘉禾那種片廠味道濃厚的電影,拒絕把演員當成活動式假人,只是利用他們的表演,再配上標準國語。因此,他不願為了口音是否正確而使用配音,他解釋:
一開始,因發行的方便,我就打定主意用國語發音。雖然明知周潤發、楊紫瓊的發音帶有廣東腔。……憑良心講,周潤發在片中的國語講得比陳水扁、比董建華、比江澤民都好,我覺得他的國語百分之九十是沒問題的。楊紫瓊的發音及腔調是有問題。但我覺得聲音本質能夠傳達的情緒比聽配音的標準國語要感動人,所以我還是割捨不下,保留原音。
李安一心想以「寫實主義」為優先考量,想帶出角色最真實的樣貌,但是華人的耳朵無法適應演員原本的聲音。值得一提的是,李安對語言政治的詮釋是從多元文化的角度切入;他把語言視為華人文化多元化後的真實反映,廣涉世界上各個有華人存在的角落,而非獨尊某一種典雅、崇高的中心,如北京或台北。比起《英雄》中,張藝謀小心翼翼地抹去港星張曼玉、梁朝偉的廣東口音,配上標準普通話,李安對語言政治的看法展現了拒絕單一語言實踐的態度。
李安對華人語言系統的看法正好與他的野心不謀而合――他企圖將一個外來、中國的電影類型整合進入全球的娛樂產業之中。這種行為不只像煉金術或東西方文化的混合,還包含一種更大的視野,超越了「給予與接受」(李安語),也包括重拍中國電影、重新塑造觀眾對中國電影的接受和反應。在李安的回憶錄《十年一覺電影夢》中,他質疑東西方電影的二元對立,認為好萊塢電影不只是流行娛樂,華語電影也不只是適合參加影展的藝術電影。李安說明,為了支撐龐大的發行市場網絡,好萊塢電影確實必須保持流行文化的全球流通。然而,這並不代表好萊塢製片只能製作出用過即丟的流行娛樂商品,非好萊塢電影也不表示只能被隔絕在全球市場之外。但是,亞洲的製片人似乎一直這麼認為。因此,各國電影產業和好萊塢之外的導演紛紛從大型商業製作退位,將自己的職業生涯奉獻給影展和藝術電影。他們能想像到的最高成就不外乎是坎城金棕櫚、威尼斯影展金熊獎、金馬獎等國內外主流影展的獎項。
李安認為這種分界已經根深柢固,更主宰了許多國家的電影製片政策,正如過去二十年間,華語電影的兩波電影新浪潮(中國大陸的第五代電影和台灣新電影)。不為美國市場拍片的導演認為自己「不適合」追求通俗電影類型,也認為自己不得不拍適合參展的藝術電影。此現象造成兩種結果:在全球網絡中,好萊塢的公式電影不斷增加繁衍、互相模仿;有特色的聲音和新題材卻無法在美國電影產業中發聲。正因為如此,藝術和商業之間的分歧日漸擴大。
李安這種對電影產業的看法,主要來自對多元文化的了解,並從中培養出獨立的思考和信念。他認為自己不只在好萊塢的製片模式中保有獨立性,也不受任何單一類型、風格、主題、甚至是語言所囿。不同於一些必須在好萊塢製作和獨立小成本電影之間轉換的導演(例如王穎),李安喜歡異質類型之間的碰撞,以創造出更具挑戰性、更精緻的票房大片(如《綠巨人浩克》),或是讓人腎上腺素激增的靈性藝術片《臥虎藏龍》,兩部片同樣都受到主流電影院的歡迎。過去,李安的外來者身分可能是一個沉重的負擔,如今卻變成他盡心維護的東西。他刻意小心維持著中國人的本分,從未申請成為美國公民,這麼做的目的是為了撐開一個空間,使人重新思考、扭轉美國的主流文化形式。李安深思熟慮、別具野心,一方面小心避免捲入好萊塢系統之中,一方面也不浪費任何工作機會。最好的方法,便是借用好萊塢發行系統的力量,製作「真正的亞洲電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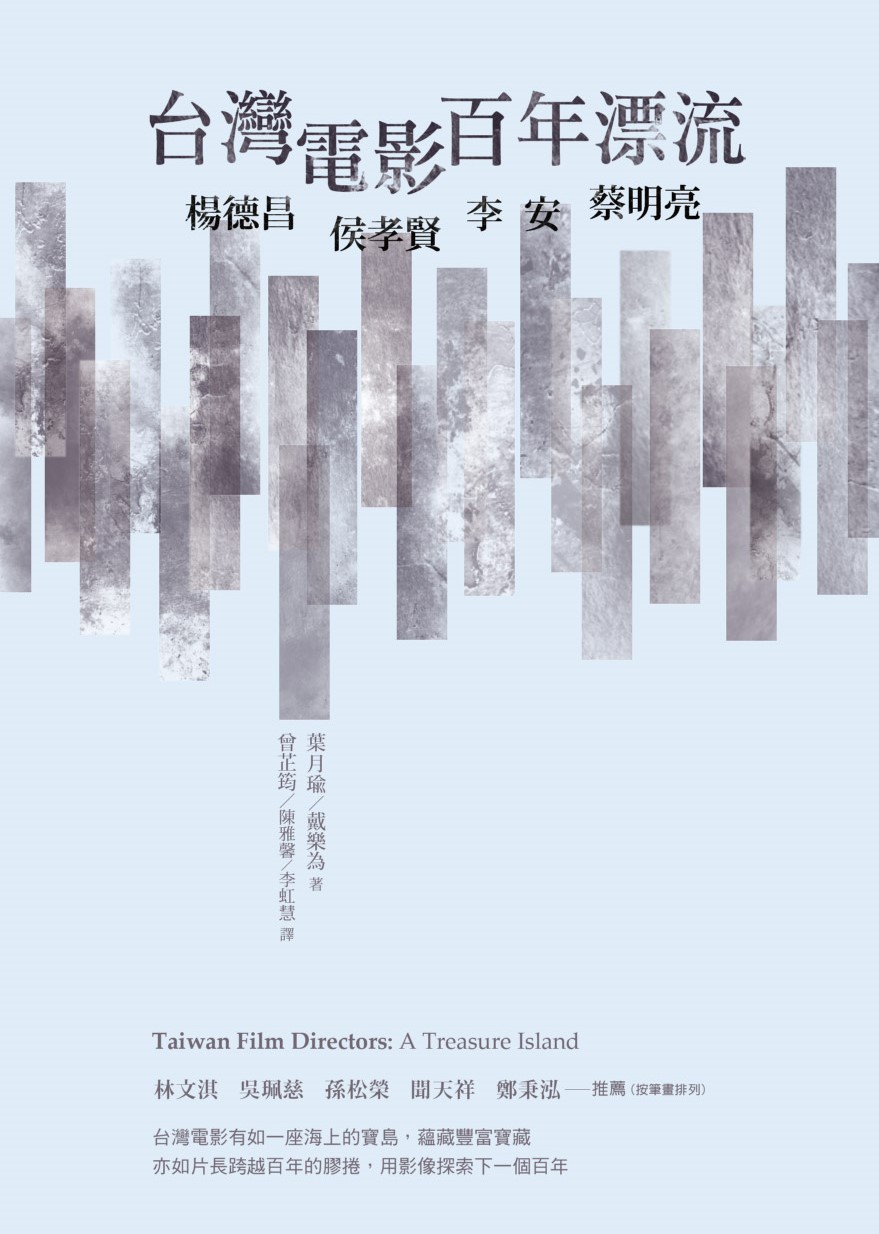
本文節錄自:《台灣電影百年漂流》一書,葉月瑜、戴樂為著,曾芷筠、陳雅馨、李虹慧譯,書林出版。
圖片來源:unsp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