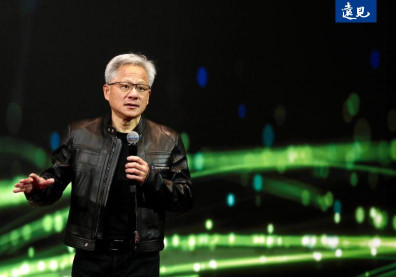「因為時代一點都不溫柔,所以才反過來追求『溫柔』。而『溫柔』表現在現實中時,又只能採取頭盔和棍棒這種粗暴的形式。在現實中的理念,暴力這東西成了非暴力,非暴力的東西卻成了暴力,當下存在著『溫柔』的悖論。」
出自《我愛過的那個時代》裡的一段文字,成為去年318學運時期,不斷被大量傳誦的重要註記。
作者是日本知名評論家川本三郎,對他來說,這本書的出版不僅是青春時代的告白,也是為了讓壓抑許久的自己,獲得重生。
年輕時,川本三郎積極參與60年代的日本反戰運動,在朝日新聞社擔任記者期間,報導自衛官刺殺事件,他基於新聞倫理為凶手保密,之後遭到報社開除,成為日本媒體史上充滿爭議性的倫理案件。
爾後他仍繼續寫作,活躍於日本藝文界,作品涵蓋文學、電影評論和翻譯等領域,著有《大正幻影》、《荷風與東京》和《林芙美子的昭和》等書,眼光獨到的他,也是最早挖掘日本作家村上春樹的評論家。
事實上,他曾透露,這件事長久以來沉重地壓在自我的生活、文章表現和風格上,即使從事評論工作,也無法獲得釋然。
但或許歷經人生波瀾,形塑出獨特的觀察視角,他的評論作品豐富又多元,這幾年提倡「東京學」和「散步學」等概念,不僅是對自我生活面貌的詮釋與重整,也是對美好生活的全面性想像。
2015年3月底,時隔318學運一周年,川本三郎來到台灣,除了隱約標誌著對革命精神致敬,他也以「東京散步:文學、歷史、電影之旅」為主題,與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李明璁對談,分享他的生活哲理。
當天,穿著黑色西裝的川本三郎,看起來精神奕奕,20多年未訪台的他,難掩興奮之情,他不時講話講到忘我,一下子就說了五分鐘,讓一旁的口譯員得提醒他給予翻譯時間。
從東京繁華起落與昔往,聊到內心多年來的痛楚,接著他點出東京特有的城市文化,包含鐵道、下町和居酒屋等,並巧妙連結自己的生命經驗和感受。
「我很喜歡到東京的下町散步,因為那裡充滿著失敗者,」川本三郎解釋,由於地震和戰亂等歷史背景因素,下町擁有許多神社,像是一座「祈禱的城市」,人們在神社參拜的身影,總讓他想起在戰爭去世的父親,祈禱,成了心靈寄託。
今年70歲的他回首過往,形容自己也像是個失敗者,於是他愛上了下町,平日的悠閒散步時光,無形中形成慰藉,當地的簡樸生活樣貌,則是溫暖他、讓他不斷向上的穩定力量。
「Beautiful Losers,美麗的失敗者,」李明璁引用李歐納‧科恩《Beautiful Losers》的書名回應了川本三郎的自敘。
經過多年,川本三郎手中的筆從未停過,體內依舊保有年少時期的熱血因子,無論時代是否回應溫柔,他不斷記錄生活觀察與點滴,寫下人生篇章。
以下整理完整對談內容:

李明璁(以下簡稱李):大家晚安,歡迎大家在週末來到這裡,也很歡迎川本先生。前幾天我們第一次碰面聊天,很興奮,跟在座的大家一樣,川本先生對我來說原本只是個出現在書上的傳奇人物,如今能親眼見到他,還一起對談,實在就像和偶像同台一樣的美夢成真。
今天主題要談東京學,台灣到日本旅遊的人數很多,據統計,每四位在東京的國際旅客當中,就有一位是台灣人,比例相當驚人。然而從1990年代開始的赴日旅遊熱潮,20年來其實逐漸有了一些變化。
早期赴日旅遊的想像和實踐,大部分與大眾文化有關,尤其受電視劇的影響。但是這幾年來,大家到日本不再只是景點觀光或消費購物為主,而嘗試轉變為更裡層的文化體驗。透過雙腳散步與雙眼凝視,旅行者放慢速度參與當地生活。這點就跟川本先生所提倡的「散步學」和「東京學」有關。因此對於這樣的深度旅行,想先請川本先生分享。
川本三郎(以下簡稱川本):很高興有機會來台灣,我從來沒想過我的著作竟然可以翻譯成中文,並在台灣出版,真是作夢也沒想到。一開始聽說要跟李老師對談,我聽說他在很厲害的大學任教,也是很厲害的老師,然後又聽說,他去年有參加太陽花學運,我當時內心就想像,他應該是個很嚴肅,而且很可怕的人吧!結果沒想到一見面,發現李老師是這樣的一位人物,讓我整個人都放鬆了!(笑)
來到台灣最讓我大吃一驚的事情,是發現街上都是年輕女性。不光是街上,包含現在的演講現場,也是以女性居多,在這裡遇到的工作夥伴也幾乎是以年輕女性為主。
我覺得一個城市要很美好,街上才能出現許多女性,為什麼?首先這代表這個城市的治安很好、很安全,再者是提供女性工作機會,因過去的女性大多是在屋內,也就是在家庭中。
以東京來說,有大量女性開始上街是70年代開始,在這之前,東京可以說是一個男性的城市。80年代後,日本女性進入職場,這具備了特定的社會背景,之前東京是個工業城市,後來轉為第三產業,像是服務業等,這讓更多女性可以參與。
我想要請問李老師,台北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讓女性投入社會,並進入職場工作?
李:我有個認識15年、很要好的日本女性朋友,她很喜歡台灣,每年都會來台很多次。她曾經說過,台北讓她有種獨特的自由感。我問她,那是什樣的自由感,日本應該也是很自由不是嗎?
她說,感覺台灣的女性不用總是刻意拘謹表現出社會或職場上期待她擁有的樣子。她也知道,台灣的女性可以自由地換工作,不像日本大多數的女性在畢業後就到會社裡當OL,快到30歲時要想辦法把自己嫁出去,接著離開職場,在家養兒育女。
台灣女性沒有這樣的LIFE CYCLE需要遵循,所以可自由地尋找工作、轉換工作,尤其對愈年輕的女性愈是如此,所以無論是具體或抽象的自由感,都讓身為日本女性的她,感到相當羨慕。
從生產面來看,台灣女性的就業人口或類別,似乎都比韓國、日本表現來得好。1980年代之後,台灣從勞力密集的產業轉變到服務業、知識密集產業時,女性和男性在工作上的性別分野也開始模糊。都會辦公室裡越來越多的女性專業人士,在經濟與城市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於此同時,台灣也逐漸邁向消費社會,感受力與消費力旺盛的女性更是不容小覷。台灣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或許比日本慢,但是女性的位置、以及對社會的影響力,卻反而是同步、甚至是超前的。
川本:原來台灣的女性是如此自由,尤其聽您說是出自一位日本女性的說法,我想她一定非常羨慕吧!若比較台北和東京這兩座城市,女性都能在晚上放鬆地進出,這是兩地的第一個共通點。第二,這也反映出兩地的居住環境很小,許多歐美人來到東京,都說我們住的地方就像是兔子窩一樣。
以我自己來說,我家很小,也沒有客廳,如果編輯要來開會,我們就會去咖啡廳或是居酒屋,我有一個假設是,如果城市居住空間愈狹小,大家就會上街。
李:我可以補充一個有趣的現象是LOVE HOTEL,歐美並沒有LOVE HOTEL,但是在日本、台灣和韓國卻很發達,這是因為居住環境小,但是大家又渴望擁有現代人的獨處空間,或是發展親密關係的地方,所以就需要這樣的空間,這是西方人難以理解的、專門為了做愛做的事,而開創的休閒娛樂場所。
川本:我就正要舉這個例子!(笑)
李:就好比咖啡廳也是一樣,咖啡雖緣起於歐洲,但是在首爾、東京和台北,我們卻擁有極為多樣選擇的咖啡廳,無論是風格或裝潢上的差異等。因為去咖啡廳不只是喝咖啡,而是想擁有短暫自由時間和個人空間的意義。因此無論是咖啡廳或是LOVE HOTEL,就是川本老師剛剛要說的,一個都市如果家庭單位的物理空間不大,就必須要有更多讓個人感到解放或發展人際親密的空間。
川本:你說得完全沒錯! 所以如果我用硬一點的話語來詮釋,一個城市的大小跟一個人的家裡是成反比的,所以家裡愈小,城市就愈大、愈發達。舉一個笑話來說,有一位作家,他渴望擁有很大的房子,於是他搬到郊外去,他幻想家裡以後有客人來就方便多了,但是因為到他家要花上一個小時,最終發現根本沒客人上門。
因為東京人住的地方小,所以大家走上街,讓東京變成一個有趣、好玩的城市,我會這樣想,也算是對西方人笑我們家是兔子窩的一種反擊吧!
再回到硬一點的話題,我想聊聊台灣的導演侯孝賢,他經常來到東京,而且是十足的鐵道迷,他到東京喜歡搭電車,對電車瞭若指掌。
事實上日本近代城市的發展,會依循著一個原則。以往在江戶時代,如果是住在城的附近,就是「城下町」,大家會繞著城市居住,在寺廟附近的話就是「門前町」。
1868年明治維新後,日本邁向現代化國家,當時建設了鐵路,一開始明治天皇認為鐵路是軍事目的,但是之後漸漸深入民間和生活,所以在汽車時代來臨之前,日本有很長一段時間是電車,也就是鐵路的時代。因此日本近代的城市風貌改變了,以鐵路車站為中心,附近有商店街,接著是住宅區,這就是日本城市和鄉鎮發展的主要原型。
1964年東京奧運後,汽車時代來臨,有了汽車後,大家比較少利用車站,反而是車子可以到達的大規模購物中心開始發達。
當日本全國開始以汽車為生活中心,卻只有東京還循著以車站為發展中心的老模式,所以很多地方的人來到東京會嚇一跳,東京還是以鐵路代步,開車的人很少。
我上次來台灣是很多年前,現在讓我驚喜的事情是台北的交通相當發達,有捷運、高鐵和台鐵等,全球的交通發展愈來愈以汽車為中心,台北仍以鐵路為發展重點嗎?想請問李老師,這是都市計畫有心要朝這樣發展,或是自然而然如此?
李:川本老師這幾天應該都坐捷運,所以沒有注意到,其實台北最特別的都市景觀之一是機車。回溯機車文化的歷史,首先因為台灣戰後初期,國民黨政府抱持一種隨時要反攻大陸的心態,所以像是公共交通等基礎建設的預算都遠不及國防預算,更不用說有長久遠見的都市規劃。
另一方面,當時日本販賣交通機具的大公司,都瞄準東南亞市場,尤其像是台灣這樣正在發展的國家。在勞力密集的產業結構中,機車就是工人階級最機動也最負擔得起的移動工具。
台北要一直等到1980年代以後才開始好好規劃公共運輸系統,在這過程中,東京當然是一個重要範本。直到近幾年,台北捷運才逐漸成為一個真正能聯結市區與市郊各區的network,坦白說已經晚了東京一整個世紀。
呼應剛才川本老師說的,東京的電車發展的確很驚人,我常使用的比喻是,電車路線就像是這座城市的血管,每條血管都流經不一樣的地方,擁有脈動的生命力,並負責維繫不同器官的運作。
日本有一門學問叫「電車人類學」,討論每條電車經過地區的歷史文化,每條路線擁有不一樣的居民認同感。像是我曾經住過中央線,就有很多庶民的集體記憶、和文人的有趣故事,形成豐富的地方認同。與此相比,台北還需要很長時間的累積,但是我已感覺,我們終會迎向電車文化的來臨。
川本:看起來這是個美麗的誤會,我上次來是20年前了。
李:如果川本先生有機會,我們應該騎機車載他(笑),他應該可以感受到台北不一樣的自由感,這是很獨特的。以前我們曾經看過有些日本歌星來台灣表演,他們都對滿街自由跑的機車,感到一種奇妙的浪漫感。
機車文化在過去是種不得不的生存策略,是第三世界人民在國家不作為下的一種自力救濟,但是未來,這可能變成是一種生活風格選擇。我們既有捷運電車等大眾交通運輸,也能有機車或腳踏車,天氣好的時候,不用鑽到地底下,就可以自由移動,我想這是台灣比較特別的地方。
川本:我對於你說的摩托車文化很有興趣,那台灣有沒有一些電影、戲劇或是流行歌曲,涵蓋這樣的內容?
李:其實有很多,我們輕易就可以舉一些例子。像是五月天的〈軋車〉,就是在講年輕人要有一台車,追求心中的自由。電影裡面也有,在侯孝賢的電影裡面,年輕人多半都騎機車代步。對於台灣人來說,機車是種象徵成年的儀式性物件,就好比對美國青少年,擁有一部汽車的意義一樣。
川本:這真的是很大的文化衝擊!在日本鐵路文化盛行,很少人騎機車,而且在日本,騎機車的形象沒有很好,會聯想到暴走族、不良少年和幫派等,所以在日本,當你說你騎機車,並不是件很有面子的事。
回到剛剛中央線話題,聽到李老師說研究中央線,讓我很開心,因為我本人就是在中央線出生,說到東京的鐵道文化,依照不同路線,給大家的印象是完全不同的,擁有自己的鐵路文化,其實有些私人的鐵路,像是東橫線、西武線等,也有社會上的階級落差。
李:我幫川山本老師做第一點歸納,大家未來去東京,如果想要擁有不一樣的旅行經驗,首先可以鎖定電車文化。請試著觀察搭乘的人、經過的站等等,這些都具有差異性和趣味性。就算是同一條線,早上、下午和晚上所搭乘的族群也都不同,這其實是觀察東京現代市容的第一步。
十幾年前我初到東京時,那時大多數台灣旅客到訪的地方都是圍繞著山手線,像是新宿、澀谷等地,這些大型商業區,其實缺乏一種生活感。我們誤以為在電視上總是播放著時尚的東京,就是以這些地方為代表,但實際上,日本年輕人真正想居住和生活的地方,並非是在這裡,而是在中央線的吉祥寺,或是像下北澤等地。這些地方並不見得是大型商業區,但卻有剛剛川本先生提到的,一個以車站為中心,周邊發展出商店街、公園、住宅區等具有當地的獨特生活樣貌。
川本:東京是有兩千兩百萬人口的超級大都市,但是存有許多小的「町」在其中,所以很多人不知道旁邊區域發生的事。曾經有位法國電影導演,來到東京拍攝紀錄片,他曾經這樣形容東京:白天的東京感覺是個現代化的大城市,但是到了夜晚卻像是鄉下的村子。
東京有個很大特色是依照時代背景和風俗民情,可以略分為兩大區域。東京的東邊是下町,所謂的老社區,東京的西邊則是山手,是比較高級的區域。世界的大城市裡,能如此明顯劃分,是相當少見的。
東京的東邊和西邊最大的差異是居住的人,東邊的下町,維持著江戶時代的傳統和氛圍,住著庶民,反過來看山手區域,它是武士住的地方,到明治維新的時候,這裡是政府官員的住處,聚集社會上比較有權力的人。
我出生在中央線,也就是山手的文化,一直到長大,我才發現我喜歡的是老社區,我喜歡到下町地區散步。至於我為何會喜歡上東邊,要說明原因可能很複雜,但有天我突然想到原因。
先說東京這個城市,放眼全球這是很特別的城市,在近代歷史中,東京遭受過兩次很大的災難,第一個是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規模相當慘烈,死了好幾萬人。第二個災難是二次大戰期間,東京持續遭受美軍空襲和轟炸,幾乎把東京毀滅,而受到最大災害的地方是東京下町。
為何受災最慘重的是下町?因為下町的地形較低窪,地層比較弱,所以大地震時期受害很嚴重。至於美軍空襲時,下町以工業發展為主,有很多製造兵器的小型工廠,因此成為空襲目標。
所謂下町,可以說是亡者居住的地方。後來我看到法國導演所拍攝的東京紀錄片,名叫《太陽之光》,透過外國人的眼睛,我看到我平常沒有注意到的現象,其中這部片拍了許多在下町地區的畫面,當地人在神社雙手合十的畫面,這時的旁白說:東京是一個祈禱的城市。
那時我看到非常有感覺,也很吃驚,我從沒想過東京有這樣的一面。我出生於1944年,但是我父親隔年就因戰爭去世,所以我對戰爭有非常痛苦的記憶,所以當我聽到,東京的下町是個禱告的地方,我就不自覺地開始喜歡上下町。
李:我在這裡可以幫忙川本老師再標出第二個重點。剛剛第一個是電車,現在第二個是下町。我個人也是一個下町迷,自從我去過東京一兩次之後,就發現下町的迷人氣息,遠勝那些人潮洶湧的商業區。
我現在去東京,幾乎都不去那些旅遊手冊標示、有吃喝玩樂景點的地方。我大部分住在日暮里、根津、千駄代木和谷中等地,這些地方坦白說沒有任何觀光景點,但是這裡有很獨特的生活氣味,在這裡不用做任何事情,就是「散步」。
這裡有許多神社,沒有什麼高樓,可以在錯落的老房子間看到上下坡的起伏,天氣好時有的地方甚至可以遠眺富士山。散步時會遇到小朋友上下課、家庭主婦出門採購或跟鄰居串門子,也有許多貓,貓是下町地區很重要的存在。此外,甚至還可以看到日本明治維新之前、江戶時代就留下來的遺跡,也就是經過兩次災難,都摧毀不了的遺跡,這就是東京之所以成為獨特東京的原因。
川:還有第三個重點,大家聽清楚囉!(笑)第三個重點是要去居酒屋。日本的居酒屋文化,是很獨特的,其實現在很多西方人來到日本都要去體驗。大家知不知道前陣子日本的和食被選為無形的世界遺產,但我覺得與其選和食,居酒屋文化比較重要。
李:我覺得太有趣了,剛剛川本老師說,要講第三個重點前,我還想說因為他是作家,我們現在又在書店對談,所以第三個重點應該是書店。結果沒想到,老師卻說,哦不,是居酒屋!(笑)
不過我覺得這兩個沒有衝突,對作家來說,除了家裡之外,最常去的兩個地方就是書店和居酒屋吧。川本老師剛剛說居酒屋是日本的世界遺產,我想書店也是。東京仍然保有有一個當今世上最大的書店區,在神田和神保町。這些書店並沒有因為數位時代來臨而沒落。
因為書店對許多東京人來說不只是賣書和買書的場所而已,就像居酒屋也不只是喝酒的餐廳,這些老派的地方,都是人與人相遇,聯結並發生各種想像,並且感受到能安心休息、或者探索新事物的場所。這就是這個都市之所以迷人的地方。
川本:剛一邊聽李老師分享,我就在思考一天要怎麼過,那我來分享一下最幸福的一天要怎麼過。我今年70歲,每天六點起床,我的老伴過世,所以我一個人獨居,起床後我就到附近公園,大概散步一小時,若有野貓,我就去餵食。
之後回家吃早餐,開始工作,差不多到下午兩三點,我的工作就告一段落,這時我就會輕鬆地搭上一輛電車,東京好大,許多複雜路線,很多地方我一次都沒有去過,我會搭車到下町地區,接著在那裡散步。
如果有書店就會進去,有二手書店更好,我會買本喜歡的書,再慢慢散步,之後進到居酒屋,打開書本,一邊閱讀、一邊喝啤酒。
李:我希望我60歲的時候,就可以過這樣的日子!(笑)
川本:並不是天天都能這樣,而是我理想中幸福的一天!(笑)在這裡,有個重點是,這樣的一整天,我都是一個人。
李:前幾天我們第一次碰面吃飯,我就談到「一個人」的文化在東京的重要性。比如在台灣也有喝酒文化,像是熱炒,但是沒有一個人會去吃熱炒。相對的,我們在日本卻能發現,即使熱鬧的居酒屋也會有一個人喝酒的文化。
「一個人」的文化在日本有長期發展的歷史。從明治維新開始,對許多文人雅士來說,練習或說享受獨處是很重要的。
許多人無法分辨寂寞和獨處的差異,寂寞是一種想要跟別人發生關連、但是卻不可得,以至於有負面感受的狀態,但獨處卻是自己enjoy,沉浸在自己世界裡,並能好好地面對自己。
我想到很多年前,我開始喜歡聊下町的時候,曾經有個旅行社找我帶一個新型態的旅行團,叫做「東京下町之旅」。我起初答應了,但馬上就後悔,因為我發現那就不是下町散步了!實在無法想像,別人在過生活,小貓走過去,或是小朋友跑過去,有人在神社拜拜,然後我們一大群人在旁邊「旅行散步」,好怪,所以我拒絕了。必須也只能是「一個人的城市體驗」或許可以說是今天又一個重要的關鍵字。
川本:唉,李老師,你把我所有想講的話都講光了!(笑)
談到一個人的文化,這就讓我想到什麼是美好城市。我認為大城市的公共建設和藝文活動,都要相當豐富,而如果城市是可以獨處,有空間和時間能自在地享受, 這樣的城市,對我來說就是美好的城市。
並不光是我,西方也有類似的想法。20世紀初,俄羅斯的小說家契訶夫曾經寫過一個故事:有三個姊妹原本住在鄉下,之後到莫斯科玩,她們進到一間酒館,回到鄉下之後,大家問她們莫斯科好不好玩,她們分享說,在莫斯科好棒,在那裡可以一個人喝酒。這就代表了,在大城市當中,雖然很多人,你卻想要隱身。
就像是我現在一個人,曾經有個朋友說,這麼喜歡一個人的話,倒不如就住在山裡。但是我不要,我就要住在城市裡,當我想一個人的時候,我可以坐著電車去居酒屋,可以很自在的享受空間。因此一個人的文化和城市發展,是有緊密關係的。
李:19世紀中期,當巴黎正在經歷大改造時,波特萊爾就有過一樣的論述。他說,現代的詩人,必然是處於人群之中。雖然在人群當中會感到強烈孤獨,但若不如此詩人的感受力就無法如此敏銳。
所以既在人群,又不在人群裡,這是波特萊爾當時面對都市一種又愛又恨的情感。剛川本老師提到侯孝賢,您也是在日本最早評論侯孝賢的人,我就不禁想到,侯孝賢的《珈琲時光》,這裡面就有剛剛老師所說的各種元素,包含電車、書店和一個人散步,還有安靜卻又豐富的各種感官體驗。
於是這部片與其說是珈琲時光,不如說也是電車時光、書店時光、一個人悠悠生活的時光。我是在長春戲院看這部電影,記得當時為了省錢而看早場,整個電影院竟然只有我一個人。但是因為一個人,我坐在那裏看,感受到遙遠又親密的東京。我隨著故事裡面的男主角淺野忠信,一起進出書店,細細聆聽電車像都市血管脈動般的聲音。
我認為生活在都市中,的確讓一個人感到孤獨,但是都市裡的種種事物,卻又可以把一個人巧妙的包覆起來,讓他因此感受到某種溫柔。所以如果一個城市的所有公共建設,都可以更細膩照顧到各種「一個人」的狀態,換句話說,能對女性、對老先生、對新移民、對同志族群都更友善的話,這個城市就是一個最好的城市吧。
很感謝老師的分享,因時間關係,現在就讓大家來發問。

聽眾A小姐:我有閱讀老師的這本《我愛過的那個時代》,去年318學運也有很多學生也閱讀這本書,想請問您對學生運動的想法?
川本:我還是要說,我真的沒有想到我的書會有中文版,讓台灣的大家能讀到,這是很光榮的事。我並不能說我對太陽花學運掌握得很透徹,但這跟我過去參與學生運動有許多共同的地方,所以我非常支持。
我想要分享日本和台灣的不同,我那個年代的學運,整個日本社會歷經高度成長, 我們一下子馬上突飛猛進,衝得太外,一下子撞壁,又掉得太快,一直到現在這個樣子。我覺得比起來,台灣的經濟發展腳步或許是比較慢的,但是慢慢在走,有高有低,經過一些時間之後,就會發現自己已經站在某個高度了,這個高度的台灣,其實我覺得某些程度,是比日本還要成熟的。
聽眾B先生:剛提到江戶時代的下町地區,這是充滿人情的地方,過去幾年,日本拍過很多時代劇,我也很喜歡看,但是最近時代劇比較少了,這是因為日本人不愛看了嗎?
川本:以江戶時代為背景的時代劇,影像作品的確愈來愈少,但是閱讀的部分,時代小說還是很受歡迎,時代小說最吸引人的地方是描述下町人的生活,下町人是從事工商種類的工作,所以大家要相互幫助,才能生活下去,我是作家,我能一個人獨立作業,若我是職人,我不可能一個人活得下去。東京也是所謂的移民社會,大家可以合作幫忙,我覺得透過時代小說,可以看到當初的下町,也就是江戶時代的人情美好。
所以我剛講到,我喜歡一個人去下町喝酒,享受一個人的時光。其實我可能有逞強的成分吧,我很想跟當地人互動,但是個性上又辦不到,所以我就去看看他們,看他們日子過得多麼快樂,我自己也會開心。
聽眾C先生:我看過書,也看過電影,對老師的故事很感動,老師年輕時對記者工作很有使命感,但是發生事情後,老師無法當記者,想請問老師,如果有機會再朝自己夢想邁進,把記者當成一生的工作,老師怎麼看?
川本:我沒有想到我的作品能翻譯成中文,寫這本書,並不是什麼光榮的故事,這不是一個成功的投手站上甲子園的故事,而是一個受到挫折、墜落的人的故事。
我當初也可以不要被炒魷魚,我是有選擇的,只要我願意把當時我知道的事告訴警方,我就能保命,但我沒有辦法做這樣的選擇,這就形同是要去密告很信任我的人,若是這樣選擇,我之後再也無法打從心底寫文章。最終我選擇不說,所以我被朝日新聞社革職。
現在回想起來,我還是覺得這是正確的決定,雖然之後過得很辛苦,經濟上有些困難,但是心態上我是問心無愧的。我當時沒有辦法做記者,我便開始寫文章,但也因為那樣的經驗,讓我嘗到了失敗的滋味,也讓我知道,自己並沒有什麼了不起。
從此之後,我關注的東西,無論是電影或是文學也好,我喜歡失敗者的故事,像是我喜歡下町,也是因為下町是一群失敗者住的地方,為什麼?因為我說過,除了發生兩次巨大災害外,下町也是能表現當年江戶文化(按:東京舊名)的地方,江戶被西邊來的長州藩和薩摩藩統治,才開啟了日本的明治維新時代,故江戶是個戰敗的城市,住在下町的人,就是失敗的人,即使到現在,相較於贏者和成功的人士,我更願意去關注失敗的人。
李:坦白說我聽到有點想掉淚。如果老師謙稱自己是失敗者的話,這讓我想起Leonard Cohen(李歐納•柯恩)的書《Beautiful Losers》,美麗的失敗者。我覺得失敗者的形象,反而突顯了體制的問題和缺憾,在《我愛過的那個時代》這本書當中,我們發現,有道德缺失的並非是老師本人,而是整個體制、甚至還包括反體制的社群本身。這本書在去年學運被大量閱讀不是沒有道理,因為這當中反映出的並不只是群起反抗的青年文化,也包含著對反抗者本身的一種自省能力。
這本書之後拍成電影,我前幾天也跟老師聊到,他說電影和書籍應該要分開看。或許電影比較強調事件的發展,而少了一點內心反省的深刻。所以希望大家能回過頭來讀這本書。老師自己也說,一開始對於電影過於關注事件本身,有點不太能接受,但他打趣地表示後來發現是由帥氣的妻夫木聰飾演,他就同意了。我聞言大笑!直說:「NO!NO!NO!川本老師也很帥,只是帥法不一樣啊!」(笑)

(圖片提供:新經典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