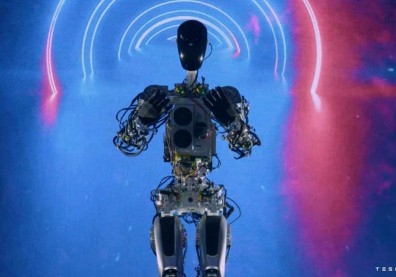沉寂多年的「愛盟」又動起來了。
這一批以「鬥性」頑強著稱的中生代國民黨菁英,再度重整出發,在今年五月正式登記為政治團體;時值國民黨內部主流派與非主流派權力競爭,分外引人注目。
特別是被視為與「非主流派」較為接近的「愛盟」,在成立宣言草案中說到:「如果朝野兩黨無法大步前進,滿足民意需求,本盟樂於見到其他健全的現代化民主政黨出現。」瞬時,引起不少的猜疑;甚至有人認為,想籌組第三黨的其實就是「愛盟」本身。
組黨爭端
追溯過去,「愛盟」的同志,以「保釣」結緣。在一九七0年代,保釣運動席捲海內外時,「愛盟」在海外與左派分子嚴陣對峙,高喊「只要有我在,中國一定強」的口號,以鮮明右派前鋒的姿態,支持中華民國政府。其後,部分盟員相繼返國,分散在黨、政、學界服務。
關於「組黨」的爭議,「愛盟」執行委員會主席陳義揚表示,以「愛盟」的專長、人力、物力,談不上組黨,也沒有組黨的意願與計畫。這位交通大學的教務長緩緩地說:「至少短期之內,組黨不是我們考慮的一個方向。」
事實上,「愛盟」自海外保釣運動、回台成立聯誼會,以迄於今的政治團體三階段,其組成的成員並非全然相同;以成立政治團體而言,內部就有許多爭論。
原「愛盟」聯誼會成員、現國民黨立委黨部總幹事朱大可自稱不願加入「愛盟」,以免為少數政治野心分子利用,做為晉階籌碼。他認為,「愛盟」不可能組黨,因為「愛盟」的盟員幾乎都是國民黨員,不可能與現存體制對抗。而且「愛盟」以知識分子為主,「他們都有專門職業,不可能放下手邊的一切,專門操作「愛盟」的政治事宜。」
一些政治核心分子,如行政院研考會主委馬英九、政大國關中心主任張京育等,過去均是「愛盟」的大將,這次都沒有加入改組後的「愛盟」政治團體。而亦是「愛盟」聯誼會會員的立委林鈺祥更表示,「愛盟」是國民黨的外圍組織,其基本主張在國民黨的主張之下,「如果「愛盟」不成為政黨,它的特色脫離不了整個國民黨的特色;而如果將來變成政黨,我也會留在國民黨,不會去參加「愛盟」的政黨。」他說。
外省勢力最後集結?
「「愛盟」要組黨,除非國民黨分裂。」焦仁和,這位被媒體記者認為貌似年輕時代宋楚瑜的總統府機要室主任說。
因此,在「愛盟」成立的第一天宣言草案審議大會上,經焦仁和堅持表決,主席陳義揚在「極不情願」的情況下,最後決定在正式宣言中,刪除上述那一段引起「組黨」聯想的文字。
從數量的角度來看,台灣住民八成是本省籍,但有二百七十餘人的「愛盟」,外省籍盟員卻占八0%以上,使得這一個改組成立的政治團體常被貼上「外省籍第二代集結」的標籤。
據「愛盟」執行委員之一的台大教授尹建中表示,盟員之所以多數是外省籍,有其歷史緣由。「當年在海外參加保釣運動的人,都是政治意識較強的人;而外省子弟因為多半有逃難的經驗,所以對政治的意識較強。」
身為「愛盟」執行委員會副主席的立委郁慕明則認為,「愛盟」並無省籍意識的問題;今天省籍問題被刻意挑撥出來,就是一種歧視。
但在台灣政壇及社會「本土化」的潮流下,同為執行委員之一的中視新聞部副理張勤,仍感慨地說:「天氣非常寒冷,我們只是聚在一塊兒取暖啊!」
因此,儘管焦仁和嚴厲地斥責:「誰挑起省籍問題,就是歷史的罪人!」也仍然擋不住外界的刻板印象。
混血情結
爭議點之三,是「愛盟」高度的國民黨色彩。這個特徵,部分盟員坦承不諱;但部分盟員則解釋,只是內部一些成員對國民黨有「堅強的認同感」。「愛盟」的非國民黨籍成員,亦為民權時報社長謝正一卻指出:「如果這個堅強的認同感仍然擺在「愛盟」裡,只會使「愛盟」變成國民黨的次級團體。」
因此,儘管「愛盟」主席陳義揚表示,歡迎不同黨派、不同省籍的人士加入「愛盟」,以超越國民黨,讓更多的人監督執政黨。但「愛盟」內的非國民黨人士仍然非常稀罕。
同樣是外省第二代子弟的民進黨籍立委林正杰指出,「愛盟」是一個國民黨右派老團體。因其「反共愛國聯盟」的歷史淵源,使得「愛盟」更像一個兄弟會;盟員聚會時,不時回憶過往,談論保釣運動的「童年往事」。
「畢竟人老了都會懷舊,聚在一起難免唏噓過往。」尹建中坦白的表示,但若過分的懷舊,就會造成新盟員沒有歸屬感,無法融合。
而「愛盟」盟員本身對更新團體所造成的異質性,多有難以平衡的矛盾;既希望「愛盟」能藉新血加入,以防止團體老化,又礙於「保釣情結」,冀望「愛盟」血統純正。
反共定位模糊不清
一九七八年,美國國務卿范錫訪問中國大陸,中共與美國建交的趨勢益顯明朗;同時,前台大哲學系教授陳鼓應等人,在選舉期間,發表當時看來頗「激進」的改革言論,批評政府無能,國家的民主、法治不夠,使得已陸續回國的「愛盟」盟員再度結合,反擊陳鼓應。
中美正式斷交後,「愛盟」在台北成立聯誼會,二十多位盟員不時餐敘,間或舉辦專題研討;早年,為許多留學生所熟悉的「大鵬營」,便是由教育部國際文教處出錢、「愛盟」出力所舉辦的。
在這次靜極思動、組織政治團體以前,「愛盟」的政治色彩,實際上,已被聯誼性沖淡許多。
「反共」、「愛國」自保釣運動迄今,一直是「愛盟」秉持的原則,然而時空的轉移,政治環境的變化,使「反共」的定位早已模糊不清。
焦仁和表示,當年「保釣」左右派對峙的情形,絕對是拚個「你死我活」;但今天,「反共」沒什麼值得標榜的,因為已經很少人願意接受共產黨的統治。所以今天的「反共」,可以採取一種和平的、漸進的手段;但基於「反共」是「愛盟」的原色,所以「我還是贊成在「愛盟」中旗幟鮮明地標示出來。」焦仁和說。
時代在變,政治生態環境也在變,「「反共」已不是這個時代的語言,大家都往大陸跑,誰還講「反共」。」林正杰批評說,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早在六0年代就說「非共而不反共」,非常實際。所以「愛盟」延用當初的名稱,並不一定符合現在的事實;因此,除非它的本質改變,否則很難有大作為。
「政治上向來少講舊情綿綿。」林正杰說,過去大家一起印傳單、搖旗吶喊;今天各人利害、背景不同,誠如作家張系國在追憶「保釣」的「昨日之怒」一書中所說:「一個人只能年輕一次,時間一旦過去,熱血逐漸冷卻,激情的心境就再難追尋!」
「愛盟」的再出發,源自於國民黨高層的分歧,雖然它結合了一批憂時憂國的知識分子;但是,在當前的局面中,「愛盟」能為自己凝聚出何種新的使命與共同的方向?對這個社會,能著力的空間又將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