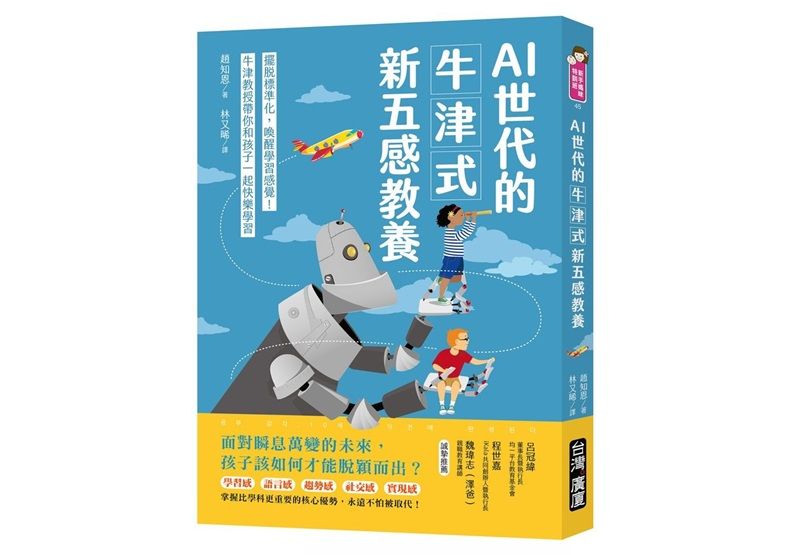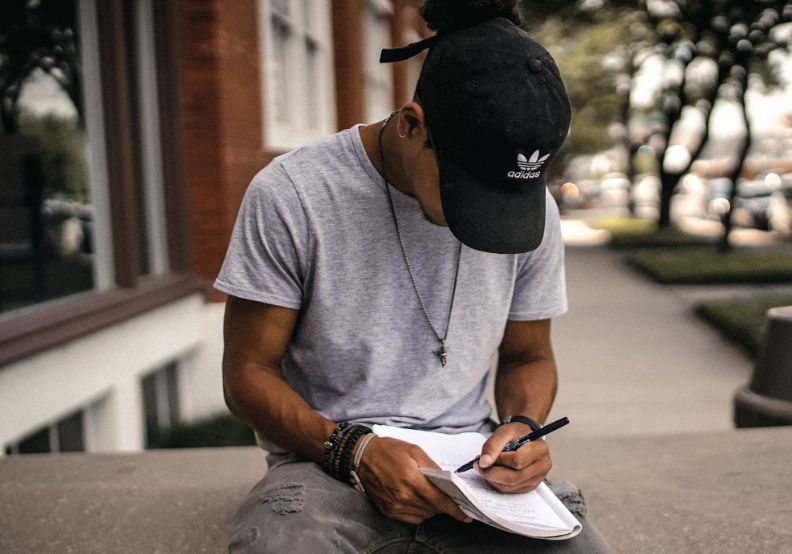作為現代父母,「該為孩子選什麼學校?」「要寫大家都在寫的評量嗎?」這些問題彷彿魔咒,總是緊箍著每顆關心子女教育的父母心。然而,我們在焦慮之中往往忘記:「每個孩子都擁有獨一無二的特質」,當將來沒有「標準」可以吻合,懂得發揮這些「不同」,才更能夠創造優勢。(本文節錄自《AI世代的牛津式新五感教養》一書,作者:趙知恩,台灣廣廈出版,以下為摘文。)
在牛津大學的新生面試中,每年都會遇到優秀的學生。在過去14年間,每到12月的第一個星期,就是學校的面試週,而我擔任東方研究學院的招生委員會主任已有7年光陰,也看過了無數份自我介紹。
我發現,私立學校的學生們會提交明顯受過指導的面試資料,在面試時,他們一聽到面試官的提問,就會馬上滔滔不絕說出演練多次的回答,但是,在牛津大學,9成的面試官都不喜歡這樣的學生。
有些學生感覺好像讀完了這世上所有的書,也有些學生信誓旦旦說讀過我的書,但只要多問幾句,就會馬上發現他們只是瀏覽過幾頁而已。我也看過很多擁有非常厲害的獲獎經驗,資歷華麗的面試者。
然而,牛津大學的教授們對於華麗的經歷並不感興趣。比起讀過一百本書,我們對於只看過一本書的人更感興趣;比起豐富的經歷和獲獎經驗,我們對於擁有深度的想法,深入研究過自身興趣的人更為好奇。
換句話說,我們希望尋找的,是對特定領域展現出豐富熱情的少數人才。
在一次入學面試中,我遇到了一名叫湯米的學生,我問他為什麼想在牛津大學讀書,湯米回答,因為他想成為有錢人。通常很少有學生會這樣回答,但湯米理直氣壯地述說了自己的故事。
他說,家裡沒有人上過大學,他想好好讀書,把爸爸的汽車修理廠經營得更好,然後成為有錢人。他對自己想要的東西既坦率又堅定。面試官們給湯米打出的分數,比在伊頓公學等名校接受面試培訓的學生還要高。
湯米以優異的成績從牛津大學畢業,現在成功地經營著事業,就像在面試時一樣堅毅、理直氣壯和幸福。湯米或許是所謂的怪胎學生,但是,這正是牛津大學在等待的人才──
能夠坦率表達自己、具有膽識的人,這些人,才是未來大學、社會真正需要的人才。
(延伸閱讀│頭腦好不代表很會念書!哈佛學生都有一項特質:「RQ」高)
將來的可能性,遠比至今取得的成就還要重要
比起在良好環境受到良好教育的乖寶寶,牛津大學更想尋找的是,在艱困環境中雖沒有受到特別照顧,但只要好好栽培,就可以長成大樹、像原石般曖曖內含光的人才。
為了申請牛津大學,通常需要在被稱為「A-Level」的英國大學考試中,獲得三個科目的A,但偶爾也會有分數未完全達標的學生申請。
然而,這些學生被錄取的情況並不少見,牛津大學也會提供全額獎學金給家境困難的學生。獲得獎學金的學生多會在成功後回到學校捐款,回饋給和自己以前處境相似的學弟妹。
和英國孩子不同的是,亞洲孩子們熱衷於累積證照,似乎是為了證明自己的能力,希望在考試、比賽上取得客觀的分數或成果。
亞洲特有的證照文化從童年就開始了。鋼琴練到徹爾尼第幾首、跆拳道黑帶、英文幾分等標準,逐漸形成了「至少要達到某種標準」的壓力,遺憾的是,這不僅奪走想像力成長的空間,而且就算取得了各種證照、考試分數,也很難真實反映出孩子的能力。
為了考試而學的知識,贏不過出自興趣學習,或是累績豐富經驗而內化的知識。
在孩子的教育上,我想家長的角色,應該是尋找出孩子能夠真心投入的事物,並幫助他們接觸那件事。這樣一來,在某個時刻,我們就會發現孩子神奇地具備了無人能及的、真正的「力量」。
(延伸閱讀│孩子不願自主學習?首爾大名師:頂尖學生都是「這樣讀書」的)
懂得與AI共處的孩子,並不擔心被取代
現在的孩子是「AI原住民」
在新冠疫情期間,學校暫停了實體課程,將近兩年的時間裡,我的小女兒潔西有3分之1的課程只能在線上進行。雖然現在已恢復線下課程,但大部分學校作業仍是在網路上完成。
對潔西而言,網路已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她從小就能熟練操作電腦和平板,甚至在還不會寫字時就開始使用表情符號,最近還會和朋友在元宇宙平台 Roblox 上玩遊戲。
潔西也習慣了自動拼寫修正功能,和朋友或遠在海外的長輩聯繫時,比起實際見面,更常透過視訊交流。這一切都讓我意識到,無論形式如何,這些孩子的生活始終與數位空間緊密相連。
「數位原住民」一詞是由馬克‧普倫斯基於 2001 年提出的。他在《數位原住民,數位移民》(Digital Natives, Digital Immigrants)一文中,將數位原住民定義為「在電腦、手機和其他數位設備環境中成長的年輕人」。
隨著數位設備的多樣化和技術的迅速發展,數位環境已發生了巨大變化,因此,我想以「AI 原住民」一詞來強調這種轉變。
我認為,包括 Z 世代(1997至2010 年出生者)、α世代(2010 年後出生者)以及未來的世代,都屬於「AI 原住民」。對他們而言,AI 是夥伴,VR 是遊樂場。
這些科技在語言學習、程式設計和寫作上都產生了巨大影響。然而,部分國家卻立法禁用 ChatGPT,業界擔憂這種做法會背離時代潮流。
對 AI 世代的孩子們來說,這樣的限制就像在紙筆時代禁用字典,或禁止千禧世代使用 Google等搜尋引擎。我們要做的不是選擇是否使用 AI,而是教育未來世代如何善用它。
我們應學會接受 AI 的幫助,但不完全依賴它,並培養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因為AI在某些情境問題下,可能提出不道德的解決方案。
最近在教導「AI 原住民」時,我意識到自己能教的並不多,因為孩子們對 AI 的理解遠超過我。在捷克參加為期一週的 AI 集中研討會時,我原本計畫教授各種 AI 工具的使用方法,但參加的 20 多歲年輕人僅用一小時便能輕鬆探索數位空間,幾乎不需要我的協助。
我發現自己在這個領域的角色不是教育者,而是引導者。Z 世代和α世代對數位空間十分熟悉,AI 對他們而言已是生活中的基本技能,而且透過充分運用 AI,他們能夠更有效率地生活。
(延伸閱讀│職場最優秀人才根本不存在?據統計:團隊有「這2項」特質表現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