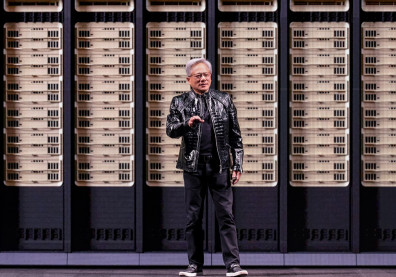這一陣子,凡是出國離開台灣的人,無論是公差、探親,還是旅遊,回來後都有個感覺:在國外真好,耳根子清淨多了,再聽不見政治人物每天聲嘶力竭的叫囂、謾罵、攻訐,眼不見心不煩嘛!等到一回來,重入鮑魚之肆,滋味實在不好受。
世界上搞民主政治的國家比比皆是,無論是老牌的還是新興的民主國家,在民主政治的活動中,恐怕找不到像台灣這麼無秩序、無規範的。諷刺的是,民主本應就是一種秩序規範,現在我們以邪惡的手段去追求善果,能尋得到嗎?
台灣的政治人物,在選舉時把大話說盡,選完了不去做,好像完全忘了,而選民也不要求他們兌現。寖假以還,就構成了今天我們這種「具有台灣社會特色」的民主政治。
言於行之間的關係,世界各國的賢哲多有討論,孔子在這方面的發言也很多。《論語》「憲問」篇有云:「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現在一般的解釋是:君子認為,如果自己說的多而做的少,是一件可恥的事。但有學者以為,這句話中的「而」字為「之」字之誤。全句應是「君子恥其言之過其行」。意思是說:君子覺得,若是說的話自己做不到,是一件可恥的事。換言之,君子不說自己做不到的話。這種解釋,似較前者為好。
「憲問」篇還有孔子的另一句話:「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就是說:一個人若大言炎炎而不知難為情,他說的話多半是做不到的。蓋想到就說的人,完全未經過思考,脫口而出的話,怎能有實踐的誠意?
在「里仁」篇,孔子提醒當代的人:「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古代的人不隨便發言,因為他們以來不及實踐為羞恥。當然,古代的人不可能每個人都達到這樣的標準,孔子意在為世人樹立一個典範,供大家效法。
同在「里仁」篇,孔子又說:「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依照孔子的看法,做為一個君子人,在言語上應謹慎,不可放縱自己,甚至遲鈍一點亦無妨,但在行動上則應快速有效。
孔子這類的想法,以在「為政」篇裡的幾句話最為典型。「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孔子告訴子貢:有什麼主張、念頭,別忙說出口,自己先去做。做到了,再說出來,這才配叫君子人。
孔子已過去幾千年,但是君子還是後人應該追求的吧!君子的標準固然不容易訂,惟言行一致總是應有之義。尤其是競選公職的政治人物,亂開支票,明知自己做不到,還說得像真的一樣,這不是存心行騙嗎?若是一個國家的領導階層都行騙術,這個國家能好得起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