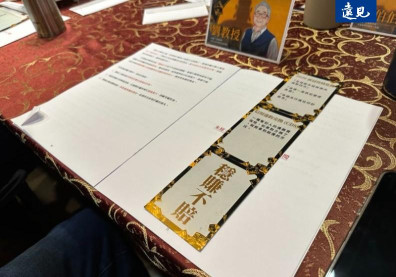●在我們面前只有病人,哪有中醫、西醫的分別?病人需要我們用什麼樣的方法治療,如此而已。你用中醫、西醫的方式看,就像用兩面透鏡去看。從透鏡看過去,可能局部扭曲,或因學得不修透徹,看到的病人也許會走樣。由中西醫兩面鏡子去看,或許你會想:病人怎麼會長成兩個樣子?……我們對人體還有不知道的地方。
江烈欽(中國醫藥學院附屬醫院中醫科醫師)
●我不認為醫學分中醫、西醫,醫學只有主流與非主流,一百年前西醫的治療跟今天的中醫差距很小,也是用草藥,沒有抗生素、輸血、打針及超音波,所以,理論上,醫學就是醫學,最終目的以及醫師的第一優先,都是在解除病人的痛苦。
洪傳岳(前陽明大學傳統醫學研究所所長、陽明大學教務長)
羅雯一直有經痛的毛病,看過婦產科卻找不出病因,看了中醫後,疼痛減輕了許多。有一次,她下腹部不適再去找中醫診療,卻毫無改善,後來去找婦產科醫師,才知道是子宮頸發炎與結腸消化不良。
對台灣民眾來說,「就醫」是一段自我摸索的過程。醫療體系裡存在著中醫、西醫兩套不同的系統;絕大部分民眾的就醫習慣是先找西醫,再看中醫。由於病人缺乏獲得正確醫療資訊的管道,什麼病找中醫、什麼病找西醫,何時找中醫、何時找西醫,病人自己下判斷;台灣高喊多年的「中西醫結合」,由病人自己實踐。
當主流醫學不能完全解決問題時、中醫成為人們自力救濟的首要途徑。但是,病人真的知道如何正確選擇中醫嗎?首先,來源多元、良莠不齊的中醫師就讓人眼花撩亂。他們有些是當年大陸來台的老中醫,有些則是拜師學藝、經過特考的中醫,還有受過正規學術訓練、由中國醫藥學院培養出來的中醫師和學士後中醫,以及一支從大陸各中醫藥學院畢業回來的隊伍。
這張中醫師的分布圖上,從名醫到江湖郎中,存在著兩個極端。長庚醫院中醫科內科主任楊賢鴻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外行的病人的確難以選擇;有的醫師因看診經驗豐富成為名醫,但名醫的代價是嘗試了很多錯誤,犧牲了很多人。學院畢業的人由於缺乏臨床訓練,醫術不見得比較高明。從大陸「取經」回來的中醫師就表現得比較好嗎?楊賢鴻說:「大陸基礎教學不錯,但是臨床是不是這麼好,學生是不是認員學,完全不知道。」
瞭解中醫,必先建立共同語言
外行人霧裡看花,內行人評判好壞的標準以及自我監控的模態在哪裡?對於西醫界與病人而言,有一套標準與監控系統做為檢驗工具之後,討論「醫療」才有意義。那麼,中醫能否提出一個可供解釋和評量的標準?誰來規約中醫?
要瞭解中醫,首先遇到的間題是欠缺共同的語言。一位中醫系的學生跟五位中醫師討論問題,五位醫師提供五套理論,令他茫然不已。當中醫之間都欠缺共同的語言時,西醫與大眾自然無法公平地認識中醫。
在這種對中醫只有片面認識的情況下,人們大都倚賴機緣或運氣選擇中醫。有些西醫排斥中醫,使得病人在西醫面前連提都不敢提;有些心態較開放的醫師在無法提供病患更滿意的治療時,會建議他們找中醫試試。而民眾在面對疑難雜症時,也會將希望寄託在中醫,視它為萬靈丹。
罹患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清蘭很容易感冒、咳嗽,一不舒服就去台大看病,二十幾年來,咳嗽只要一發作都非常痛苦。當親友告訴她,彰化有一家中醫的祖傳秘方非常有效時,不禁燃起一絲希望,結果跑了好幾趟,花了錢,病情依然不見改善。
西醫不會因成功治癒一、兩個案例,就宣稱某療法有效,必須達到統計學上的標準,才會獲得認可。但中醫的治療標準不一樣,缺乏有意義的統計,只要是有效的個案就被凸顯,成為「治療上的奇蹟」。一位不願具名的醫療行為觀察者表示:「這很奇怪,有效與無效沒有客觀的評價。」
使用中醫,必先學習正確方法
現在的醫療問題顯然已經不是單純的中、西醫就能解決。大部分西醫幾乎完全無法理解傳統中醫的語言。台北市立中醫醫院院長張恆鴻表示,很多醫師似乎不瞭解病人的問題在哪裡。他舉例,一位病人北上求醫,他對醫師說「我肝火蹴大」,結果挨罵:「肝裡底哪侑火」。
中醫本身的問題,以及中西醫之間區隔分明,毫不對話、彼此充滿偏見的關係,讓夾在中間的病人不但無法左右逢源,反而愈看愈迷惑。腳傷的彥文看了骨科很久,西醫說需要長期復建,但是舊疾並沒有改善。於是他陸續拜訪了三家中醫傷科,四個醫師有四種以上的治療方式,他心中充滿不解。
民眾中西醫交錯尋求的醫療行為愈加普遍,讓醫師面臨比過去更複雜的局面。例如,病人送到西醫急診,結果是吃了十全大補湯出問題。另一個病人早上去看中醫,下午去看西醫,他拿著中藥問西醫該不該吃?才接受針灸的病人向西醫表示情況有改善,明天要不要去?這些例子層出不窮,「十全大補湯?急診醫師要不要去想這是什麼?民眾提出關於中醫的問題,西醫要怎麼回答?」張恆鴻質疑。
在現代醫療系統下運作的中醫,面臨更多因醫療體制限制與主流醫學影響所造成的問題。簡單說,病完全無法離開西醫。在健保制度、醫療架構及市場的規範下,病人傾向先找西醫;連診斷書、出生或死亡證明書也都由西醫開立。
是否能瞭解現代醫療架構下所定義的疾病,也成為中醫面臨的最大問題。比方說,病人向中醫師詢問B型肝炎及肝癌的治療方法時,醫師是否瞭解那是什麼疾病?如果求診的病人正在服用類固醇、免疫抑制劑或荷爾蒙等藥物,會發生什麼影響?再開中藥給他,又可能造成什麼問題?可以停藥嗎?先吃哪個,後吃哪個?病人療程到哪裡?張恆鴻指出,這是現代中醫無法躲避的問題,「我不認為中醫師的學術與價值水準需要西醫來判斷,但是中醫必須理解現在面臨的新情況。這些問題就算是常識也要懂,更何況你是要去服務客戶。」
因此,回歸正統教育訓練中醫,以及培養一群能促進中西醫對話與結合的醫師,成為部分醫界人士試圖解決這種醫療困境的方式。
中西醫都需要再教育
中醫需要依自己學術的標準,建立一套客觀的訓練模式,目前亟待建立的是中醫學校與中醫院。中國醫藥學院附屬醫院中醫科醫師蕭恆毅表示:「要使用中醫,就必須學習如何正確使用它。」陽明大學教務長洪傳岳認為:「中醫需要回歸正統訓練,變成正統之後就沒有秘密可言,只要花工夫大家都可以學,然後發揚光大。」
至於中西醫之間要對話,就得建立共同的語言,理解彼此是第一步。馬偕醫院小兒科主任沈淵遙表示,從基礎理論、動物實驗、化學實驗到人體實驗,西方醫學已經建立了一套比較完整與嚴格的模式,東方醫學則比較偏向另一套形而上的思考模式,彼此都不願意打破藩籬,如果彼此願意瞭解,就會發現,中醫講五臟六俯,西醫講解剖結構,基本上都是在描述身體器官的結構,只是傳統醫學因當時無法解剖,只能以傳統的思考角度與語三言來陳述。
中西醫都需要再教育。張恆鴻指出:「雖然現在不可能將所有中西醫的水平拉到彼此認可的程度,但是透過教育,十年後,這些醫生應該能聽懂對方的語言,醫學院勢必要放入中醫的課程。」沈淵遙則認為中醫應該接受現代醫學與科學的方式,做一些研究、討論與訓練。
也許,縮減中西醫的差距,開發中醫真實而清楚的面貌,才能為徘徊在中西醫路口的人建立一些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