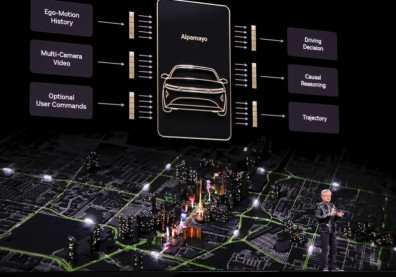80 年代,未來是一條通往城市的公路,青年離鄉,窩居在霓虹都市裡,高唱「台北不是我的家」;現在,青年依舊懷抱夢想,卻踏上反方向,揮別城市的熱鬧喧囂,在山海、鄉野、村落,找到用心生活的理由。
「一定有一種生活,可以不再被時間或金錢逼迫;一定有一種人生,在做自己的同時,也能夠貢獻社會。」拒絕朝九晚五上班,塩見直紀提出「半農半X」的新生活型態。
半農半X,就是在農耕之餘,找一個熱愛的興趣、專長或志業,以農務勞動養活自己、量身訂製「X」餵養靈魂。對於原本就來自農村的農二代,返鄉,成為令人心動的選項,不僅為了繼承家業,他們懷著憨膽,闖出有別傳統的經營方式。
社群協力 奇客邦
一群怪傑的理想國度
返鄉青年、打工換宿者,或者只是流浪中暫時歇腳,歸人和過客在花蓮玉里相遇,共組帶著怪奇和實驗精神的「奇客邦」。
夏日的玉里夜晚,在半數房舍未見燈亮的寂靜眷村中,有間平房不時傳出歡聲笑語,偶爾伴隨著吉他的彈唱聲。
這裡,是奇客邦(Geektopia)的祕密基地。1 年多前,它還只是眷村裡一間破舊平房,沒水、沒電;現在,殘破老屋搖身變成溫馨的工作室。每天晚上,奇客邦的成員都會聚集於此談天說地,分享著彼此的生活點滴。
奇客邦發起人阿竚,是個70 年次的攝影師,不過目前的「正職」卻是「藍色小山」的小老闆兼主廚,因為父母年事已高,身為獨子的阿竚,9 年前決定返鄉接下這間和他同齡的店,並決定以自己的餐飲專長,將牛排館轉型為歐義餐廳。
阿竚想帶來的改變不僅於此,更想集結其他返鄉的年輕人,共同為故鄉投注新的能量與改變。白天,阿竚扮演餐廳小老闆和主廚的身分;晚上和假日的空檔,則用影像記錄玉里的這些人、那些事,幫助大家重新認識自己的故鄉。
同為奇客邦一員,目前是「農二代」的小劍劍補充說,「一開始返鄉最深的感觸就是,一個年輕人在鄉下好孤單喔。」隨著熟識的朋友相繼回來,在一次偶然相聚下,大家就組成一個非營利的返鄉青年工作室,奇客邦因此成立。
在台東縣東河鄉,四面環山的阿拉巴灣,位處偏遠、交通不便,鮮少有遊客造訪。這裡沒有便利商店、超市,甚至沒有菜市場,為了幫助偏鄉小朋友,奇客邦決定從玉里出發,前往泰源村進行分享物資的小旅行。
在阿竚的鏡頭下,這趟小旅行有歡樂,有溫馨,並為泰源在地一個專屬失親、單親孩子的課後天堂「泰源書屋」,記錄下一個溫柔而美麗的故事。
場景拉回玉里的西瓜田,一群人正聽著綽號西瓜大王的阿強,解說如何挑選好西瓜,一邊品嘗甜而多汁的當季在地水果,瓜田旁還有樂團演奏,還搭配打西瓜的趣味遊戲。
「藉著社區小旅行的活動,可以讓更多人認識花東與玉里,」奇客邦成員之一、也是國小老師的謝家豪,道出奇客邦對未來的各種期望。
除了用微電影記錄玉里的美食、景點、職人、產業,藉此吸引更多人前來,也希望能活絡在地經濟,為年輕人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他們也打算活化鎮上閒置的老屋,招募各類專長的換宿夥伴,這些正在進行或即將展開的計畫,正在凝聚一股改變玉里的力量。
食藝傳承 美好花生
守護土壤裡的珍珠
放下公事包、脫掉高跟鞋,年輕夫婦回到花生田裡揮汗農作、在高溫鍋爐前舉鍋鏟快炒,傳承媽媽真材實作的手藝。
花蓮,鳳林。
夏日,清晨5點多,遠方山頭,燦爛朝陽乍現。
梁郁倫和丈夫鍾順龍全副防曬武裝(斗笠、斗笠巾、袖套、手套),走進自家花生田,開始進行花生採收。
栽種花生的農事,1年可分二期,第一期是2月底種,7月初採收;第二期是7月底種,11月底採收。
梁郁倫說,雖然可用機械採收,但是機器不易前行的邊界地帶,就得靠人力進行。土鬆處,可用雙手將花生整株連根拔起,「至於土壤稍硬的地方,就須一手抓住整株花生用力上拉,另一手用小鋤頭順勢鬆土,拔起來後,稍微搖晃讓土壤鬆落,手掌再抓住落花生,輕輕一轉就摘下了。」
花生採收完成,並不代表大功告成,另一項重頭戲「日曬」,才要登場。「採收下來的花生,必須即刻鋪在曬場,開始翻耙。要點有二:第一,能耙得愈薄愈好;第二,翻耙的次數要勤快,在烈陽底下,乾燥的效率才能相乘,」梁郁倫指出:「曬花生時,要時時注意天色,遇到了午後雷陣雨,如果來不及蓋上防水布,淋濕的花生可就要多曬上幾日了。」
這對揮汗農作的年輕夫妻,2009年之前,他們還是都會上班族,活躍於媒體和文化圈。如今,他們放下公事包和高跟鞋,雙腳緊緊踏在故鄉的土地上。
梁郁倫是南投埔里人,在倫敦念藝術管理碩士時,與在當地攻讀影像創作的鍾順龍相識相戀。返台後,梁郁倫在基金會負責藝術展覽,鍾順龍則任職於報社當攝影記者,兩個人在台北職場擁有各自的舞台。
梁郁倫回憶,在英國留學時,她就經常懷念家鄉菜,當她知道婆婆的炒花生手藝可能從此失傳,便和丈夫討論是否該返鄉,接手這項具有農村特色的傳統食藝。
「以前在台北工作時,對自己所吃的食物,不是很了解,」梁郁倫坦言,跟著婆婆一路學下來,看她只選用當期花生,在陽光下自然曝曬,而且為了避免與空氣接觸而變質,下鍋前才將花生剝殼,種種用心,就是為了保持品質以及口感香氣。
「懂得什麼是好東西,才能享用好東西,」梁郁倫說。
鍾順龍說,小時候因為家裡開農機行,衣服上總是有著機油味,對於農事一直很排斥。沒想到,離開了故鄉,甚至飛到地球的另一端,繞了一圈,最後還是倦鳥歸巢,回到他最熟悉的農田裡,找回了生命的重心。
茶鄉旅行 吉林茶園
茶園飄散柚花香
熱愛摩托車旅行的茶園少東返鄉接班,就像小綠葉蟬吸吮後,茶葉飄散蜜香,四代茶業有了嶄新變化。
採訪前夕,彭瑋翔才剛從蘭嶼自助旅行回來。一頭長髮、古銅膚色,說起在蘭嶼騎機車、游泳、拜訪在地作家夏曼.藍波安的種種,眉飛色舞,彷彿孩子般的興奮。
不過,一坐下來執壺煮茶,彭瑋翔整個人又顯得氣定神閒了。
水燒開了,倒入茶葉中。茶葉在熱水中舞動,彷彿從悠長的夢境醒來。彭瑋翔再將金黃茶湯傾注杯中,熱氣微微升起。
款待客人的心意,就從奉上一杯茶開始。
當天他泡的第一杯茶,是吉林茶園的招牌──「蜜香紅茶」。這也是瑞穗舞鶴一帶,最具代表性的茶。
彭瑋翔說,蜜香紅茶會在花東地區盛行,跟自然環境密不可分。茶區地處北回歸線,濕熱的夏天成了蟲害溫床,政府又推廣無毒農業政策,以致茶蟲很多。不過,茶農發現,有一種茶蟲,叫做小綠葉蟬,茶葉經牠吮吸後,產生化學變化,散發蜜香和花果香味,以這種茶葉製作的紅茶,就是「蜜香紅茶」。
74年次的彭瑋翔,有著客家、原住民血統,是第四代茶農,從小在農家長大,課餘之間會到茶園、製茶廠幫忙,做一些簡單的雜務,但是對於農事並沒有特別的興趣,家人也沒有把他當接班人栽培。
退伍前夕某次休假,他陪著父親巡視茶園,父子商量下,他決定接手家裡的茶園事業。這個決定的背後,代表的不只是一份工作,也是一種生活型態的選擇。
每年3月是柚花盛開的季節。柚花潔白如雪,散放甜香芬芳。包括了吉林茶園在內的業者,趕緊摘取柚花,與當季春茶一起烘焙,製作出7分茶香、3分花香的柚花茶。
2011年起,他趁著柚子花季時節與民宿合作,推出「柚花季深度體驗」。2天1夜活動中,帶領團員走訪柚子園、茶園、泡湯、喝鮮奶、泡溫泉。一方面滿足他過去想當領隊的心願,另一方面也透過深度小旅行,讓更多人認識故鄉的美好。
接班第5年,彭瑋翔交出亮眼成績單。2013年瑞穗鄉農會蜜香紅茶競賽,吉林茶園在15項紅茶項目中奪下10面金牌。
「其實,吉林茶園一直是優良茶比賽的常勝軍,」彭瑋翔說,不過,父執輩做茶,比較重茶香是否濃郁,而他更重視茶葉喝起來是否健康,因此也盡量要求自家以有機農法來種茶,「因為現在的消費者不只在乎好喝,更要喝得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