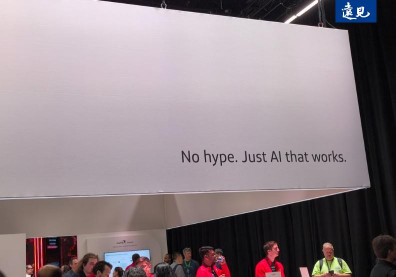不要再多了,有一種少,是把最好的留給你。
快速都市化的腳步下,綠色的山林已然逝去,怪手無情的挖著大石,沙塵漫天、轟隆作響,向深山挖出一條條水泥道路,文明的傲慢,擅自侵入大自然,步道水泥化覆蓋住泥土與樹根,棲地遭到切割、逕流沖刷加劇,在爭取快速、開發的思維下,我們正付出山林崩解的代價。
一鋤頭、一木頭,用雙手觸摸土壤,手作步道展開自己和對大地的探索,在親近郊山的同時,放下身段、傾聽山林,嘗試扭轉過去使用山林的態度與經驗,彷彿引領著人們走向山的祕境。
蜿蜒曲折的動線與美景,是內山裡的綠色小徑,訴說著台灣這片土地近百年來的變遷與生活足跡,而路的遠方,是透過與土地深層的互動,反思文明的傲慢,促發環境的覺知,勾勒出一幅公民參與的畫面。
一條走向未來的步道
有多久沒有好好走路?是否已經很久沒有走進山林,細細品味空氣中的芬多精,總是忽略了自然千變萬化的繽紛。生活的快速伴隨著經濟開發的節奏,讓雙腳脫離了土地的真實,忘了珍惜得來不易的自然美景,於是看盡風華的歷史痕跡,正一點一滴的消逝。
電影《看見台灣》,以令人驚豔的山林美景揭開序幕,連綿的山峰,像是通往祕境的天梯,成為城市迷人的天際線,保留了許多台灣山林的美景,令人屏息。然而畫面一轉,映入眼簾的是光禿的山壁、崩塌的土石,過度開發的土地承載,訴說著這塊土地的美麗與哀愁。
千里步道協會副執行長徐銘謙,是台灣山林的守護人之一。台灣是山林之島,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超過260座,密度之高,堪稱世界之最,但是在921大地震、莫拉克颱風無數的災難之後,我們看見的是柔腸寸斷的山脈。
人類文明的過度開發,讓福爾摩莎的美麗讚嘆,成了一場歎息。
如何守護山林的美?徐銘謙決定自己找答案。2007年,她遠赴美國阿帕拉契山徑,學習手作步道。在全長3400公里的天然土徑上,沒有水泥,用最天然的落葉為步道褥席,自然成型的枕木,是最好的階梯,也是對生態最好的維護。徐銘謙發現,把自己置身在山林中,你才能知道山需要什麼,學習「像山一樣思考」便是最好的答案。
她將答案帶回台灣,一路走來,徐銘謙挽起袖子、彎下腰,領著志工們,用行動追尋著自己理想中的山林。她想保留山林裡原始的風貌,守護步道的天然鋪面,避免不當水泥硬體、鋼構工程入侵山林。
整齊的水泥台階沿著山脊一路延伸至山頭,這是許多山間步道的畫面。陽明山坪頂古圳的天然安山岩被挖除,取而代之的是花崗岩水泥石階,山林工程化的比例愈來愈高,增長速度愈來愈快,處處可見的欄杆與平台,留下大興土木的痕跡。
長期觀察山林的變化,徐銘謙發現台灣許多步道面臨過度工程化的困境,以台北市郊山步道為例,水泥化高達75%,毫無人工鋪面的自然步道僅剩10%;新北市的水泥步道不到30%,但是人工建設比率超過60%。讓她心驚的是,這些數據,每天不斷的增加。
而透過步道運動,徐銘謙想讓更多人與自然和諧互動,她希望能喚起人們對環境使用的反思,讓步道使用者成為行動公民,在參與的過程中,學習傾聽與對話,達成對台灣國土共同的想像。
蜿蜒的步道,像是一種途徑,徒步走過後,看見的會是一個新的世界。而徐銘謙正以一種細微但直接的方式,拼湊出她的山林拼圖。
步道第1站:找回山林故事與記憶
走進台北市的福州山公園,順著水泥做的步道往裡走,一個右轉,轉進了綠意盎然的碎石步道。這段碎石步道,僅僅是將大碎石、泥土、小碎石,均勻混合後鋪平;以木頭及石頭施作了排水邊溝,讓水流得以排出,避免造成泥濘積水。
步道一旁的姑婆芋上,台北樹蛙沉沉的睡著,幾隻紅嘴黑鵯在樹上歇著,偶爾還有幾隻人面蜘蛛掛在矮樹之間,織羅了緊密漂亮的網。
這是徐銘謙帶領志工手作的步道,一條取材自然的生態工法,所施作的山間步道。這條步道,保留了生態豐富性,彷彿進入台北近郊的世外桃源,而這正是徐銘謙想留下的山林記憶。
每一條步道,就是一個精彩的故事。徐銘謙聊起每條步道的差別和獨特的工法技藝,顯得特別興奮。
從暖暖通往十分、雙溪有一條古道,陡峭斜上,石階走來卻略嫌狹窄,原來在日治時期,先民利用這條古道挑著扁擔做買賣,石階的寬度設計,是讓一公尺半的扁擔剛好能通過,而先民利用扁擔向上彈起的瞬間,向上邁步便能稍微省力。因此走在暖暖古道上,便能遙想村民挑起扁擔,將汗水沿途灑落山路上。他們或許也曾在越嶺後,觀看同一片山下美景,並且在拾階而上時,找棵大樹歇息。
自然中的每一個細節,都能看見先民的智慧、歷史人文的痕跡。但我們總因忙碌與快速,而錯過太多緩慢呼吸的機會,甚至任由過度工程化的水泥重重包裹住樹幹,難以喘息。
步道第2 站:拉近人與自然的距離
台灣的美,來自鬱鬱蒼蒼的山林,卻鮮少人知道,台灣超過3000 公尺的高山,有260 座以上,密度非常高。或許這也反映了我們對於自己擁有的自然財富,有多冷漠。
徐銘謙說,人們將城市裡的舒適、方便、安全帶入山林。用水泥鋼筋及許多硬體設備框出了一個自以為安全的世界,鋪上階梯才方便好走、設置欄杆才有安全感,卻忽略了水泥步道常常裂開損毀、鋼筋外露反而更加危險,人和自然的關係愈來愈遠。
而參與手作步道,像是一場環境教育,徐銘謙想將人帶回山林,重新讓人與自然互動。
她想起自己第一次在阿帕拉契山脈參與步道施作時,滿臉的問號及茫然,3 天後,卻發現自己看待山林的眼光有了轉變,像是戴上了一副眼鏡,看清楚了每個自然細節,她開始注重步道的坡度,觀察向陽背陽的位置,重新開啟了和山林對話的機會。
每一次的對話,都是一場慎重且艱難的挑戰。將參與者置身於問題的核心,透過環境整體的觀察,思考「該砍哪一棵樹?」徐銘謙認為,山林資源的智慧取用,在於如何抉擇,「不是不能砍樹,而是為何而砍,如何選擇、如何使用,」透過不斷的反思,以及和夥伴的交流,無形中拉近了參與者與大自然之間的關係,也讓不同價值觀的人,有對話與思辨的機會。
步道第3 站:把最好的留給下一代
悠悠山林,幾千年來承受了許多無情的破壞與掠奪,而山林的決定與承擔是代代相傳的,我們會留下什麼樣的山林給下一代?
拋出了這個問題,徐銘謙靜默了許久。面對不斷增加的水泥鋪面步道、硬體欄杆、平台,她的心裡十分焦慮。台灣的人均水泥消耗量居全球第2 位,為世界平均值的5.2 倍。除了自然景致的消失,水泥步道留下的還包含了嚴重的環境問題。
她不敢想像未來的山林畫面,但她相信,唯有徒步走過、甚或徒手做過,才能真正領略山林之美。
徐銘謙的步道沒有終點,因為每一雙手刻在土地上的記憶將會不斷延續。我們會留下什麼樣的山林給下一代?「我不知道,但我想把最好的都留下來,」她最後這麼回應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