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經常誤以為人皆相同:勞動力市場是同質的;人們有類似的價值觀;理性的人類,嗯,是理性的。基於這種想法便能輕鬆假設經濟模型可運作良好。然而,這種簡化思維偶爾會礙事。若談到移民,「人人相同」的想法會模糊某些關鍵議題。無論我們是否同意,經濟「俱樂部」並非總是民族國家:我們亦可透過文化、種族或宗教差異定義他們。大熔爐並非總能奏效。倘若融合不成,經濟成果便會令人失望。
民族融合起初集中於非洲。非洲民族國家包含太多種族,因此國民教育程度低落、金融體系原始落後、獨裁者貪瀆腐敗,以及基礎設施付之闕如:太多利益團體(interest group)相互競爭,人人各自盤算,不願或無法相互認同,大家無不想方設法擴大自己的經濟租(economic rent,譯注:原本指從土地獲得的收益,後來泛指透過獨佔權力而獲取的收入),眾人甚至會破壞公共貨物的供應;各方鉤心鬥角,經濟便會發展遲滯。(註一)而,並非只有非洲才會出現這種問題。英國的宗教學校林立(包括基督教、回教或猶太教),很可能讓年輕人形成利益團體(學校與董事偶爾會對抗教育當局)。類似的問題也出現於法國:法國政府在二○一○年禁止女性於公共場合穿戴全罩面紗(niqab)與全身式罩袍(burqa),結果引發國家和宗教相對權力的爭論,而這種論戰在二十世紀初期曾讓天主教(Catholic Church)與法蘭西第三共和(Third Republic)分裂。
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倘若缺乏共同的文化規範(cultural norm),便會立即動搖根基。如果某個俱樂部的成員對俱樂部的規則抱持不同的概念(而且比較不願意遵守規則),其他人為何會想入會呢?(註二)根據定義,社會保護(social protection,又譯社會保障)就是地方政府或國家提供的保護:界定誰可受到保護,其實就是界定誰不受到保護。
這反過來又引發了另一個根本的問題。福利國家通常是閉門造車的。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各國加強了邊境管制(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在一九二○年代末期發表了一連串聲明,從旁推波助瀾。國聯是一戰後組成的跨政府組織,乃是全球第一個旨在維護世界和平的國際組織,他們會推行這類舉措,令人感到古怪不解),因此更容易隨意實施稅制、提供各類福利與國家服務。疆域界定之後,各國便擁有極大的財政自主權:如此一來,他們更容易成為經濟俱樂部(economic club)。
在歐盟境內,前述的「四大自由」以及《申根公約》締造的共同邊界暗示著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適切融合:勞動力和資本可以更順暢流動,讓資源分配更有效率;歐盟各國鼎力支持社會市場模式(的共同規範),包括編列福利金幫助窮人。
敘利亞顛覆了這一切。
二○一○年,敘利亞內戰爆發前夕,該國人口為二千二百萬。五年之後,其中一千二百萬人流離失所:有人在敘利亞境內四處遷移(八百萬人),也有愈來愈多人跨越敘利亞邊境前往他國避難。多數難民起初待在土耳其(超過二百萬人)、
黎巴嫩(超過一百萬人)或約旦(超過五十萬人)。土耳其已經要處理諸多經濟問題,而且國內政治暴力日益升高,安置難民得耗費大量金錢,金額估計為八十億美元,或是二○一五年國民所得的百分之一左右。
然而,土耳其和黎巴嫩並非許多敘利亞難民的逃亡終點:這兩國只是跳板,有些人希望能前往歐盟去過更好的生活。因此,在二○一五年尋求歐盟庇護的人數比前一年增加了一倍以上,大約四分之一是敘利亞人;其餘則包括巴爾幹人(百分之十五)、阿富汗人(百分之十三)、伊拉克人(百分之九)與巴基斯坦人(百分之四)。柏林圍牆倒塌以及一九九○年代南斯拉夫分裂引發各種危機之後,申請庇護的難民人數都沒有這麼多。
其中一個結果是庇護申請案件堆積如山:到了二○一五年年底,約有八十五萬尋求庇護者處於悲慘境地,焦急等待申請結果。許多人待在最靠近敘利亞的歐盟國家:通常是希臘與義大利。(註三)另一個結果是獲得庇護者沒有平分四散到各地:多數人一旦進入歐盟,便會前往德國和瑞典,因為這兩個富裕國家起初至少比其他國家更樂意接納難民。
無論難民有何人道主義需求,抵達歐盟的龐大難民嚴重威脅到《申根公約》,甚至危及歐盟的存續。要解釋這個問題,最好從誘因來切入。包圍《阿姆斯特丹條約》簽署國的申根「邊界」不是由歐盟部隊管制。每個國家都得分頭保護這個共同邊界。
然而,首先接納尋求庇護者的歐盟國家會認為,難民一旦進入歐盟,便會遷移到其他地方。因此,無論尋求庇護者是真是假、他們是來自敘利亞或其他國家、或者他們是政治難民或經濟移民,甚至他們是正直的公民或(在極少數的情況下)是暗中策劃殺人或破壞的恐怖分子,處理庇護案件的國家都會隨意核准難民的申請。如果出了問題,也會成為別國的問題。這樣一來,《申根公約》便不再可行。
最終,德國只能仰賴希臘管制歐洲邊界;若管控不嚴而有疏漏,德國將比希臘承受更大的衝擊。希臘要應付嚴重的經濟問題,因此缺乏管控邊界的必要資源(或許也缺乏意志力)。然而,邊界有了漏洞之後,便會衍生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湯瑪士.霍布斯曾說,民族國家的核心角色是保護公民。如果霍布斯說得沒錯,《申根公約》將逐漸崩解:歐陸的各民族國家不得不重新管制邊界,進而威脅奠基歐盟的四大自由的其中一個自由(人員自由移動)。無論《申根公約》能提供多少經濟利益,但歐洲對難民遷徙已經束手無策,讓這個公約危在旦夕。各國正逐漸恢復昔日的邊境管制措施。
註一:請參閱:W. Easterly and R. Levine, ‘Africa’s growth tragedy: Policies and ethnic divis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2:4, pp.1203-50。
註二:國家貪污指數(country corruption index)根本無法說明從這些國家來的移民會做出何種行為;然而,值得一提的是,非政府組織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依照最清廉到最貪腐的程度列出一百六十七個國家,敘利亞排在第一百五十四名。請參閱:http://www.transparency.org/cpi2015#results-table。
註三:原因之一是難民必須在穿越申根邊界之後抵達的第一個歐盟國家提出庇護申請。尋求庇護者一進入歐盟便會進入希臘和義大利,對這兩國的移民局造成極大的壓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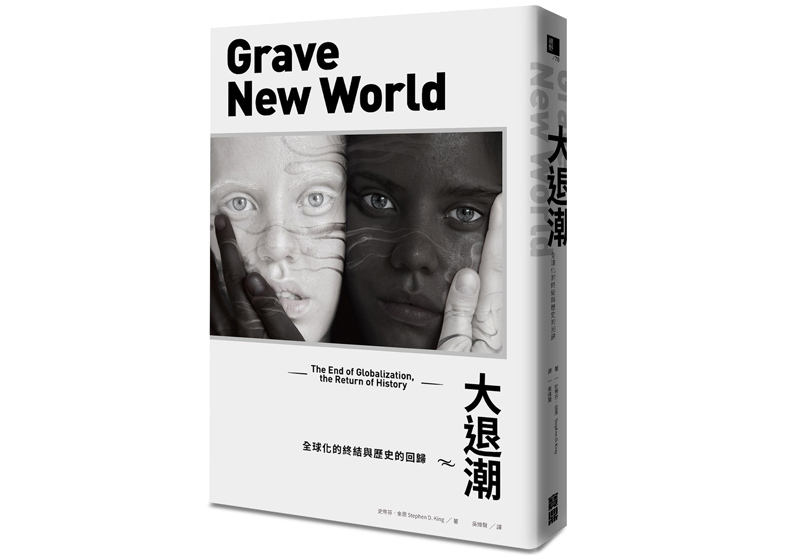
本文節錄自:《大退潮:全球化的終結與歷史的回歸》一書,史帝芬‧金恩(Stephen D. King)著,吳煒聲譯,寶鼎出版。
圖片來源:pixab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