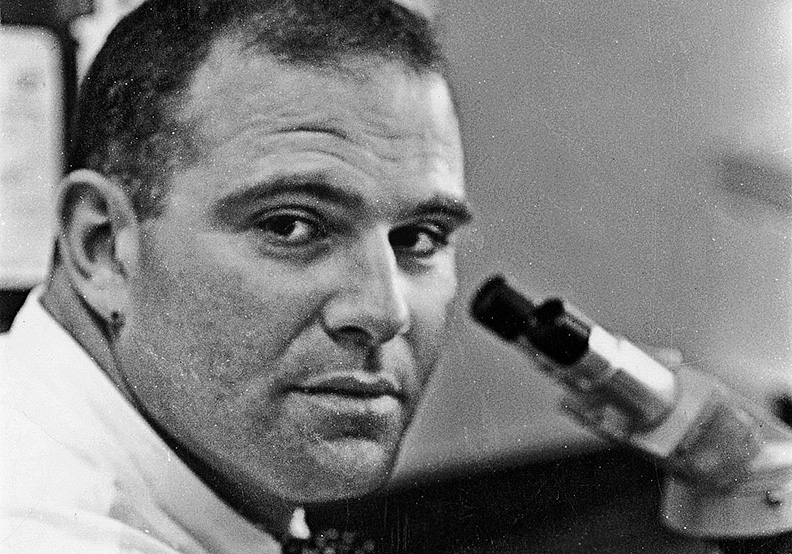一九六六年九月,我暫停實驗室的工作,開始在布朗克斯區的一間頭痛診所幫真正的病人看病,這對我來說是極大的解脫。本以為我是主治頭痛,頂多加點別的問題,但我很快就發現,情況可能複雜得多,至少在所謂的「典型偏頭痛」病人身上,頭痛不僅令他們飽受煎熬,而且引起極為廣泛的症狀—簡直可寫成一部神經學百科全書。
當中很多病人告訴我,他們曾經看過內科或婦科或眼科或某某科醫師,卻不曾從他們那裡獲得應有的重視。這讓我有感而發:美國醫學界的專科醫師愈來愈多,這中間卻似乎出了什麼問題。家庭醫師愈來愈少,而他們是金字塔的基礎。我父親和兩個哥哥都是全科醫師,我發覺自己不像是專治偏頭痛的超專科醫師,而像是這些病人一開始該去看的全科醫師。我覺得詢問他們生活上的方方面面,是我的事情、我的責任。
我看過一名每逢星期天就「頭痛噁心想吐」的年輕人。他描述頭痛之前會看到閃爍的鋸齒狀線條,所以這很容易診斷出是典型偏頭痛。我告訴他,這種情況有藥可醫,只要他一開始看到鋸齒狀線條,趕快把麥角胺(ergotamine)錠含在舌頭底下,這樣偏頭痛應該就不會發作。一星期後他打電話給我,激動得不得了。藥錠真的有效,他果然不頭痛了。他說:「願上帝保佑你,醫師!」我心想:「天哪,這藥也太厲害了吧?」
到了下個週末,我沒聽說他的消息,很好奇他的進展如何,於是打電話給他。他語氣相當平淡,告訴我藥錠再度發揮功效,但奇怪的是,他接著卻抱怨連連,說他很無聊。過去十五年來,每逢星期天伺候偏頭痛早已是慣例,他的家人這天會來探望他,他是大家的焦點人物;而現在,這一切都沒了。
又過了一星期,我接到他姊姊打來的緊急電話,說他哮喘發作很嚴重,正在施以氧氣及腎上腺素治療。她的語氣暗示,這或許是我的錯,怪我無端惹來一場風波。當天稍晚,我打電話問候病人,他告訴我,他小時候曾經哮喘發作,但後來被偏頭痛「取而代之」。我只顧處理他目前的症狀,竟漏掉這部分的重要病史。
「我們可以開治療哮喘的藥給你,」我建議。
「不要,」他回答:「我想要別的……你覺得我星期天有必要生病嗎?」他的話讓我大吃一驚,但我說:「我們討論一下吧。」
於是我們花了兩個月時間探討他「星期天有必要生病」的想當然耳。隨著我們的「探討」,偏頭痛愈來愈少打擾他,最後差不多消失了。對我來說,這個例子說明:有時不自覺的動機可能與生理習性產生關連,也說明:不能將疾病或疾病的治療從「某人的整體生活模式、背景、經濟情況」片面擷取出來。
頭痛診所的另一名病人是個年輕的數學家,他也有星期天偏頭痛的毛病。星期三他開始緊張煩躁,星期四變得更嚴重,星期五無法正常工作,星期六倍感煎熬,到了星期天便產生可怕的偏頭痛。但是之後,偏頭痛一到下午便消失了。隨著偏頭痛消失,有時病人會突然冒汗或排出一些淺色的尿液,這有點像是某種宣洩作用,既是生理層面,也是情緒層面。病人的偏頭痛與神經緊張一掃而空,頓覺神清氣爽、如獲新生,既冷靜又創意十足。星期天晚上及星期一、二,他做出來的數學研究極具獨創性,然後,他又會開始煩躁起來。
當我開藥給這位病人,治療他的偏頭痛,竟然改變了他的數學研究能力,因為藥物打亂了這種奇特的週循環—先是疾病與痛苦,接下來卻是健康無比、創意十足。
沒有兩位偏頭痛病人是相同的,所有的偏頭痛病人都是獨一無二的。和他們一起面對疾病,才是我真正的學醫生涯。
偏頭痛診所的負責人是鼎鼎大名的弗里德曼(Arnold P. Friedman),他寫過很多偏頭痛的文章,經營這間首創先例的診所已經二十多年。我覺得弗里德曼對我很有好感。他認為我很聰明,我感覺他想要收我為徒。他對我很親切,安排給我的門診病人比別人多,而且付給我的薪水也稍微多一些。他把我介紹給他女兒,我甚至懷疑,他會不會是想把我和他女兒送作堆。
後來發生一段奇怪的插曲。星期六早上我都會和他碰面,告訴他這星期看了哪些有意思的病人。一九六七年初的某個星期六,我告訴他,有一位病人在看到閃爍的鋸齒狀曲線(許多偏頭痛都有這樣的先兆)之後,並沒有演變成頭痛,反而出現嚴重的腹痛、嘔吐。我說我曾見過其他好幾位病人也像這樣,他們顯然是從頭痛轉變為腹痛,我不知道是否該挖出維多利亞時代的古老名詞:腹型偏頭痛。(這就是為什麼後來在我寫的書《偏頭痛》上,開宗明義第一句話便強調:頭痛絕對不是偏頭痛的唯一症狀,這也是為什麼《偏頭痛》整個第二章專門在講各式各樣不頭痛的偏頭痛。)
說著說著,弗里德曼突然變了個人。他滿臉通紅大喊:「你什麼意思,說什麼腹型偏頭痛?這裡是頭痛診所!偏頭痛migraine的原意就是半個頭骨!它指的就是頭痛!我不許你說什麼不頭痛的偏頭痛!」
我嚇得閉嘴,簡直難以置信。這還算是小衝突而已,更火爆的場面發生在一九六七年夏天。
我在《幻覺》書中曾描述,一九六七年二月,在安非他命誘發的頓悟之下,我把李文(Edward Liveing)一八七三年出版的《論偏頭痛》從頭到尾拜讀完,下定決心自己也要寫一本《偏頭痛》來相媲美:一本屬於一九六○年代、結合我自己眾多病人實例的《偏頭痛》。
一九六七年夏天,在偏頭痛診所工作一年之後,我回英國度假。令我自己大感驚訝的是,我竟然在幾星期之內寫出一本關於偏頭痛的書。我並沒有刻意計劃,突然就這麼洋洋灑灑寫出一本書來。
我從倫敦發電報給弗里德曼,說我莫名其妙文思泉湧、冒出一本書,已經拿去給費伯(Faber & Faber)出版社(註一),這家英國出版社曾出版我母親寫的書,他們有興趣幫我出版。我希望弗里德曼會喜歡這本書,並且請他幫我寫序。他發回來的電報說:「住手!什麼事也別做。」
等我回到紐約,弗里德曼看起來一點也不親切了,反而看起來很精神失常。他差點把我手上的書稿搶去撕掉。他質問我:「你以為你是誰?竟敢寫什麼偏頭痛的書?簡直是膽大妄為!」我說:「很抱歉,事情就這麼發生了。」他說他要請德高望重的偏頭痛界權威人士來審查書稿。
此等反應令我大吃一驚。幾天後,我看見弗里德曼的助手在抄寫我的書稿。我並不太理會這件事,但我注意到了。大約過了三星期,弗里德曼給我一封審閱者寄來的信,寄信人的識別特徵都已經拿掉。這封信缺乏任何真正具有建設性的批評內容,反而充滿對於書的風格及作者的人身惡意攻擊。當我向弗里德曼提到這點,他回答說:「恰恰相反,他說的完全正確。你的著作本來就廢話連篇,基本上全是垃圾。」他又接著說,我看過的那些病例(我自己寫的筆記)會統統鎖起來,以後我碰也別想碰。他警告我千萬別想再寫什麼書,如果硬要寫,他不僅會炒我魷魚,而且以後我在美國絕對找不到另一份神經學的相關工作。當時他是美國神經學學會(ANA)頭痛領域的主席,若沒有他的推薦,我真的很有可能再也找不到工作。
我把弗里德曼的威脅跟父母說,希望能得到他們的支持,但我父親卻說(以我來看實在太窩囊了):「你最好不要激怒這個人,他會毀掉你的一生。」所以,我壓抑自己的感受,過了好幾個月。這幾個月算是我這輩子最慘的其中幾個月。我在偏頭痛診所繼續看診,最後,到了一九六八年六月,我決定再也不忍氣吞聲了。我拜託診所工友幫忙,讓我晚上進入診所。在午夜與凌晨三點之間,我抽出自己的筆記,辛辛苦苦拚命用手抄寫。後來我告訴弗里德曼,我想休長假回倫敦,他立刻問道:「你還想回去寫你那本書嗎?」
我說:「我非寫不可。」
「等你寫完,你也完了,」他說。
我憂心忡忡回到英國,真的是氣到全身顫抖。一星期後,我接到他的電報,我被解雇了。這讓我顫抖得更厲害,但我頓時有了全然不同的感受。我心想:「這隻潑猴再也不能在我肩上撒野。我可以任意做自己想做的事,誰也管不著。」
現在我可以愛寫什麼就寫什麼,但同時我也給自己下了極為嚴苛、幾近瘋狂、迫在眉睫的最後通牒。我對一九六七年的手稿不太滿意,決定整本重寫。九月一日那天,我對自己說:「九月十日之前,如果你還沒有把完成的書稿交到費伯出版社,你就死定了。」在這樣的自我威脅下,我開始奮筆疾書。不到一、兩天,威脅感不翼而飛,寫作的樂趣隨之而來。我不再嗑藥,但這段日子卻精力充沛、興奮得不得了。對我來說,這本書簡直就像是「自己在寫自己」,一字一句自動自發迅速各就各位。每天晚上我只睡幾個小時。九月九日那天,比預定的期限還提早一天,我把完成的書稿拿去費伯出版社。他們的辦公室位於大羅素街,離大英博物館很近,我交完書稿便走去博物館。看著那裡的手工藝品—陶器、雕塑、工具,特別是書籍和手稿,這些東西都活得比它們的創作者還久。我有感而發:我竟然也做出了一點東西。這東西也許不太重要,但它本身是真實的,是存在的,在我離開人世之後,這東西還會繼續活下去。
如此強烈的感受前所未有,這種感受是:創造出真實且具有某種價值的東西,正如我寫作的第一本書—面臨弗里德曼那樣的威脅、面臨自我威脅而寫出來的書。回到紐約,我有一種喜樂感,簡直是幸福滿溢。我好想大喊「哈利路亞!」但是我太害羞了,喊不出來。於是我每晚都去聽音樂會,聽莫札特歌劇、聽德國聲樂家費雪迪斯考演唱舒伯特的作品,感覺生氣蓬勃、活力充沛。
在一九六八年秋季那段既興奮又激動的日子裡(六個星期左右),我還不停的寫,希望為那本偏頭痛的書增添更詳細的描述,例如先兆期可能會看到的幾何圖案,以及大腦可能發生什麼情況的一些推論。我把這些拉拉雜雜的附錄,寄給英國神經學家古蒂(William Gooddy),他已經為我那本書寫好精采的序文。古蒂說:「不—算了啦,原來的書稿已經夠好了。這些想法,你未來幾年還會一次又一次回過頭來檢視。」(註二) 我很慶幸,他讓書逃過了我的蠻橫及滔滔不絕,那時的我簡直是興奮過度,變得有點狂躁。
我和我的編輯辛辛苦苦整理插圖及參考文獻,到了一九六九年春天,一切準備就緒。但是一九六九年過了,接著一九七○年也過了,書卻遲遲沒有出版,我愈來愈感到沮喪及憤怒。到最後,我找來一位著作經紀人,名叫羅斯(Innes Rose),他對出版社施加了一點壓力,出版社終於在一九七一年一月推出那本書(不過書名頁上卻印成一九七○年)。
為了書的出版,我專程去了趟倫敦。一如既往,我待在我們馬普斯伯里路的老家。出版那天,我父親走進我的臥室,臉色蒼白且抖個不停,手裡拿著《泰唔士報》。他一副很恐懼的樣子,說:「你上報了。」報紙上有一篇很不錯的書評,說《偏頭痛》是「不偏不倚、權威可信、才華洋溢」之類的。但就我父親而言,這沒什麼差別,我已經犯下滔天大罪(雖然不是什麼違法的蠢事),只因為我上了報。
在那個年代,只要犯了四大罪狀的任何一項:酗酒、成癮、通姦、廣告,就會被英國「執業醫師登記名冊」除名。我父親認為,《偏頭痛》的書評出現在一般媒體,可能會被看成是廣告。我竟然讓自己曝了光!他本人向來(或自認為)很低調。他廣受病人、家人及朋友的愛戴,但出了這個小圈子,外界對他並不熟悉。我已經逾越分際、違反規範,他很替我擔心。這正好跟我既有的感覺一致,在那個年代,我常常把「發表」(publish)錯看成「懲罰」(punish)。我覺得如果發表任何東西就會受到懲罰,但我卻不得不發表—這樣的矛盾幾乎快把我撕成兩半。
對我父親來說,「擁有好名聲、受別人尊重」是非常重要的,比任何世俗的具體成就或權力還要重要。他很謙虛,簡直到了自我貶抑的地步。別的不說,他輕忽了一件事:他其實是很了不起的診斷醫師,專科醫師常常把搞不定的病例送來給他,因為大家都知道他具有不可思議的能力,可以做出令人意想不到的診斷。(註三)但他很安於他的本分、安於他在社會上的地位、他所擁有的好口碑,默默自得其樂。他希望他所有的兒子不管做什麼事,也都能為自己贏得好名聲,不致使「薩克斯」這姓氏蒙羞。
漸漸的,看過《泰唔士報》書評後一直擔心受怕的父親,在看到醫療媒體也多有好評時,總算可以安心了,畢竟《英國醫學期刊》和《刺絡針》(Lancet )期刊本來就是十九世紀的醫師為了醫師而創立的。我想此時此刻,他應該開始感覺到,我寫的書肯定還不錯,當初堅持寫那本書是對的,即使那本書害我賠上我的工作。(而且,假如弗里德曼的權勢真的像他恐嚇的那樣,說不定還賠上我在美國的任何神經學相關工作。)
我母親從一開始就很喜歡那本書,這麼多年來,我第一次感覺到父母和我站在同一陣線,承認他們那瘋狂、叛逆的兒子,終究還是有那麼一點好處—這幾年來不曉得幹了多少行為不檢的蠢事,如今總算踏上臨床工作的正途。
註一:不過,費伯出版社裡有人看完後,給了很特別的評語。他說:「這本書讀起來太容易了,這樣會讓人對內容起疑心。麻煩寫得更專業一點。」
註二:事實上,在一九九二年,我真的為《偏頭痛》這本書添加了附錄,部分是由於看了偏頭痛藝術展而受到鼓舞,部分則是由於跟好友西格爾(Ralph Siegel)討論,他是很棒的數學家兼神經科學家。二十年後,也就是二○一二年,我在寫《幻覺》的時候,又以另一種觀點重新審視「偏頭痛先兆」這個題材。
註三:一九七二年,我表親阿爾.卡普(Al Capp,美國著名漫畫家)來諮詢我爸,他的一系列離奇症狀,把他自己的醫師給考倒了。
我爸在兩人握手時看了他一眼,說道:「你是不是在服用阿普利素寧(Apresoline)?」
這是當時用來控制高血壓的一種藥。
「是啊,」阿爾說,十分驚訝。
「你得了全身性紅斑狼瘡,是阿普利素寧引起的,」我爸解釋:「幸運的是,這種由藥物引起的症狀完全是可逆的,但假如你不把阿普利素寧停掉,很可能會沒命。」阿爾覺得,我爸憑著「閃電般的直覺」,救了他一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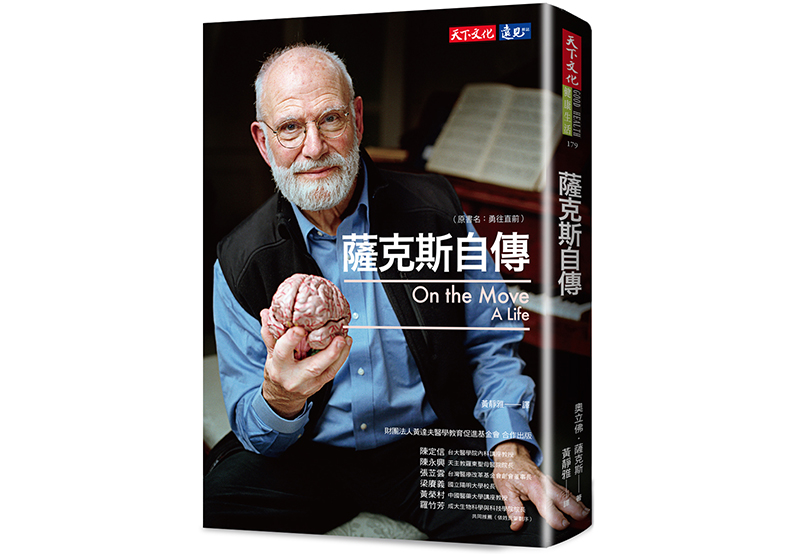
本文節錄自:《薩克斯自傳(原書名:勇往直前)》一書,奧立佛‧薩克斯(Oliver Sacks)著,黃靜雅譯,天下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