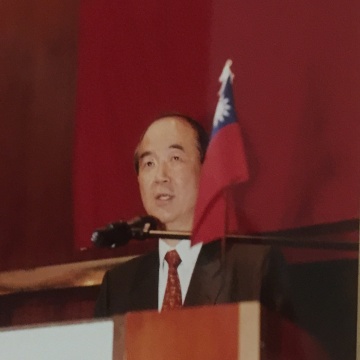將近半個世紀前的抗戰期間,先父宗南將軍以戰區司令長官之身分坐鎮西安。政府給他的任務是東抗日本,西防蘇俄,北拒中共,內安甘、寧、新疆;招收人才,教育幹部,再將整編好的部隊,支援全國各戰場。那時,陝西一位大儒特以對聯一幅相贈,曰:「大將威如山鎮重,先生道與日光明。」父親看後說:「大將何足道哉!道與日光明才是重要的。」
我自幼見到父親的機會並不多。我出生較晚,在台灣成長;印象最深的,總是他回到家中時所自然流露的威嚴。
有一晚,父親把我叫住,問我將來要做什麼?十歲的我,不假思索,說道:「我要像您一樣,做個軍人。」沒想到父親並沒有顯出同意的表情,卻以和藹而堅定的口吻說:「你要做大丈夫。」「什麼是大丈夫?」我問。父親說:「真正對人們有貢獻的人就是大丈夫,譬如大科學家、大工程師、大醫生。」原來父親的期望已超過軍事的層面」他自己戎馬倥傯,勞瘁一生,念茲在茲的,都是整個國家的建設。
與士兵同甘苦
父親生活上的簡樸廉潔是出名的。數十年軍旅生活,住宿常在寺廟祠堂裡,不勞民力,不借民房,即使任司令長官時也是如此。連總統蔣公的侍衛人員赴西安,看到他的生活行止都深表詫異。
我幼年時家中沒有冰箱,而台灣暑間酷熱,年年也就這樣過了。後來羅列將軍送來一台舊冰箱,父親頗不以為然,迭經部屬苦勸,才沒有退回。
他的想法是生活與士兵同甘苦,官兵過什麼日子,他的家也該如此。他一向為部屬,為傷患殘疾者爭取福利,購置產業,卻從未想到自己,因此母親自然較操勞辛苦。
記得我十三歲時,有一天汗衫破了被他看到,不但未責備,反而哈哈大笑,作一首打油詩給我:「行年一十三,常穿破布衫;縫補又縫補,難看真難看!」回想起來,他對這事的反應就是對我價值觀的教育。
父母在民國二十六年即已訂婚,只因抗戰爆發,父親以匈奴未滅,何以家為,請求母親將婚事延後;母親亦深明大義,乃先赴美留學,直到取得博士學位返國任教數年後,方始成婚。
這期間經過十年漫長的等待和考驗,在他們終於再相見時,父親曾作詩送給母親,其中有幾句是「……猶見天涯奇女子,相逢依舊未婚時……我亦思君情不勝,為君居處尚無家。」
父母婚後因戰亂不停,仍是聚少離多,直到民國四十年代末,父親自澎湖防衛司令任滿返台北,才得以有較多時間與母親及四個子女相聚。那幾年母親鼓勵他研習英文以及覽讀聖經;我記得每當台灣神學院的陳教授來查經時,父親一定認真發問,並且擇節背誦。
這時我們父子倆相聚時間較多,我對他的畏懼也逐漸變成孺慕之情。父親曾鼓勵我讀東周列國志、三國演義等,而且不時問我的讀後心得,以及學校各種課業的進展。但正當我感到與父親問心靈逐漸緊密契合時,民國五十一年二月十四日,十四歲的我都驟然失去了這位生命的榜樣,精神上的支柱與朋友般的摯誼。
在其後的年歲裡,我飽嘗喪父之痛。我曾多次默默地肅立在父親遺像前深思,向他立志、向他保證……,而我也似乎常看到他眼中露出肯定的微笑。
令人常懷念
三十年來,我在國內外讀到有關父親的文章甚多,也從各方人士口中聽到許多關於他的事蹟。父親的功業自有史筆的評論,而最令我驚訝與感動的,是凡與父親接觸較久、認識較深的人,不論是師長、同學、朋友、部屬,都是那樣地尊敬他、推崇他、愛護他。
經國先生當年與父親交往甚多也甚深,後來在我出國留學前向他辭行,敬請訓誨時,他曾感慨的說:你父親是我最好的朋友!」
何應欽上將在九十多歲訪問南非時,一再向當時正在南非服務的我認真地強調:「你父親是我最喜歡的學生。」黃埔一期的幾位老伯,最近還對我吐露,父親是他們心目中最尊敬的同學。
另外一位曾任父親長官的蔣鼎文伯父,在二十多年前某個春節來家裡向先母賀節時,巧遇我帶了當時還是女朋友的內子第一次回家介紹給先母。蔣老先生看到我的女友,深深注目,連連點頭,然後直趨客廳父親遺像前,幾乎聲淚俱下的大聲說道:「宗南!宗南!你可以放心了,胡家有後了!」害得女友滿臉通紅。
警界一位首長說,當年他在派出所任警員時檢查戶口,有一次到曾任父親參謀長的盛文將軍府中;一提到父親,盛將軍百感交集,竟然一面哭,一面喊著:「胡先生!胡先生!」這位首長說,從來沒有看到長官對部屬感召有如此強烈者。
不但如此,父親的故舊學生,每年到了父親忌日必定聚會,風雨無阻的登陽明山竹子湖墓園行禮紀念。一個人去世了三、五年,他的故舊去紀念固屬常情;但到了去世已三十個年頭,每年還能有數百人聚集致意,實在是稀少而可感的事。
皇軍最難纏的敵人
我常常想,雖然父親愛護朋友,獎掖人才,尤其喜歡培植青年,且在日記中也立志「要盡一切力量,為部屬、同學、朋友、學生謀出路」,然而並不是人人都能獲得升遷,都可如願以償,也並非人人都能發達,能遂其心意。但為什麼有這麼多人,經歷了這麼長久的時間之後,遼這樣深切感念著他?又是什麼因素,什麼力量促使他們這樣長久的維繫在一起?
這可能不是一兩句話說得完的。但起碼我因為看到及聽到許多有關父親的感人事蹟,所以相信父親所部必是上下一心的優秀部隊。
他們能夠在中共「長征」期間,翻山越嶺,窮追苦戰,度越松藩,深入甘肅,屢敗共軍。且能在抗戰期間以血肉之軀,抵抗日軍的戰機大炮,死守淞滬長達六週之久。當時排、連、團長大多壯烈犧牲,存者誓死不退,令國際間對我國刮目相看。其後部隊北調陝西,日軍進犯河洛多次均不得逞,當時日本評論家稱父親的部隊「是皇軍最難纏用的敵人」。
民國三十六年,父親所部在短短的五日之內,迅速進擊,攻克共軍盤據了十餘年、工事最為堅固的首府延安,使得中共因喪失首都,雖在大陸上逐漸擴大占領區,其政權卻不為國際所承認。唯中央受共諜謀略影響,總在軍隊調動上不予父親有集中兵力、圍殲共軍的機會。
其後全國局勢逆轉,父親直屬部隊多被分散調往東北、華北、新疆各路支援。剩餘的幾個軍又犯戰略之大忌,於三十八年底奉命自漢中跋涉千餘里外的重慶與成都,支援友軍;都因友軍或棄守或降敵,主力未開到,就被迫逐次投入戰場。
結果雖因奮戰而爭取到時間,使中央政府得以順利轉進來台,所部精銳都在大量共軍與叛軍圍擊中,遭父親續飛西昌重整旗鼓,召訓散兵新兵,迅速擴充至數萬人。中共以芒刺在背,乃於準備數月後,調集十數倍以上的兵力,圍攻擊破了此一國軍在大陸最後據點。父親則在蔣公的命令與部屬的苦勸下,為爾後號召流散之幹部、學生而赴台。
四川及西康之役,實為掩護政府在台灣站穩腳步之重要戰略作為,然將士犧牲之慘烈,每當我讀到此段悲壯的戰史,莫不為之掩卷長歎。父親自己則是把他椎心的苦痛深埋心底,從頭幹起,致力明恥教戰;日記中充滿著絕不灰心氣餒的積極精神,對於外界不明真相的謗語,更是從無一語自解。
先生道與日光明
我任職於駐芝加哥辦事處時,常有機會遇見大陸學人;當他們由別人那裡知曉父親的名字時,對我都非常感到興趣。由於他們大多對中共的教條產生質疑,所以常常問及我過去所知悉的歷史真相。一日,我反問一位年輕的大陸學生,「你何以這麼年輕還知道胡某某?」他答道:「我們每一個人都知道。因為從小看的小人書,都說是打胡宗南。」啊!父親!如此,我更明瞭您當年為了多難的國家,付出了您的一切。
父親在台灣始終不願出任重職,反而請纓到大陳去,將那至苦的不毛之地,建成反共堡壘。後來在澎湖,除了著重軍事建設之外,還大規模的協助地方建設,增進居民福利(包括籌建跨海大橋)。他愛才、愛民的天性,贏得了當地父老的尊敬和讚賞。前年澎湖縣縣長王乾同訪問芝加哥時,我自我介紹,他大表高興;返國後立即寄來林投公園中父親銅像的照片,代表當地同胞的深切懷念。
近年來,國際局勢丕變於瞬息之間;今天,中共的許多變化也不可避免的在進行,「亡共在共」已是昭然若揭的事實。在父親逝世三十年後的今日,國際上既有如此有利於我的發展,而父親奉獻一生心血的中華民國,又在寶島成長茁壯。父親的千萬朋友、學生正繼續著他的精神,為熱愛的國族獻身,正是「先生道與日光明」。
我相信,父親在天之靈一定可以含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