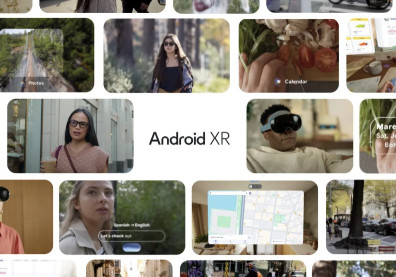凌晨兩點半。林口工業區絕大多數的工廠,都已沈睡在漆黑而靜論的夜空裡;兩盞值勤的路燈打亮「聯合報天天向您問好」的標示,入口處,印報機轟隆轉動傳來的巨響,引領來客進入一個分秒必爭的報業世界。
停靠發報台的送報車正張開大口,吞裝一捆捆剛剛出爐的新報。樓梯間裡,穿著深藍制服的印報工急促奔竄而上,擦肩走過的廠長賀克明心底有數:今天的印刷可能有點問題。
「我們的印刷工一向都是「跑著」解決問題,」三十歲出頭的賀克明揚著眉說:「七年前我剛進聯合報,看到開印前大家都用跑的送印版,就知道這個公司非成功不可!」
在中國人的報業市場裡,聯合報已經這樣跑過四十個年頭。四十年間,它由一張發行一萬兩千份的「聯合版」,擴展為總發行量超過兩百五十萬份,據點遍及亞、美、歐三洲,發行廣被全球的七份報紙,締造出國際間規模最大的民營中文報團。聯合報系旗下的員工和資產,也同步躍升。
從調頭寸到紅白眼
四十年前,「聯合報」只有一百五十個人手,月月得靠調頭寸來發薪水。四十年後,聯合報系的五千五百名員工不但擁有傲視同行的待遇,還可享用休閒中心、醫療診所、優惠貸款等福利。而四幢位於台北東區的辦公大樓,和九座分布海內外、備有高速輪轉彩色印報機的印刷廠,使這個報團的根基愈扎愈深。
有人用紅、白眼相看,視它為「報閥」、「財閥」,但有更多追求經營之道的人想要追根究底:聯合報為什麼能有今天?
頭頂銀絲,自認在聯合報四十年「打過人生最美好戰役」的專業報人劉昌平,用簡單的八字訣,理出聯合報成功路的線索:決策者「領導有方」、同仁間「敬業樂群」。
這八個字人人耳熟能詳,但要劍及履及,並在組織中蔚為風氣,形成文化,卻是極大的挑戰。
民國四十年,中央軍校出身、做過總統警衛團團長的王惕吾,振臂迎向領導報業的挑戰。他與已故的范鶴言、林頂立聯手,把三份風雨飄搖瀕臨關閉的民營報紙--民族報、經濟時報和全民日報,改組成一份「聯合版」,是為聯合報前身。
而今,七十九歲的王惕吾早已成為領導七報及十餘家相關事業的董事長。在員工眼裡,他是一位看得遠、看得準的總司令,也是一位寬厚、親切的大家長;他充滿精神感召的力量,具有相當的領袖魅力。
親近他的人觀察,王惕吾的領導風格深受軍旅背景影響。他把軍中的倫理管理用在經營企業上,以袍襗精神對待下屬,恩威並重、甘苦共嘗;他講求戰略、戰術,凡事慎思、明辨後必然篤行,重大決策鮮少失誤。
不服輸的氣概
回顧民生凋蔽的四十年代,公營的中央日報、新生報在人力、財力、設備上優越同行,民營報紙的市場占有率僅為一三.三%,根本缺乏競爭條件。但剛踏入報業世界的王惕吾,滿懷不服輸的氣概,全力投入、虛心向學。
他一天工作十八個小時,白天管業務、財務,晚上看編務、印務。他對家人講:「我的書沒有其他報人讀得多,也沒有留過學,不通洋文,唯一能比的,就是比他們更投入。他們一個禮拜上六天班,我上七天,一年下來,我就比他們多五十二天;他們一天上兩班,我上四班……。」
資深同仁對他學習的態度印象深刻。進入聯合報近四十年的總管理處顧問劉潔記得,王惕吾一開始到編輯部時,總是不發一語地坐到深夜,過了一段時間他開口了,所說的話讓人覺得,他已相當在行。
那時聯合報經濟拮据,在西寧南路租的辦公室光線幽暗,走廊黑漆漆,總編輯的辦公桌白天要挪用來出報,員工薪水月月難發。然而,在這個草創階段,大家都有背水一戰的心情,士氣高昂。為了努力讓社會認同「聯合報」,許多人和王惕吾一樣,以社為家。
王惕吾給屬下的「精神報酬」勝過其他。他有一本記事簿和人事卡片,詳載每個同仁的背景與家庭狀況,沒事就拿出來翻。因此,從總編輯到印刷工、送報童……他不僅叫得出每一個人的名字,也瞭解每一個人的特長。
曾經有人向他報告,某位負責出納的同事嗜酒,中午喝高梁,可以喝到兩眼通紅。他反問:「他有沒有因此數錯鈔票?如果沒有,我可以告訴你,他不但中午喝,晚上回家、睡覺之前也還要喝。他就是有這個本事呀!」
肉肥湯才肥
有時,他會像個部隊的指揮官那樣,到第一線巡視,給同仁立即的鼓勵。例如,他常站在編輯的身後看他們下標題,並動手把下好的標題拿過來欣賞,使編輯精神大振。
王惕吾的某些作風,或許更像「父兄」。一個每天跟早班火車出勤的送報工得了肺病,按照報社規定,病假超過一定時間就止付薪水,王惕吾自己掏腰包,要他安心休養兩年把病養好。
他在生活中平易近人,但當屬下工作不力,卻是暴跳如雷,不假辭色的。有時事情處理得離譜,像送報時間無故延誤了,他會激動得拍桌子,用浙江東陽國語直著嗓子罵人。
除施威外,他也有論功行賞的作法。例如,發給同仁酬勞股的股面一不;按照發行和廣告業績的收入,發給員工業績獎金……。王惕吾十分相信,「一鍋湯中煮肉,肉肥湯才能肥」。 這樣甘苦共嘗的結果,聯合報創刊第八年,終於以八萬份的發行量,超越當時的第一大報中央日報,得到第一顆勝利的果實;這時聯合報也第一次置產,把社址搬到康定路,一幢屬於自己的五層辦公樓。
聯合報擺脫了朝不保夕的生存威脅,立刻著手建立制度規章,王惕吾也逐漸表現出「辦報企業家」的胸襟與魄力。
六0年代初,和他合夥的范鶴言、林頂立因財務問題相繼賣出股權,接手的台塑企業董事長王永慶又以優惠方式把股權轉讓給他後,聯合報由三分天下定一尊。王惕吾的思想、精神和理念,便更加充分地反映到經營決策與企業文化上。
無私無他辦大報
他常告訴同仁,自己是為「福國利民、興利除弊」而辦報,辦報的人一定要先做到「無私」,才能「無他」。三十多年前,民營報的力量仍十分薄弱,他期許同業團結起來,一同為國家服務。因此,當有人向他要聯合報所訂的制度規章時,他「一點點沒有自私」,把整份都交了出來。
五0年代經濟顯著成長後,報紙銷售激增,引發了報業的大會戰。王惕吾開始用大手筆的投資,強化新聞的競爭力。
資深同仁都知道,如果聯合報上有一條精采的獨家新聞,王惕吾會開心一整天,甚至還會打電話向那位記者致意;如果遠遠聽到他高嗓門的吼聲,一定是當天的新聞有不如別家之處。
曾經做過聯合報採訪主任的師大教授于衡仍然記得,民國五十二年,副總統陳誠訪問越南,他和十八名記者隨行採訪。為了取得競爭優勢,陳誠與吳廷談巡視戰略村的那一天,他以「加急電報」發回一千四百二十五個字的特稿,約花費台幣三萬八千七百元。當時用這筆錢足可買一幢小洋房,他對報社有些歉然,王惕吾非但沒有吝惜,還直說很好。
「他這種只要別的報紙沒有、聯合報有,代價在所不惜的性格,別人比不上!」兩年多前退休的于衡,對近期王惕吾仍屢賞重金給搶得獨家新聞的記者,表示「其來有自」。
雖然聯合報獎勵「獨家新聞」,這位精於「整軍、練兵、用兵」之道的總司令,都更講求以團隊力量來打組織戰。他經常說,報社沒有個人英雄,成功歸於團體。從早年紅葉棒球隊風靡台灣時,跑社會、體育新聞的記者聯袂採訪,到近年六四天安門事件、東歐民主風潮,凡有重大新聞發生,聯合報總會派遣一支採訪部隊,同心協力的完成任務。
發行領域全島一體
聯合報組織戰的火力,在行銷網路上尤見鋒銳。在發行領域全島一體的策略下,目前全省共有一千三百多個分銷聯合報的單位,十九個只銷聯合報系報紙的大型分社,六個發行中心服務組,和四個分布在不同地區的廣告公司。這張綿密的組織網,使絕大多數的同業相形之下,僅能以游擊隊回應。
王惕吾深諳「提綱挈領,由各小部隊執行命令、貫徹政策」的組織戰訣竅。一位由他報轉進聯合報的高階主管發現,這個機構層級分明,講究分層負責,老闆對主管相當信任,只不斷地談「大導向」,自己獲得授權的程度,相對高於從前。
一次,曾經做過國防部長的總統府資政俞大維到聯合報參觀,最後下了這樣的結論:「我一生用人、帶兵只用八個字:知他、用他、信他、諒他,沒想到王惕吾把它做得最徹底!」
在組織戰和團隊精神的前導下,聯合報的人事升遷循序漸進,重要位置很少輕易變動,管道日久雖嫌擁塞,但人事呈現相當程度的穩定。一位加入聯合報二十多年的記者說:「在這裡工作不需要拉關係、走後門,上下之間,也沒有人擺官架子,唯一的挑戰就是把事情做好。」
企業文化薰陶的結果,聯合報記者給外界的印象是:他們比較文氣,少有人張牙舞爪,自以為是無冕王;他們講求團隊合作,大家像是穿了制服,不太表現個人色彩。
國家、報紙、我
由於價值觀鮮明具體,長久以來,離開聯合報的人大多是因為氣息不投合,或者是,不能接受王惕吾的意識型態。
王惕吾走過一段兵亂頻仍的中國近代史,軍人出身的他,深奉愛國、忠黨為絕對真理。他相信,國家利益高於新聞專業利益;社會利益高於報社職業利益。
他的子女透露,父親的優先順序是這樣排的:國家、黨、社會、報紙、私人。因此,他雖極力爭取新聞自由,又要求旗下的新聞記者自我約束,「我認為有許多事情就是不能講,」他嚴正地堅持。
這種態度直接影響聯合報的言論尺度。近年來台灣的變化驚天動地,外界批評聯合報過於保守,甚至連業務部門的客戶都已強烈反應。王惕吾絲毫不為所動。「聯合報保守的是整個國家、社會的利益,不是報社的利益,」他對屬下說:「何況什麼叫做保守?難道迎合時麾、趨炎附勢、譁眾取寵就是開放?」
他標榜正派辦報的理念:正派的報紙要避免「前進」的偏激與「保守」的偏失,而能去私存公,堅守報紙為「社會公器」的立場。
親近他的人指出,王惕吾可以接受批評,但絕對無法忍受任何一方面的落伍。他有強烈的企圖心,是一個絕對的第一主義者,不斷要求自我超越。聯合報業務部總經理楊仁烽引述他的召示說:「勝利是無可取代的。第一就是第一,第二跟第一百一樣。」
他的眼睛永遠往前看,追隨他的人發覺,他對未來情勢的判斷「有很特殊的靈感,和很優異的天賦」。八年前,他建議高級主管把聯合報第三版,由社會新聞改成報導科技、環保、消費趨勢的現代生活,大家猶疑難決。他一肩挑起,「改!錯了我負責。」結果是,聯合報改版後,其他報紙紛紛跟進。
也就是用這樣的眼光,二十五年內,聯合報以母報之軀,生出了經濟日報,民生報,紐約、泰國、歐洲世界日報以及聯合晚報等六份報紙。除歐洲日報外,目前每一份報紙都已有盈餘。
四十年的大小戰役中,王惕吾少數失算的案例之一是,聯合報最強勁的競爭對手--中國時報,因率先使用彩色印刷,而使報份快速成長。他不諱言,當初他並不贊成彩色印刷,因為全世界的報紙都講究內容、水準,除了星期天的書報外,沒有用花俏的印刷來吸引讀者的。「後來我無法違背競爭大勢,」他坦承。
融入趨勢當務之急
台灣的大勢在黨禁、報禁解除,強人政治告終後,瞬息萬變。位於忠孝東路四段的聯合報大樓堅穩踏實,但過去聯合報賴以成功的企業文化和創業精神,在社會急遽變遷下,已難掩動搖。
明顯的事實是,倫理和人情愈來愈不可恃。當躺在病榻上的王惕吾仍殷殷關切老同仁年關是否難過時,有人舉著白條,在聯合報大樓前抗議受屈;當聯合報自覺提供了最好的工作環境,而以留住人才為榮時,有員工結朋跳槽,向聯合報的「向心力」挑戰。
「聯合報的企業文化在流矢,」一位高階主管憂心地說:「如何融入社會脈動,重塑聯合報精神,是當務之急。」
強人形象的王惕吾創造了聯合報王國的第一個四十年,接棒的第二代若要打開新局,得先解答這道考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