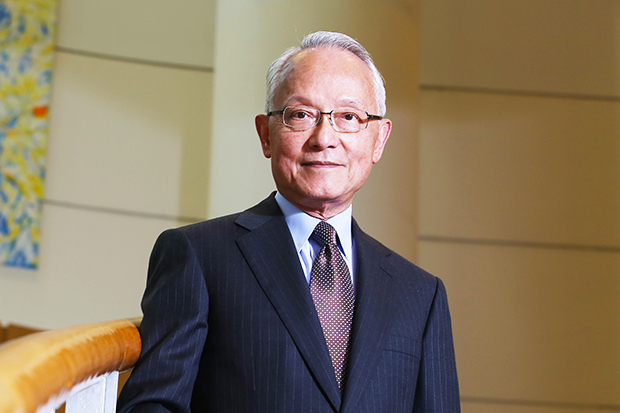我會說,當我每天面對每一位病人時,如何恪守「首先,不造成傷害」的誓言。輕如,我有沒有花時間讓他們了解,如何自我照護,說服他感冒不必看醫師、也不必吃藥,但有不安時,可隨時找到我;重的,如我們提供高危險的治療時,是否為病人做了最周全的評估,確定病人的身體與心理的狀況撐得過險峻的治療過程。我們的醫護團隊是否有充分的能力應對所有可能發生的狀況,而不致因為治療而加速病人的死亡,都是我每天工作時會遭遇的挑戰,也是我不斷地在修習的功課。
至於最大的挑戰,則是一件在1980年代中期發生的事。當時我服務的杜克大學醫學院,從哈佛聘請了一位骨髓移植的專家,他主張為高期別的乳癌病人,做自體骨髓移植的治療。
根據我自己的判斷,那樣的療法,療效可疑,傷害性太大。因此,我向內科主任提出我的疑慮,但是,因為這位專家所發表的論文宣稱他在哈佛的初步試驗效果顯著。之後,病人慕名前來杜克求醫,不久全世界知名的醫學中心也紛紛跟進。那時,美國大多數保險公司都因為該療法費用昂貴,而且,還沒有經過隨機臨床試驗(RCT)來證實其療效,所以拒絕給付。結果,有不少病人因此提出訴訟,保險公司敵不過輿論的壓力而投降。為了解決爭議,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決定進行隨機臨床試驗。多年後,結果揭曉,乳癌自體骨髓移植療法才被放棄。
這中間還有個插曲,最早報導臨床試驗結果很好的南非醫師,被發現其研究造假。這是一個極具戲劇性也極值得醫界引以為戒的慘痛教訓。
重要決策須經過團隊討論
那麼,如何不傷害病人呢?就要永遠保持謙卑的態度,不斷地增進知識,以加強自己的判斷力,此外,還要時時向專家諮詢,來彌補自己的盲點與人性的弱點。
行醫最大的困難是,如何為病人做最正確的抉擇。雖然,不夠熱情的醫師不願為病人多走一哩路,不會為病人赴湯蹈火,就無法為病人解決困難的問題;但是,熱愛病人的醫師,也可能失去客觀,以為自己慈悲為懷,英雄式地想為病人爭取最後一線希望,然而,動機再良善,如果病人的身心經不起險峻的治療時,醫師的熱情往往加速了病人的死亡。
21世紀先進的醫療確實可以克服很多困難的醫療問題,但是,高難度的醫療無法單打獨鬥,而必須依賴不同專業的密切合作。所以,我一再地提醒我的同仁,做任何重要的醫療決策時,一定要經過團隊的討論。激烈的辯論是熱情的呈現,最後一定要達到共識,做了決定以後,大家就要同心協力、全力以赴為病人爭取最好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