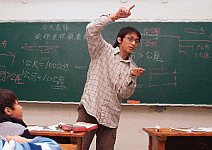「歡迎嚐嚐看喔!」轉身拿起一盤香甜酥脆的餅乾,臉上黑紅暗影斑駁交錯、五官變形的燒燙傷友,笑容洋溢地走進一群高談闊論的記者間,悉心招呼大家,品嚐他們的手藝成果。
長久在旁人異樣眼光下生活,人們對燒燙傷的人印象總是內向封閉。在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與茉莉二手書店合作的「二手書換捐款」記者會上,燒燙傷友的開朗,讓在場眾人動容。自1981年成立,陽光基金會已經讓數千位顏面損傷者,重新找回自信心與成就感。
陽光基金會並不孤單。根據內政部統計,台灣社會團體自1997年的1萬2825家,到2005年,已有2萬6139家,足足成長104%。(見頁202表1)
不僅數量有著超速成長,這幾年,非營利組織(NPO)的規模也同步擴大。
根據《第三部門學刊》的「台灣前50大基金會發展生態分析」顯示,台灣前50大基金會基金總額自1991年的106.2億元,2001年已躍升至636.2億元,成長近五倍。(見頁202表2)
第三勢力,庇護官商棄守之地
「非營利組織是社會參與力發展的縮影,」東吳大學社會系教授楊孝濚說。
過去20年是非營利組織的快速成長期。1986年解嚴後,人民團體法、集會遊行法修正,促使人民意識覺醒。在喜馬拉雅基金會所做的「台灣300家主要基金會調查」顯示,超過五成基金會都是在解嚴後10年內成立。(見頁202表3)
從1980年消基會發起消費者運動,標誌民間衝撞體制的勝利,20多年來,非營利組織一直在台灣社會各個領域,點點滴滴改善台灣
路見不平的社服團體,致力讓身處社會邊緣,長久遭到漠視的弱勢族群,獲得公平對待。
例如,過去,銀髮老人往往被送至設備簡陋的安養院,台中的天主教曉明社會福利基金會卻以慰問、復健的居家服務,讓長者獲得良好照料。
又如,雛妓曾被視為常態,被推入火坑的少女只能躲在暗角哭泣,但在勵馨基金會用廣告、座談、活動大力推動「反雛妓社會運動」後,社會大眾開始正視兒童性受虐問題,讓「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三讀通過。
再如,哀人所哀的醫療團體,努力讓醫療環境合理化,讓保健觀念深植人心。
曾經,病人不敢要求醫療品質,不懂如何自我保護,導致醫院蠹蟲橫行。在醫改會的奔走呼籲下,「藥袋標示」成了基本常識,原本難以流通的病歷,也有了清楚的標準。
當企業汲汲營利,政府官僚緩慢,非營利組織愈來愈成為台灣社會不可或缺的第三勢力。
「其實很多人都有能力外移,但就是因為不甘心、不放心,所以一直留下來耕耘,」台大社工系助理教授,同時也是醫改會副執行長的劉淑瓊道出了許多非營利組織工作者的心聲,「學術界很安逸,可以過得不錯,但是若知識只是拿來升等,真的很可惜,為什麼不貢獻社會?」
NPO規模,全球第七大經濟體
非營利組織是社會良心,若說政府是軸承,企業是滾輪,非營利組織就是拉動社會進步的牽引帶。
在美國,非營利組織是最大的雇主。而就全球規模來看,1995~1998年,35個國家的非營利組織部門總共創造1.3兆美元的產值,堪稱全球第七大經濟體,僅次於美、日、中、德、英、法。
在台灣,非營利組織的就業人口,也從1999占全國總就業3.4%,提升到4.6%。
甚至非營利組織也已成為一門新顯學。現在有愈來愈多人願意以專業、嚴肅的態度,去思考如何有效能、有效率地經營非營利組織。
翻開政大EMBA的通訊錄,會發現晚晴婦女協會總幹事羅瓊玉、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總幹事林錦川、光寶文教基金會執行長張豫偉、研揚文教基金會執行長黃慧美等人都在此進修。
政大EMBA有非營利事業管理組,中山大學有國際非政府組織研究中心,而台大、輔大、中正、暨南大學也不落人後地跟起這波非營利組織學習潮。總計全台已有20幾所大學院校,開設非營利組織相關的學程。
去年10月申請留學、寫推薦信的旺季,台大社工系教授馮燕發現,申請念非營利組織的學生,較往年增加許多。「現在非營利組織已經是個顯學,」馮燕分析,過去強調的是專業分工,在面對愈來愈複雜的問題時,科際整合的能力益形重要,「所有事都講求綜效,而非營利組織就是綜效的實踐。」
隨著非營利組織日漸熱門,年輕人對於進入錢少事多的非營利組織工作,也不若以往畏懼。
1979年生,身材瘦高、總帶著陽光笑容的牛慕慈,台大公衛系畢業後,就選了與非營利組織息息相關的復健諮商,做為出國留學的主修。「當初出國念書,就已知道回國工作不會賺大錢,」現在在陽光基金會當心理師的牛慕慈,也知道長輩難免會比較子女的薪水,但她希望自己「活在世上不只賺錢,還能對社會有幫助。」
當非營利組織管理的教育日益普及,台灣草根性強的基金會與社團組織,可望在專業度與透明度上,獲得下一波的提升。
社會企業,做生意也做公益
現在口袋充實的企業,也成了許多非營利的組織的源頭活水。
為推廣日漸式微的京劇藝術,成立魏海敏京劇藝術文教基金會的名伶魏海敏,就大歎會務經營困難,不募款絕對不行,「一年只孳息1萬、2萬元,連付房租都不夠!」
走進暖色調的喜憨兒烘焙屋,很難不想起花旗的喜憨兒認同卡。這張自1998年開始的公益認同卡,標榜將消費金額的0.275%捐拾喜憨兒基金會,配合大量媒體宣傳,至今發卡量超過18萬張,每年捐助金額在新台幣800萬元上下。
「企業要的是形象,非營利組織要的是資源,是一種各取所需的伙伴關係,」國家文藝基金會總監曹鸞姿表示,雖然國藝會是政府型基金會,但「科技藝術獎」「聲音藝術展」等需要大量電子設備、耗資可觀的大型專案,都是仰賴企業的慷慨贊助,才得以成形。
自1993年美國哈佛大學成立「社會企業發展中心」、1997年史丹佛大學成立「社會企業家精神發展中心」,引起許多商學院跟進,開發營利「社會企業」的概念就像野火燎原般,成為非營利組織、媒體的熱門話題。「有遠見的社會事業經營者,能以更有效的方式,為世界人類謀福祉,」史丹佛大學公共服務系教授迪斯(J. Gregory Dees)說。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非營利組織以使命感為斧,以行動力為鑿,用點滴汗水開鑿出台灣更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