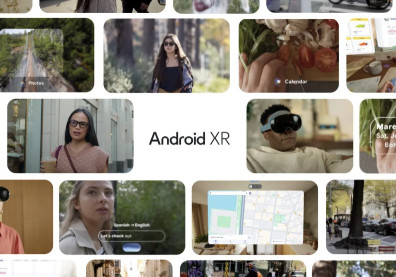一九九八年年底美國明尼蘇達州長改選,代表「改革黨」出馬的職業摔角選手溫杜拉(J. Ventura),在民主共和兩大黨的夾殺下,逆勢高票當選,跌破所有專家的眼鏡。這是美國政壇「第三勢力」前所未有的勝利,也是有史來第一場「虛擬競選」的勝利。
不論基層組織或競選經費,改革黨都遠非兩大政黨的對手。沿用傳統的選戰策略,溫杜拉難有勝算。但網際網路這個利器,卻重新改寫選戰的規則。溫杜拉沒有競選總部,幹部會議和拜票安排,全部在線上進行,租辦公室的預算就這樣節省下來。
「小本經營」的溫杜拉,只花了六百多美元架設個人專屬網站,結果收效千百倍於此。他透過網站廣泛募款,義賣印製他肖像的 T恤。就連他為選舉向銀行貸款,也是從網路徵求到保證人;競選經費總計有三分之二是從網路「化緣」來的。
如虎添翼的是,溫杜拉從網站招募到三千名義工。他巡迴拜票所到之處,都事先透過網路聯繫義工到場助陣,使他的場子特別聲勢浩大。兩大黨縱使基層組織龐大,也很難動員這麼多群眾。溫杜拉在媒體的曝光度,自然也就「高燒不退」。
溫杜拉的細心處是,隨行的攝影人員立刻把造勢會場的畫面,用筆記型電腦傳回網站進行編排。義工們返家後,打開電腦與溫杜拉連線,就能在網站看到自己的照片,感動得更加死忠。
體格魁梧的溫杜拉,從前在職業摔角界外號「身體」(body)。網路奇兵的選戰策略,使他博得「頭腦」(mind)的新外號,甚至被封為「網路時代的JFK」(JFK指美國故總統甘迺迪)。
用科技打選戰
回顧本世紀的美國政壇可發現,每隔約四十年,選戰模式就會被傳播科技徹底顛覆一次。誰最先掌握新科技,誰就是贏家。
一九二○年代,美國跨進收音機的時代。最先洞悉其政治潛力的,就是羅斯福總統。當時流行的選戰招式不是全國巡迴演講,就是嘉年華會遊行。罹患小兒麻痺症的羅斯福,先天就吃了大虧,但他卻靠著天賦的沈穩嗓音,用廣播征服美國選民。
一九六○年,甘迺迪和尼克森的電視辯論會,象徵美國跨進電視的紀元。比起政治閱歷,甘迺迪遠不如尼克森,但在講究形象包裝的電視上,甘迺迪的年輕成為資產。與其說尼克森敗給甘迺迪,不如說是敗給電視。
「四十」年風水輪流轉,電視的政治霸權,已開始面臨網路的挑戰。九六年美國總統大選時,「年高德劭」的共和黨候選人杜爾率先向選民公布網址,純粹是爭取年輕選票的噱頭;並沒有任何參選人真的把網路當回事。
然而,即將起跑的兩千年總統大選,很可能是美國「網路政治」的元年。四年前那場選舉,美國選民的網路普及率不到一五%,今年可望提升到七○%,誰都不能再忽視這個戰場。
在民主黨方面,呼聲最高的現任副總統高爾本身就是標準的網路迷,競選班底的網路高手如雲。《新共和》週刊報導說,高爾每天都要瀏覽自己的網站好幾次,隨時提出改進的意見。
共和黨方面,專屬網站最「炫」的,要算是《富比士》雜誌老闆佛柏斯。不滿意媒體報導的他,乾脆把演講搬到網路,自己做實況轉播。只要捐出十美元,就可報名參加團體聊天室,跟佛柏斯線上對話。
更有創意的點子是,用網站招募「電子選區領導幹部」。只要在佛柏斯網站輸進簡單的個人資料,就完成登記報名的手續,成為佛柏斯競選班底的成員。你招徠的支持者愈多,頭銜也就愈高,從「電子街區」的區長,升格為「電子市」的市長,最後晉身「電子全國委員會」。佛柏斯的網站將設置你的專屬網頁,透過電腦連線,你就可參與競選總部的決策,分享機密的選戰情報,貢獻所見所聞或獨家創意。
同樣角逐共和黨總統提名的卡西奇(J. Kasich), 網站則採取因地制宜的設計。不同州別的選民上卡西奇的網站時,看到的內容也不同。
還有別的方式可做到這種「分眾傳播」。例如亞里斯多德出版公司(Aristotle Publishing),就和美國線上(AOL)合作,接受佛柏斯的廣告委託。AOL 過濾網路用戶的資料後,就可讓佛柏斯競選網站橫幅廣告(banner ads),出現在他指定對象的電腦螢幕上。
瓦解金權政治的利器
網路絕非花俏的宣傳伎倆而已,更捎來政治良性化的希望。
「網路可以幫你打一場低預算的選戰。即使財力不如人,也能跟有錢的對手平起平坐競爭,」美國加州選民基金會理事長亞歷山大(K. Alexander)說。
競選經費的惡性膨脹,不啻民主政治的致命傷。最會吃錢的,莫過於電視和郵件廣告。這迫使政治人物下海,接受非法的政治獻金。除非有主流政黨與財界做靠山,或是本身財勢雄厚,否則很難有出頭的機會。「物美價廉」的網路,正是瓦解金權政治的利器。
十九世紀時,參選者的群眾演說,經常「馬拉松」幾個小時。收音機問世後,縮短為數十分鐘。進入電視時代,競選廣告更精簡到以「秒」計算。轉瞬即逝的片刻,除了聳動的口號與影像,根本無法傳達任何政見,膚淺成為政治的寫照。
相對的,任何長篇大論的政綱,選民都能輕易從網路下載。參選者有無真材實料,在網路無所遁形。
「網友造訪政治網站,平均瀏覽八分鐘。比起電視廣告的三十秒或電話拉票的四十五秒,這簡直就像『永恆』那麼長,」創辦「心靈分享」網路競選公司的西格爾(J. Seiger) 比喻。
「網站提供新的選舉技術,吸引有深度的選民。他們要充實的訊息,傳播媒體對候選人的包裝,引不起他們的興趣,」哈佛大學教授喀瑪克(E. Kamarck)說。
參選者經由網路,可直接把訊息傳達給選民,不必受媒體的制約。傳統媒體的報導篇幅無疑偏厚主流政黨,透過網路自行發聲,邊緣政黨或獨立候選人更有機會脫穎而出。
《網路政治》作者韋恩萊施(Wayne Rash)指出,現在許多傳統媒體乾脆從參選者的網站取材,節省採訪的成本。
組織戰移到網路上開打
在爭取新支持者方面,競選網站的功效如何雖然尚無定論,但可以肯定的是,要把現有支持者組織動員起來,網路絕對事半功倍。
透過網站招募競選義工,效果得到公認。由於美國的投票率低落,競選義工格外重要。在投票日當天,他們可以把老弱殘疾者開車運送到投票所,或協助家庭主婦臨時看顧小孩,用各種能想到的方式動員支持者投票。
喀瑪克教授在《民主.com?網路世界的統治》書中指出,九六年約翰凱利(J. Kerry)在參議員選戰的險勝,和九七年惠特曼(C. T. Whitman) 在州長選戰的險勝,都是在倒數計時階段,藉由網路動員義工,才踢進臨門的一腳。
若論募款的潛力,網路堪稱吸金機器。方便性是它的優勢,支持者不必親自到造勢會場,把錢投進募款箱;也不必跑到金融機構,填寫表格匯寄支票。只需要坐在電腦前,敲進信用卡的帳號,滑鼠點幾下就輕鬆完成。
喀瑪克教授指出,美國民眾政治捐款的動機是很現實的。與其說是候選人的形象,不如說是在特定政策議題上所持的立場,才是決定捐款與否的因素。網路能容納長篇大論,是發表政策的最佳工具,吸收捐款當然駕輕就熟。
亞里斯多德公司估計,今年美國總統大選,從網路募集的政治獻金將占全體的五%到一○%;二○○四年的總統大選,更可望躍升到八○%。
傳統政黨打組織戰的方法,是發展地方黨部系統,扎根到地方民間社團。但美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安德魯(J. Andrew) 坦言,地緣性團體的衰落使得組織戰愈來愈難打。相反的,網路同好的虛擬團體數量卻呈爆炸性增加。未來的組織戰,可能要移師到網路開打。
「人們現在透過網路,愛花的跟愛花的串連,愛車的跟愛車的串連。從前政治的基礎在於地理,今後政治的基礎在於共同興趣,」安德魯說。
文宣戰的雷達
文宣戰方面,網路最有威力的就是「目標鎖定」(targeting) 的功能。在選民這塊大餅中,網路可輕易搜尋到潛在的支持者,把量身訂作(customized) 的文宣訴求對準這小部分的選民發送,不至於把有限的經費和時間虛擲在不可能投票給你的選民身上。
舉例來說,假設有位哈特先生打算在波士頓競選議員。他的專業是環保議題,曾經出版垃圾焚化爐的專書。選舉文宣的訴求對象,不消說是環保取向的選民。
哈特先生花筆小錢,就可從網路搜尋引擎公司買到波士頓地區登記用戶的資料。有誰搜尋過環保組織的網站,即刻呈現在眼前。哈特先生不費吹灰之力即可取得登記用戶的住址和e-mail帳號。哈特先生按著地址,文宣品就可直搗票倉。
哈特先生如法炮製,跟當地的電子報接洽。凡是在線上瀏覽過焚化爐報導的讀者,他都買得到名單和地址。而網路書店那裡他也可付費檢索,查出在波士頓地區誰購買他的著作。有了網路做引導,文宣戰就好比安裝了雷達。
近年來,商業領域的顧客資料庫擴充速度極為驚人。隨著電子商務的盛行,業者利用俗稱「餅乾」(cookies) 的技術,顧客的線上消費行為被無所遁形地追蹤記錄。這些商業資料庫,成為美國政界急欲勘探的金礦。
「消費者資料庫的擴大,把前所未有的巨量資訊放在參選者(敲電腦)的指尖下。他們不但掌握你的姓名、年齡、住址和投票紀錄,還知道你的家庭組成、房屋是買的還是租的、你訂閱什麼雜誌、開什麼車子、是否吸菸喝酒、去不去教堂、做什麼運動,以及各種購物嗜好,」《新共和》週刊寫道。
利用龐大的商業資料庫做基礎,只要搭配簡單的問卷,經由電腦分析,候選人就可獲知支持者的精確定位,祭出投其所好的選戰訴求。例如去年美國參院期中選舉時,民主黨奧勒岡州參選人羅恩韋登(Ron Wyden ),借助這套技術,才發現他的「鐵票部隊」是在亞裔比例和教育程度皆高的社區中無黨無派的年輕選民。傳統的問卷統計方式受限於樣本數太少,根本無法把如此特殊的群體篩選出來。
被侵略的選民隱私權
同樣借助商業資料庫,美國有些政治顧問公司,已經能將選民這塊大餅,精細切割出多達六十種「生活形態聚落」。什麼樣的聚落,就訴諸什麼樣的宣傳劇本。
樂觀者認為,選舉宣傳的量身訂作化可提高選民的投票興趣,沖淡利益團體「投票部隊」的影響力。但是《一對一未來》作者瑪莎洛格絲(M. Rogers)質疑,這將鼓勵政客濫開競選支票,「對這群選民做這個承諾,對那群選民做那個承諾,即使兩者互相矛盾衝突。」
此外,選民隱私權被侵犯的問題,更是不容忽視。電子競選的技術難題已逐漸被克服,但政治倫理的挑戰卻方興未艾。
比起電視的宣傳效果,網站固然在「分眾行銷」更勝一籌,但正如美國民主黨媒體顧問施若姆(R. Shrum)指出的,「選戰最後決勝的關鍵,往往在於對政治較冷淡的中間選民。要想確保你的訊息能傳達給他們,唯有透過電視。因為網路宣傳的前提條件在於,選民會積極主動去蒐集政治訊息。然而大多數的選民,其實都是政治訊息的被動接收者。」
無論如何,網路政治的旋風在世界各國都蔚然成形。地廣人稀的澳洲今年初舉行大選時,勞工黨的網站在五週內吸引兩百萬人次造訪,而澳洲全國選民總共不過一千一百萬人。比起費時耗力的巴士巡迴拜票,成本效益不知高出多少倍。
同樣的,去年九月間德國薩爾邦議會選舉時,一向給人老朽印象的基民聯盟(CDU)也借助炫奇的網站,使年輕選票大幅成長一七%,擊敗執政十四年的社民黨。甚至德國綠黨也熱衷架設網站,以洗脫「敵視科技」的形象。
從英國到美國加州,都正在醞釀開放網路投票。果真如此,網路世界的政治硝煙味將會更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