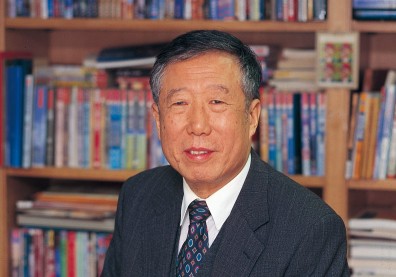漫天風沙中,你的孩子是牧羊人,嘴裡叼草、手拿長棍;當你領讀航經世界的知識,他轉頭不理,還挑戰你,究竟你是粗暴還是管教?愈愛他,他愈搗蛋?你的愛,到底還有多深?攤開世界地圖,請試著找出賴索托(Lesotho)在哪裡?
這個位在非洲南部的小國,約是台灣的10分之8倍大,是全世界最大的國中之國,全境完全被南非共和國包圍。因地處高原,又有「天空王國」的稱號。陳緯哲就是在這裡開始他的冒險之旅。
那年春天,華語系畢業、在雜誌社工作的陳緯哲剛滿24歲。當全球華語熱,一條華語老師的路,該怎麼走才算特別?最後,他落腳在南非境內有著無邊藍天黃沙覆蓋,愛滋盛行的一個小國──賴索托。
他說:「與其轉述別人的生命如何對世界產生改變,不如自己冒險,闖出自己的故事來得真切!」但是出發以後,很多事情都與常人所說的故事不同:離家尋找新的歸宿,但家的呼喚依舊強烈,現實逼著年輕的生命做出選擇……然而世界上沒有兩條河流,曾切割出一樣的山谷,還以同樣的曲折角度入海,即使出發前也曾因徬徨哭泣,面對自己不安且隔閡的心,他仍舊打算創作屬於自己的「故事」,放手一搏的冒險。如果有機會,你是否選擇像他一樣出發?一起看看他的冒險故事:
2015 年3 月,我初次抵達這個天空之國。在南非約堡由人派車接入賴索托,一過邊境,印象最深刻的是路旁的招牌中,有不少竟都是寫著殯葬服務。而這一次的出發,我則是以志工的身分申請來到這裡。
那時24 歲的我,出發前歷經了祖父過世,也曾在大學期間喜歡的雜誌社實習、任職。這樣的人生,正安穩步上軌道,往人生的下個階段前進。
只是我喊停了。當年紀相仿的受訪者,在雜誌中說明他的理想與抱負,我的心竟也怦怦跳著。大學主修對外華語教學,卻從未出國實習的我自問,「我是不是還有未完的旅程?現在不做,以後就不會做了?」就在這個念頭的支持下,我離開了雜誌社。原先家中重病的祖父緊接著過世,彷彿塵埃落定的片刻,我找到了我的目的地。
是哥哥也是老師
我所服務的是位於賴索托的阿彌陀佛關懷中心(ACC),它是台灣慧禮和尚花費20年在非洲成立的孤兒院,著眼的不免是宗教情懷,但更多是對這塊土地上流離失所孤兒的同情。除了賴索托,馬拉威、史瓦濟蘭、納米比亞也有據點。收容孤兒、提供教育直到他們成年。如果可能,還資助他們讀大學,希望他們能成為非洲往後社會中堅,透過教育跟知識轉換他們父母雙亡,可能失學流浪的命運。
儘管有這樣的目標,但真正面對孩子時,又是另一種情境。來這裡當華語老師,絕對不同於海外其他華語老師的機會。教學地點是關懷中心附設的圓通學校,也有當地老師教授課程,但在華語課程外,我們24小時與小孩住在一起。每天眼睛睜開,念頭就是孩子。因為他們是孤兒,所以我們就是小孩的家長、父母、哥哥、姊姊。我們關心他的健康、飲食、個性、品行、課業;在以中華文化給他們薰陶的同時,也確保他們沒有和賴索托傳統文化脫節。230個年紀從4歲到16歲的孩子,由近20位華人,帶領當地保母、老師、守衛,共同維持。
刻意隨興而放逐般的旅程,收穫也如意外一般,總是可以令我驚喜,而打從心裡感到甜蜜與哀傷。以往從未想過進行幼童教學的我,沒想到自己現在會那麼的喜愛小孩。初見面時,黑人小孩一個個因為這裡的佛教禮儀薰陶聲聲「阿彌陀佛」向你問好。一個個看起來也都像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
直到後來,日久相處,我開始會說,「其實他們真的沒有那麼黑啦!」「你看誰誰誰的眼睛很特別」。他們一個個都在我的心頭占據了一個地方。而雖然這些孤兒在收養進院之初,我們都會給他們一個中文名子,男生以「天」為首,如「天南」、「天賢」:女生以「地」為首,如「地惠」、「地珠」,我還是會盡量學著說他們當地賴索托語(Sesotho),用他們的原名叫他們。
也許因為天天都有課堂教學,也都會到小孩房陪伴他們的緣故,距離感消融於無形。我是個沉默的人,在小孩房的陪伴,起初總是觀察,早晨他們將毯子疊成豆腐乾狀、拿杯子倒水;我四處走動,看他們小小年紀在廁所用大盆子洗衣服,尿床的就把床墊拿到中庭去曬。為了熟悉,一個一個問名字,問到小孩用中文說,「你已經問我第5遍了」。我才不好意思地說,這次我一定記住。
課堂上,小孩叫我「老師」,下課很自然就改口為「哥哥」,最近甚至有小孩發明出「哥哥老師」這樣的稱號。在我聽來,都是再高興不過。因為我們在這裡所扮演的角色,本來就不單純是老師或外來者,而是應該能深入孩子心底的家人。
有小孩曾在課堂上,用英文在面紙上寫著幾行字,拿給了我,讓我很難忘。上面寫著“I am a boy, I love you. My friend and I put you on my heart.”(我愛你,我和我朋友把你放我的心上。)
作為老師,白天上課;作為哥哥,晚上陪自習。儘管英文還沒好到能解釋他們的數學題,卻可以用淺顯的計算讓孩子意會。晚餐後下雨了,孩子沒帶雨衣,就把他裹在自己的雨衣裡,一起前行。
在台灣家裡是長孫,但卻也沒想過要如何關心照顧弟妹。來到賴索托,面對只能用淺顯中文溝通、心思單純的黑人小孩,卻是心思細膩的想把他們捧在手心。「就像自己的小孩、弟弟、妹妹一樣。」
回家的呼喚與孩子的牽絆
常在院區小孩房四處走逛的我,一天不經意被問:「你走的時候,這個(指著手錶)可以給我嗎?」我問:「你那麼想要我走嗎?」小孩說:「你走,我們會哭。」我想:「那為什麼要這樣問呢?」
關於離開賴索托,我總有很多想像。他人問過,我回答,既然都是家人,哪裡有離開家人的理由。然而,想著台灣的家裡,透過無遠弗屆的通訊軟體傳來的訊息,無論是家人摩擦吵架、還是長輩的失智或行動不便,都像是在敲著一聲聲回家的催促。
面對賴索托的孩子,我能給多少承諾?這個院區成立5年,來來去去的華人職義工可能接近上百,也因此孩子知道,有那麼一天,你會就此消失在他們的世界中。也因此,他想問你能夠留下什麼,是帽子還是鞋子。但我們這些曾在這邊停留的人,所帶來、付出的,就是時間與精力的陪伴。我曾想過,也曾給過的承諾是,我要帶哪個小孩到台灣看我的家。你沒有媽媽了,就來看看我的媽媽吧!
還不到我離開賴索托的那一天。但每每目睹院區的車載著別人遠去,感覺總像生離死別。曾經日夜相伴,今後是萬里之外。看著別人走,總會想像自己也會有那麼一天,而那天又會是個什麼場景,該掉下多少眼淚。曾經,我以為自己是因為一無所有,沒有經驗,也沒有包袱,才會來到這裡。今天我看見,正是因為我擁有的太多。我的原生家庭,我生長的社會、台灣給予我的養分太充沛,讓我充分體會到自我的富足。那些曾經給過我溫暖的,就是我今天如此樂於給予擁抱的原因。
一段人生,換一段回憶。其實是你的回憶,也是他的回憶。「你認識青老師嗎?」在賴索托,同樣的句型,人名可以代換成其他老師。這些人,我都不曾真正認識,但經常聽到,也算認識了。你來過、待過,最後離開。但是離開的,從來不會真正離開。因為你們都住在孩子們打鬧聊天的話題中,他們永遠的回憶中。
「你希望我待多久?」當孩子問我何時要回去這樣的問題時,我總是這樣回問。孩子說,「待到我老的時候」、「待到我26歲......」。其實這答案,這承諾,我說不準,也給不起。
也許,等我住進你們的回憶裡時,就永遠不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