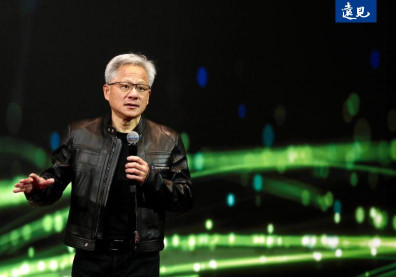沒有人喜歡說錯話,但為什麼有人總是失言?說話得體跟不會說話的人之間,有沒有一種說話的「藝術及技術」區別?
蔡穎卿跟洪蘭認為,得體的說話源自一種「距離美感」,因為距離讓說話的人彼此拉出一個相互尊重的空間。尊重的心,會讓說話像對位音樂一樣,才能彼此傾聽、相互應答,達到說話溝通真正的目的。
說話得體1:先分說話場合的主客體
洪蘭( 以下簡稱「洪」):老爺酒店集團執行長沈方正在他的書《能被小用,才是大才》說,現在的人好
像完全不懂得說話禮貌。他舉例,一天,有個公家單位租他們場地辦活動,他親自出來招待。一位年輕女生看到他就講,「我是XXX,這個活動窗口是XXX,你有事情就直接去找他。」沈方正當下想:再怎麼樣我也不是執行窗口。
後來,他仔細觀察這個女生,發現她也不是故意的,她跟每個人說話都是用同樣的態度。這個年輕人不看對象、不看場合,說出來的話就會顯得她「白目」。
人跟人之間需要語言的距離,尤其彼此不熟的時候,距離是尊重,是一種安全,也是美感。日本人講話時有很多敬語,他們非常在乎距離遠近關係。
記得有人告訴我,她去日本說日語都沒有人願意跟她講話,後來才發現,因為她學的日語是人家認為很粗俗的,在日本,有教養的人講話很客氣,但是她沒有學到這些,所以到處碰壁。
蔡穎卿(以下簡稱「蔡」):得體的說話不但要分場合,同時也要了解講話的主客位置。曾經有媒體訪問我要拍照,工作人員對我說:「你今天穿的衣服不好,跟書架顏色太像。」這就是立場錯置的話,這樣的口氣好像不是請我做一件事情,而是在指責我。
我受的教育教導我,當別人請吃東西時只能說「謝謝!」,絕對沒有立場說「還不錯吃!」。對別人請客總要表示謝意,而不是評論口氣,說話方式、語氣的拿捏,都不應該失去我們說話的立場。洪:主客體立場至少要分辨今天是誰幫忙誰,但現在居然很多人都不會。有出版社要我幫忙為一本書作推薦,他寄來書稿是星期五,然後叫我星期一寄回去。我心裡想,怎麼只給我3 天時間,我不是吃你的飯,也不是你的職員。後來跟對方反映3 天時
間不夠,他居然說:「我沒叫妳一定要看,我只需要妳的簽名,這是掛名推薦。」後來我就寫信給出版社老闆告訴他,你們的工作人員真是太沒禮貌了,而且做事方法也有問題。
蔡:分清楚講話主客體外,看場合說話也很重要。我不知道洪老師同不同意,政務官是不能有臉書的?
洪:不可以,絕對不可以。前行政院發言人胡幼偉在臉書上發言說是個人意見,離開後還在臉書上說:「唉呀!你們是不是高興死了,你們最喜歡的老師又回來教你們了。」這真是太糟糕了。他以為臉書是個人身分,其實當政務官就是代表政府團隊,哪有分什麼私人身分?
蔡:因為沒有任何人可以幫你判斷,你這時候講話是用個人身分,還是官方身分?顯然,大家覺得什麼場合說什麼話是重要的,但放到個人身上就輕忽了。
我曾經接過編輯寫給我的信說「好愛你喔!」或者以「親愛的」為開頭、「念念」為結尾,但這位編輯我從未見過面。我認為,親近可愛不是每一種關係都適用,而是要看場合,人和人之間通常要選擇比較成熟的態度,特別在工作上更要如此。
上個禮拜跟一位雜誌編輯討論新專欄,她講到一個關於用語的例子讓我很贊同。她說,在國際採訪場合,中國記者問的問題不一定真的很好,可是因為他們用的語言比較正式,所以會讓人家感覺他們相對於台灣記者更為專業。
說話得體2:用字遣詞講究雅
蔡:語言本來就有經驗上的約定俗成,成為「雅」或「俗」。某些字,像「爽」就是比較難聽的字。在古文裡面,它是「差池」的意思,像屢試不爽,但後來有人把它用在男女之事上,因為與生活習慣的連結認知,大家會有另一種想像,所以「爽」這個字就不適合到處說。
洪:現在動不動就說「我不爽」,以前是說「我不喜歡」。有天,我問一個學生考試考過沒?他傳手機簡訊給我,就回一個字:「爽!」他們不了解,這個字是很粗野的。
蔡:洪老師有一次在演講場合提到,現在年輕人都稱自己先生為「老公」,其實是很粗的話,我也深有同感。可是我回來告訴我的學員,他們就問:「為什麼不好聽?」其中有位學員回答得很好,她說:「雖然我不知道老公為什麼不好聽,可是有一次我們跟曾志朗部長開會,院長花5 分鐘講洪蘭老師,他的代稱詞都是『洪老師』,雖然那5 分鐘都是在講洪老師有多麼好,可是完全不會讓人有肉麻的感覺。」我覺得她這個說法恰巧就說明了,適當的語言距離會讓人比較舒服。
洪:有一陣子我們很強調「草根性」,但是草根性並不是草莽粗俗,草根性是腳踩在土地上,比較純樸踏實,但絕不是粗俗。所以我說LP 不可以在公共場合講,這是一個很粗俗的字,尤其不能用外交部長的身分來講。他們這樣等於把粗俗當作草根性,誣蔑了草根。
蔡:語言的使用在無形當中會影響別人對你的尊重。我不能理解像「事業線」這種明顯貶低女性的話,連女記者自己都講得很開心而不自覺。如果我們希望得到別人的尊重,這種字就不應該拿出來講,自重發言,等於是傳遞給對方知道一定要尊重你,當對方講出不禮貌的話,一定要有所表示,就算沒有嚴詞駁斥,也不要加入起鬨。
洪:「 事業線」這個詞是怎麼來的?
蔡:應該是從綜藝節目出來的,但現在連專業的新聞女記者也這樣說。
洪:我比較擔心的是,很多一時的流行語變成語言的一部分,雖說語言一直在轉變,但是我們都希望它是朝好的方向變,而不是朝粗俗的方向變。其實大眾傳播媒體的影響很大,它形塑強化社會的慣用語,如果它粗俗,我們不知不覺也不覺得難聽了。像昨天報紙標題寫:「撿屍」,就是喝到爛醉被男生撿走,真難聽耶!
蔡:如果專業人士都失去了他們對語言的準據,整個社會的語言要靠什麼來教養?我們不能只靠閱讀對不對?如果大家都以聳動為目的,今天你聳動,明天我比你更聳動,大家眾聲喧嘩,這就是白居易《琵琶行》說的「嘔啞嘲哳難為聽」。
洪:沈方正在書裡還提到,有人來面試會滿口粗話,「屁啦!」「誰鳥它!」聽到這些粗話就立刻叫對方回家了,才不看他是什麼學校畢業的。為什麼年輕人連面試的時候都會講粗話?可見得他們不覺得有問題,因為我們的大眾媒體整天都這樣講,同學們也這樣溝通,有人還告訴我,三字經是講話的標點符號,如果平常都習慣這種說話的模式,正式場合失言一點也不奇怪。
禮貌是年輕人的第一個機會
蔡:所以我一直認為禮貌是年輕人的第一個機會。
洪:因為有禮貌,他們才可能會進入這個公司,人家才會打開這扇門。他如果沒禮貌,人家第一眼就讓他走了。你在一個公司裡面要爬起來,不會說話、白目,你怎麼去跟人家工作?
蔡:我們怎麼教孩子?我們鼓勵孩子看報,但報紙都是這些字眼,該怎麼辦?
洪:我常開玩笑說:「 台灣報紙大概只能看《國語日報》了!」很多人罵我生活在維多利亞時代,但父母親自己要想清楚自己講的話,因為孩子是從父母身上學習,任何用字遣詞都是身教,會影響孩子將來的交友與就業,對他的影響非常大,因為講話粗俗的人,沒有人喜歡跟他交朋友。父母不要以為,當我講話粗俗的時候代表了我的草根性,而且要教導孩子尊敬長輩、長幼有序,跟長輩講話時應該要怎麼講,不可以對老師指名道姓,不管在哪個時代,這是基本的禮貌,你一定要教孩子禮貌,把孩子教好了,其實就成功一半了。
當孩子沒有教養,人家第一個罵父母,第二個罵老師,「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父母與老師都有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