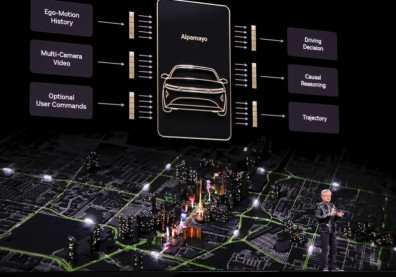醫藥分業爭議不休,台灣民眾的醫療權益,還搖擺在一張釋出與否波折重重的處方簽,全球的病人主權革命則已經蔚為趨勢了。
一九九四年十月,美國默士藥廠(Merck)宣布了一項創舉:凡使用其治療攝護腺癌藥品Proscar有不滿意者,可以退費兩百七十五美元。
藥吃不好可以退費,以前的人絕難想像有這等事情,但在今日卻成為可能。因為許多國家的醫療體系,已脫離過去唯我獨尊的專家形象,進入以消費者為導向的時代。
轉變之所以出現,與近年來許多政府共同的痛處有關--財政。
西歐的福利國家國庫日益捉襟見肘,不斷提高全民健保民眾就診的自付額度,於是民眾也相對要求樣樣都管的政府,給予人民更多醫療的選擇權與自主權。
以法國為例,過去法國人民連買維他命或皮膚過敏藥膏,都要經過藥師的審核。今日法國的納稅人則不僅要求能自由購買如避孕丸等常用藥品,也企圖以選票影響立法,改變過去只有醫生能決定患者用藥的規定。前年有個法國國會議員為了爭取選票,就打出了「讓民眾有權決定選用什麼心臟藥」這樣史無前例的政見。
醫療資訊大解禁
這種情況在美國則更為明顯。
美國為控制醫療支出在七0年代過於快速的成長,把全民醫療照護的經營權分給了各個「管理醫療公司」(managed-care firm),由這些公司向民間單位(公司或社區)販賣套裝的健保產品。
由於消費者是事先付錢,所以這些公司為追求利潤,會嚴格要求醫師每一樣診療,都是銀子花在刀口上,另一方面則要努力保持顧客滿意度,以免客戶跳槽至別家公司。
結果是,醫院或藥廠為了取得這些公司的合約,公布了許多被醫界視為禁臠的醫療資訊。
例如日前一項關於病人用藥傷害的研究在美國公布,其中發現六0%的用藥傷害病例,與一些醫師經常處方的心臟藥、抗生素或解熱鎮痛劑有關聯。像這類的訊息,過去很可能半途就被封殺在醫療體系之中,現在則成為一種公眾的資訊。
迫些資訊提高了民眾的知識與警覺,也相對提高了他們對於醫療品質的要求,以及參與醫療政策制定的企圖心。
以前通常只有藥廠或醫院會遊說政府撥出預算進行某些醫療研究。今日美國患者的遊說團體,則如雨後春筍般地興起。
例如美國著名的前垃圾債券大王米爾肯(M. Milken),在罹患攝護腺癌之後成立了CAPCURE基金會。他找來了前美國總統候選人杜爾等政經界聞人參與,最後不僅讓美國政府掏出荷包裡的鈔票進行新藥研究,甚至還在一九九四年宣布:當年的十月是「攝護癌知識月」。
不過,在爭取醫療主權上最有成就的,當屬美國的愛滋病團體。他們最戲劇化的事蹟,是主動引進英國一家生產愛滋新藥AZT的公司,以更低的價格打敗本土的葛蘭索大藥廠,取得政府合約。他們還主動負起了教育大眾、提供各種愛滋資訊的任務,並且進行反對醫護人員歧視愛滋病患的運動。
不做無知的病患
在這些團體身上,完全找不到傳統病患被動、無知的影子。
無知是世界各地患者在面對醫療體系最大的痛楚。到醫療院所就診,常有類似的經驗:醫生一句「去照X光」,患者一個口令一個動作,卻完全不知,也不曾被告知其作用為何?是否非照不可?
台灣南部曾有,位接受人工授精的不孕婦女,已經躺著要送入手術房了,醫護人員才告知她:「這次用的不是妳先生的精子。」
針對類似的痛苦經驗,當前各地的病人主權運動中,資訊權是普遍的重點;其中兩大訴求是:「消費者得到充分告知的醫療選擇」,及「提供證據證實(evidence based)有效或有用的醫療照護」。
英國一個婦女團體取得全民健保局的合作,對英格蘭地區的孕婦提供資訊,讓她們知道做超音波掃描的利弊、必要性,以及其他相關資訊,例如每兩百個經超音波檢查認為有問題而墮掉的胎兒,就有一個其實仍然是正常的。這些資訊使得八0%的就診婦女,在進行超音波檢查之前重新思考。雖然最後大部分仍然決定要做這項檢查,但婦女的醫療選擇權卻得到提升。
美國一些醫療人權團體最新的目標,則是要求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對於藥物以及一些新療法的審查過程能夠透明化,不要讓醫院、藥廠和政府為了某些利益糾葛,把患者的醫療選擇權給「協商」掉了。
全球民眾醫療主權意識的提升,除了拜健康財政等結構性因素之賜,資訊科技的普及,也讓過去被壟斷的醫療知識,有了新的出口。
從藥學字典到疾病自我診斷,各樣的套裝電腦軟體是近年歐美的熱門商品,德國的醫療光碟銷售年成長率達八0%。更重要的是網路社會的建立,已大幅改寫醫療教育與資訊傳播的方式和速度。
愈來愈多人可以透過網路,從全球各地的醫療資訊站找到豐富的資訊;而為數龐大的網上醫療討論群,更等於一個個的跨國界的病患組織。
「許多資訊我比醫生先知道,現在可以反過來與醫生討論。」這是台北一位陳姓洗腎患者,參加了網際網路討論群的心得。
事實上,許多美國的醫療院所和藥局,已經把網路諮詢視為必要的服務項目。
吃了太多藥
英國加州地區,有接近一半的民眾已經自家中與地區醫院連線,患者與醫療人員之間的溝通不再局限於等候一小時、診斷三分鐘的被動狀態,可以透過網路得到醫院專業的諮詢。
把醫療資訊當商品販賣,或患者自行尋求醫療資訊,在過去會被認定是干擾專業醫療;許多人也擔心患者知道太多只是徒增困擾,或讓他們到處亂投醫。但在今日無論民間或政府,對此都開始出現不一樣的看法。
美國前藥政處長伍德卡克(J. Woodcock)曾表示,現在不一定只有醫生才可以擁有判斷藥物適用與否的能力。
事實上一些研究也顯示,患者醫療資訊與知識愈充足,對促進健康與控制醫療預算都有幫助。
美國史丹福大學醫學中心,曾經做過一項長達四年的追蹤研究發現,那些在醫療過程中,得到詳盡資訊與充足諮詢的患者,比那些一知半解的患者,平均就醫次數減少了四0%。
相對地,民眾醫療知識的缺乏,將帶來最多的醫療資源浪費。
五0年代到七0年代,美國每年的健康支出,在二十年內增加了五百億,可是民眾的壽命卻只增加了四個月。研究發現,問題出在民眾的醫療知識並沒有以相對的幅度增加,結果只是被醫療市場牽著鼻子走,做了更多不必要的檢查、動了不必要的手術、吃了更多不必要的藥物,不僅醫療資源浪費,反倒生出了許多因為不當醫療帶來的「醫原病」。
台灣的狀況又是如何呢?
根據台大醫師王正一在一九九五年對國人用藥與就醫認知的調查,高達九七%的受訪者不知道自己生病時吃的是什麼藥;有將近三分之一的人,一個病同時看好幾個醫生,也因此,十個人當中就有兩個人重複用藥。
今年一月台大公衛系副教授季瑋珠一項醫藥分業的民意調查,同樣發現,受訪者中有八五%的人,對於看病所服用的藥物為何,並不知道(見表)。
在此同時,台灣健保費用則以每年二0%的比率上漲,已經達到一年兩千四百億台幣的支出。
無藥可醫的台灣
究竟原因是如本地醫界所言,民眾愛看病、濫吃藥、亂吃藥所造成,還是因為絕少手握過處方簽的台灣民眾,恰是英國醫學社會學學者左拉(M. Zola)所言,是一群「被除權的患者」--由醫界高高在上控制知識,民眾沒有對應能力,只能依賴、無力監督?
從近期的調查來看,台灣的民眾普遍認為關於自身醫療的資訊沒有得到滿足,但是卻有相當大的比例不敢(或不會)向醫師問問題。三月醫藥分業開辦之前,表示會向醫師索取處方簽的民眾也不到三成(見表)。這顯示,台灣民眾的醫療主權仍然相當低落。
當醫、藥雙方為了爭調劑權,而高喊「聖戰」的時候,大部分的台灣民眾卻還無法肯定他們是那張處方簽的主人。
去年台灣熱門的醫藥新聞之一,就是醫院內出現最強效的第三線抗生素也對付不了的病菌 「一個無藥可醫的台灣」已成為許多人的憂慮。
無藥可醫的台灣,正是一個缺乏監督的醫療體系,和無知無權的民眾共同濫用抗生素之下的結果。
這樣的結果有沒有可能改變?「從一張處方簽開始的教育,關係了台灣民眾能否重新成為醫療體系的主人,也關係了全民健保的成敗。」陽明大學黃文鴻副教授語重心長地表示。
無論如何,過去一段時間醫藥分業的爭議,的確為民眾帶來重新做主的機會。
服務於新聞界的沈小姐,近日來仔細看了關於醫藥分業的新聞,恍然大悟:「原來,每次去看病,醫生都開三日份的藥,是因為三天藥向健保局申報免審,醫院請領藥費最簡單。」她下定決心下次要問問醫生:「難道每個人每次生病都需要吃三天藥?」
「從正面來看,事件爭議愈大,問題就愈容易攤在陽光下,也增加民眾的思考與了解,這是主權意識開始的第一步。」一位長期關注醫療人權的醫師表示。
三月裡,各大醫院的藥局紛紛掛起了「諮詢」的牌子。等著領藥的患者,望著那些新設窗口,有的開始交頭接耳的討論,還有的好奇地走過去,看看裡頭執班的藥師。對台灣民眾而言,一個諮詢的窗口,象徵了醫病平權的第一步:患者就像消費者,需要有售後服務。
而在一場抗議運行中,只見主持人拿麥克風高喊:「讓民眾做主人!」信誓旦旦要給大眾更好的用藥資訊。
醫藥分業不是醫藥兩造的聖戰,全民健康有沒有機會,就看台灣民眾能否也意識到:我才是醫療體系真正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