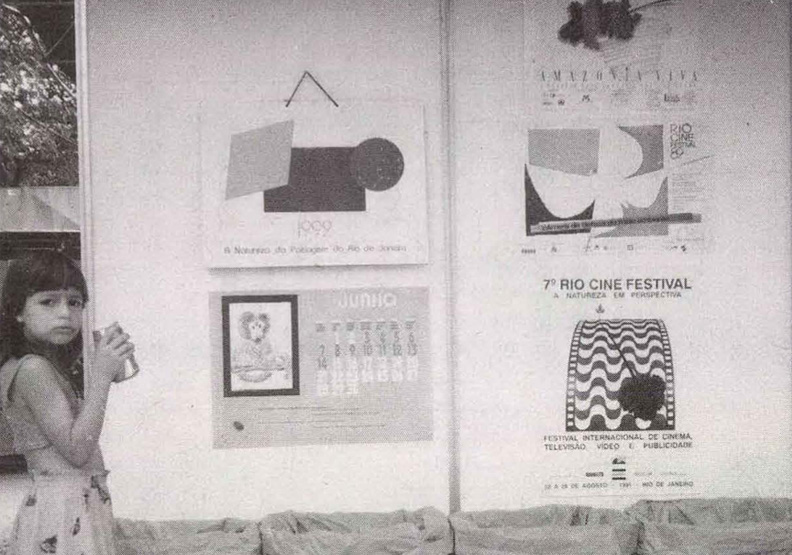里約會議前,中共試爆核彈,立法院通過核四預算;里約會議後,台灣要買一百架幻象式戰鬥磯,大陸也要買烏克蘭航空母艦。對於人類生存的唯一地球,中國人的世界性環保觀點究竟是什麼?
6月,南半球的秋末,氣溫怡人。里約最著名的卡巴卡巴那海灘上,每天都有成群的慢跑者,在享受和煦的海風。
當先進開發國家花數百萬美金,從挪威開出一艘名叫GAIA的船,載著500位來自五大洲的兒童,到巴西來慶祝地球高峰會與全球論壇時,口號聲在各個角落響起,全世界的媒體都引用著大會的口號──IN OUR HANDS;然而,世界到底在誰的手中?
窮國的反撲
媒體起初的焦點圍繞著南北對抗,窮國與富國清算舊帳,77個小矮人(G77,77個第三世界國家的聯盟)與七個巨人(G7,七個先進開發國家集團)玩角力。
美國總統布希到巴西時,與會各國反美情緒達到最高點。這一方面是由於美國自18世紀以來,嚴重剝削第三世界國家資源,特別是美國後院的拉丁美洲國家,所以自然成為眾矢之的;另一方面則由於美國以全世界二十五分之一的人口,消耗百分之二十五的能源、物資,同時製造百分之二十五的二氧化碳與氟氯碳化物,已經到了人神共憤的地步。
美國不願簽署全球變遷、物種多樣化公約是可以理解的,它只願放過與其自身利益無直接衝突的「森林原則」做為讓步底線。
反美的情緒不僅衝著美國官方,矛頭也指向民間團體。巴西本土知識分子組成的亞馬遜永續基金會董事長曼多瓦尼說:「你看那些美國的保護熱帶雨林組織,利用亞馬遜雨林的危機,每年在美國和全球各地募了數百萬美金的善款,但是除了製作精美而昂貴的紀念品、書籍、錄影帶,和招引來成千上萬的雨林觀光客之外,巴西人從來都沒有看到這些錢為熱帶雨林做任何事。」
「有些美國人還以為熱帶雨林是在佛羅里達州,還有人問亞馬遜是在美國的那一州。」在佛羅里達經營房地產致富的曼多瓦尼想用永續發展的原則,為祖國的熱帶雨林謀一條出路,既能利用雨林資源,免除原住民被迫失去生活依據,也可以防止雨林的生物遺傳基因流失,他們的這項計畫已受到聯合國的重視。
難以清除的政治污染
「我們總不能讓美國的大企業從實際破壞雨林的行為賺走資源,又再讓美國那些光說不練的環保團體,從口頭的保育,再賺走世界的同情與援助。第三世界國家應該站在同一條陣線上,否則地球的資源會立刻被帝國主義榨乾。」曼多瓦尼說。
從里約會議中各國政府與民間展示的環保資料,看到人類對未來的企圖與深受環境惡化威脅的危機意識;國際間對環保有共識,也有矛盾,但是那遙遠的鼓聲愈來愈清晰,特別是民主國家,民間團體的意識與行動均已覺醒。
台灣的官方、民間與學術界都有代表參加這次在里約舉行的、民間性質較高的全球論壇或國會地球高峰會,卻無法以任何正式的身分進入地球高峰會,甚至內政部營建署的官員要以冒充記者的手段混入會場,以取得會議資料,實在尷尬。
事實上就連主張西藏獨立的「達賴喇嘛辦公室」的人,都可以正式身分成為非政府組織的觀察員,在會場上暢言主張,台灣在那裡?
台灣的各路人馬出發前,曾開會討論「台灣觀點」與「台灣立場」,眾人尋尋覓覓之後,分別提出不同的觀點與立場;民間團體提出的是──是的,台灣關心(YES, TAIWAN CARE),以回應聯合國的「我們關心!」的口號;官方則以環保署、經濟部、農委會等單位製作了一套印刷精美的宣傳品,宣傳台灣的持續發展與環境保護的經驗。這兩分台灣內部的聲音,前者固然熱心有餘,誠意可感,但缺乏實質的力量;後者則失於華而不實,缺乏自省能力,而自省力是里約會議中最重要的精神。
對全球的環境與發展議題,台灣只有很淺的觀點和很虛浮的立場,其最大的問題是政治立場模糊。島內不統不獨的現勢,大家可以瞭解接受,但在國際上,「一個中國政策」讓台灣失去絕大多數的自主立場,即使台灣的環保團體在地球高峰會上也不得其門而入,必須經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認證,才能取得民間團體的觀察員身分,這是很難讓台灣人接受的待遇。
中國人沒有觀點?
在缺乏國際參與的情況下,台灣沒有充分地接觸與認識這個地球,怎麼能找到自己的「觀點」?頂多只能表示一下台灣願遵守國際環保規章,願意出錢援助未開發國家,或是談一談台灣的小學生如何響應資源回收。
台灣的立場只能在模糊的資訊中摸索,民間與官方都成了某種程度的狹視與重聽,這是未來台灣在發展上的最大瓶頸。坐井觀天不免夜郎自大,以台灣的經濟奇蹟為傲,是非常危險的發展模式,也正是里約會議對人類的最大警告。
在里約會議前,中共在羅布泊試爆了一顆相當於一百萬噸黃色炸藥的核彈;里約會議之後,台灣要買法國一百架幻象2000戰鬥機,中共也要買烏克蘭的航空母艦,這可能就是一種典型的中國人觀點。兩岸在里約會議所暢言的世界和平與永續發展不見了,只剩下鄧小平的講話與核四預算在立法院過關的回應。
當記者在里約訪問出席國會地球高峰會的立法院長劉松藩,是否打算在立法院推動一個特別的會期,以解決國內在環境與發展上所遇到的困境,劉松藩很坦白地說:「國內的事務非常多,立法院不可能有一個專門的環境與發展會期。」劉松藩的回答是中肯的,至少告訴了台灣的環保署和環保團體,他們的工作還不夠,未來還需要努力,換句話說,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台灣沒有觀點,台灣關心的是蒙特婁公約對台灣的外貿有什麼影響,布希會不會簽什麼公約,美國的態度如何,六年國建中富有的台灣會花多少銀子在蓋焚化爐上,全世界都在搶位子。
在里約,我們清楚地看到全世界都在那裡搶位子;日本民間與官方在里約的優秀表現,是為了進入聯合國安理會常務理事會鋪路,出錢出力在所不辭;即使不時互相指責對方,但對外時槍口一致。巴西即使背了1000多億美元的外債,仍然爭取第三世界的主導地位,主辦里約會議全民動員,毫不含糊。各國都在找自己在21世紀的位子,環境與發展這個全球議題自然是重點中的重點。
在里約,我們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世界在變,變中有善有惡。生活在這宇宙中藍色小泡泡的人類,終於有機會,和平地坐下來談關於他們與他們子孫的問題,這已經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一件工程──人類終於發覺他們命運是一體的。
(方儉為台灣地球日聯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