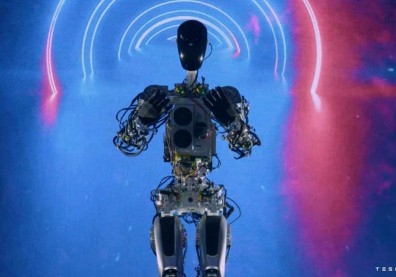七0年代,中國大陸的再度開放對共產制度所帶來的衝擊,可能不亞於一九四九年的關閉所帶來的震動。
一九八五年,我接受了廣東省政府之邀,對廣東實施改革後的發展進行研究報導。廣東官員明白,由一個外國學者作報導,將會較令人信服。而我也以自費訪問的形式,以保持立場的獨立,官員們也同意不審閱我的原稿。本書就是關於一個中國省分在一九七八至八八年這十年間,北京政府實施開明政策時的故事。
毛澤東逝世兩年後,也就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由鄧小平所制定的一項新的沿海戰略,旨在推動經濟發展,為一九七八至八八年這十年的改革揭開了序幕。以前,為了全國的平均分布資源和減少外強的覬覦,毛澤東挪走沿海地區的資源來建設內地貧窮的省分,結果常常是代價巨大,收效甚微。鄧小平上台後,改變毛澤東的作法,決定加速沿海地區的發展,試驗新的制度,以成為帶動中國其餘地區成長的火車頭。
在諸沿海城市中,廣東具有獨特的優勢。處在中國南方一角的廣東遠離北京,有二千四百公里的海岸線,用它來作試驗,如果發生政治、經濟混亂,不必怎麼擔心會對首都產生威脅。當時在中國重工業和國家收入中,廣東只占很小比重,因此進行試驗可能為國民帶來的風險也很小。同時,由於毗鄰香港,廣東是中國諸省中最容易瞭解世界發展、最有能力試驗外國技術和管理方法適用與否的省分。中國因此允許廣東帶頭試驗,即如口號所示:「先走一步」。
改革前哨
在蘇聯和東歐國家考慮改革的時候,廣東已開始先行動。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以外交辭令在中共十三大會議中說,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並不相同,他們均以各自的方式推行改革。但事實上,中國大陸早在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推行經濟改革的前幾年,便開始了經濟改革,並在這方面走得比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都要遠。而中國內部在推行改革方面,廣東又比任何其他省分有活力。如果廣東已比中國其他省分先走了一步,那麼廣東便可能比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先走了二步。
與其他省分相較,廣東人的出國機會較多,帶回的西方資訊也較多,最能感受到西方的國富兵強,因此廣東出了不少愛國志士,領導中國對抗西方的挑戰,鴉片戰爭便是在一批抗英志十的發動下在廣東打響的。維新運動的領導人康有為和梁啟超都是廣東人,領導辛亥革命的孫中山也是廣東人,他並且在廣州建立了國民政府。蔣介石曾任地處廣州市郊的黃埔軍校校長,並以該軍校畢業生為骨幹,建立了他的早期權力基礎。毛澤東的事業則始於廣州農民運動講習社,並在那兒構思出了他的農村革命方案。
但是一九四九年的共產黨革命的精神中心,既不在廣東也不在其他沿海地區,而是在中國內地。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對資本主義世界關上大門,取消一切對外聯繫的管道,共產黨領導人為廣東引人了與其他省分相同的政治結構、政策和運動。
六0年代和七0年代初期,中共不僅是在新的經濟政策上著重開發內地,而且在政治上也變得本土主義。直到一九七八年實施改革之後,廣東才重新擔負起幫助國家富強起來應付外國挑戰的歷史性角色,但O此時中國已是一個強權獨立國家,領導權牢牢地掌握在共產黨手中,廣東已不再需要扮演抵抗外強的角色,而是扮演率先改革社會主義制度的角色。
對外貿易好景不常
對外貿易一直是廣東經濟發展的核心。一九七八到八0年是廣東外貿的最佳時期,廣東省內外的商品出口額從一九七八年的二十八億元人民幣,上升到一九八0年的四十八億元。海外銷售額上升了約五0%,一九八0年達到了二十一億美元。
為了促進各地同香港和東南亞市場的直接貿易,廣東於一九七八年和七九年兩年,為外國船隻開放了近一百個港口和裝貨點。外國資金在一九七八年重新進入廣東,至一九八0年,外國投資額超過了二億美元,其中大部分是投資在鄉鎮小型工業。
但是,好景不常。一九八一至八四年期間,廣東出口的每年平均增長率不到一%。情況最不好的是一九八二年,當年廣東的海外銷售額下降了七%。一九八二至八四年,收購出口商品連續三年下降。當外貿幹部被問及這段時期外貿業績為何這麼差時,他們會列舉出香港市場疲弱和本省貿易基礎設施落後等原因。
能源短缺是外來投資者的一大頭痛問題,他們每個人都不得不為用電配額而談判。停電和電壓不足是常有的事情。在夏令季節,廣州一些工廠每週只開工三、四天。通訊也同樣極端落後。穗港之間的國際直撥電話直到一九八四年才通話使用;而大部分城市,如佛山、江門、石岐等,則遲至一九八六年才有直撥電話和電傳。由於在運輸、通訊和能源方面的落後,廣東的出口銷售因此付出了沈重的代價。
旅遊設施影響外資
另一影響投資的消極現象,是八0年代初期在旅遊設施上開支過大,而幾乎這些設施都有港澳資本參與,同期,在製造業方面的外來投資卻僅有微小的收益。一九八四年,廣東的合資工廠吸收了二千四百六十萬美元的外來資本;而另一方面,在建造旅遊賓館方面的外來投資,卻高達一千九百五十萬美元。賓館貶值很快,雖然在旺季可以賺取大量外幣,但就長期發展出口換匯而言,它們就毫無貢獻。
一九八五年這一年,被廣東外貿界譽為「飛黃騰達」的一年。的確,這四年期間,廣東的進出口表現非常出色。出口從一九八四年的二十五億美元,上升到一九八七年的七十億美元,漲幅達一八0%。與任何東亞新興工業經濟區創下的紀錄相比,廣東的成長率也是毫不遜色的。
簡言之,一九八五年以後,廣東外貿已成為廣東經濟戰略中的主流。全省各地的加工出口區興旺發達。一九八八年初,光是佛山縣市一處,就有六個這樣的加工區在運作,為外國投資者提供各種「優惠條件和政策」。
這些加工區以及許多出口導向型的城鎮已成為某些特定工業的生產中心,吸引了大批資金、勞動力和管理人員。東莞市的太平鎮就是玩具工業的中心;增城縣則以廣東省的「牛仔褲之都」而著稱,整個增城縣城就是個巨大的牛仔褲銷售市場,數以百計的商店、攤位、街頭小販在出售堆積如山的牛仔褲。
以香港為圓心,半徑二百四十公里的地區內形成了一個由出口加工衛星城組成的帶狀區,為香港及其出口市場提供產品,且在技術密集的中心裡,把技術和原料結合起來。廣東省則通過了幾項地方法規,鼓勵香港商人把加工工業轉移到廣東來,反應頗為熱烈。這些城鎮轉為外向型經濟後隨之而來的繁榮,也許是一九八五至八七年進出口熱潮中所取得的最受人注目的成就。
粵港漸成單一經濟區
粵港兩地經濟區的相互交織始於七0年代後期,特別是一九八四年達成了香港回歸中國的協議之後,兩地的交往更頻繁。過境手續簡化了,一九八八年,每天從香港進入廣東的商用車輛多達一萬部,每逢週末還有數萬名香港人到廣東旅遊。火車、飛機、渡船,尤其是貨車,將香港和廣東各城鎮聯繫起來。深圳和鄰近的廣東各縣,實際上已成了香港新的近郊和遠郊,許多香港商號在這些地方設廠,以利用當地的廉價土地和勞動力。
儘管粵港有形成單一經濟區的趨勢,但是由於存在著兩種制度、兩種幣制、兩種生活水平,以及兩個各自為政的政府,所以粵港地區的協調工作並不易進行。
在美國,哥倫比亞特區是政治首腦,而紐約則是商業首府;相對地,廣州依然是粵港地區的政治中心,在消息傳遞、金融、國際貿易和商業等方面發揮作用。而香港則成為高科技和工業工程中心;香港新辦的大學「香港理工學院」,就是一所培訓廣東人員的重要中心。
未蒙上九七大限陰影
粵港經濟區結構改變的速度,可謂驚人。香港過去在低工資勞力密集型工業上,幾乎徘徊了三十年,而深圳工資提高之快,不出十年就度過了那個階段。八0年代期間,香港公司以驚人的速度將製造業搬到邊界那邊去,卻往往對本港工人的命運缺乏足夠的考慮。
數起訴訟案顯示,許多香港工人早晨去上班,才突然發現工廠空空如也,機器已在一夜之間搬到邊界對面去了。甚至連珠江三角洲各縣在八0年代後期也感受到了壓力,因為工人工資提高了,交通運輸系統也改善了,不得不引進新的生產設備來提高勞動生產率。雖然香港有九七大限的陰影,新出現的粵港地區仍是八0年代末期,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地區之一。
在技術水平、生產效率和教育程度等方面,廣東在八0年代後期仍然大幅落後於幾個新興工業經濟區,但其增長速度卻比台灣和南韓高事發展期的增長速度為快。香港是世界一流的訊息、金融和運輸中心,廣東則是向香港提供農村產品和廉價勞動力的內陸腹地,兩地自然地結合起來,在國際市場上角逐競爭。正如一位香港華人商界領袖所說:「隨著香港和廣東的攜手合作,我們準備與任何一個新興工業化經濟區較量一番。」
廣東的發展也影響中國大陸其他省分。位於西江並與廣東毗鄰的廣西省梧州市,已被非正式地稱作「廣西的深圳」。梧州從廣東吸收了新觀念和新產品,梧州周圍地區又從與廣東貿易中受益,因而比廣西其他地區更繁榮。閩南和湘南,都由於它們與廣東的貿易而興旺起來。
換取別省資源
雖然這種貿易對毗鄰廣東的地區最為直接,但也逐漸遍及全國其他各地。為了說服廣西提供電力,廣東資助廣西興建一座大型水力發電站;而為了從其他各地取得所需資源,廣東正在與別省談判,以簽訂投資開發項目的合同,來換取別省的資源。福建官員更普公開說過,在運用特殊政策方面,福建做得沒有廣東那麼好,所以決心以廣東為榜樣。
蘇聯人也在對他們的經濟制度進行改革,不過在他們的基本決策中,廣東的成功不大可能產生重要的作用,但是,來自蘇聯和東歐的官員已對中國的經濟改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自一九七八年以後,每年都有好幾個來自東歐和蘇聯的重要代表團到廣東訪問,考察廣東的改革進程,代表團成員包括資深的計劃官員和學術機構的領導成員。訪問者對廣東發展的規模和速度印象深刻,並且認為廣東的某些改革,例如價格改革,已經遠較全國其他地區推行得深入。蘇聯對深圳特別感興趣,一九八八年,也考慮在海參威建立一個經濟特區。
愛沙尼亞也在考慮和芬蘭建立某種類似廣東和香港那樣的聯繫,不過規模要小些;同時蘇聯境內一些接近奧地利和其他西歐地區的地方也受到了鼓舞,考慮要和外界建立各種的地區性聯繫。最起碼,在蘇聯的內部辯論中,關於廣東和中國其他地方改革成功的報導,已被用來支持和幫助制定他們自己的改革方針。一個社會主義大省能夠達到如此迅速的增長,此事本身便是一個極大的鼓舞力量。
改變面貌開步走
在共產黨統治的前兩個十年中,廣東領導人忙著擴大政治權力。無暇處理經濟問題;在第三個十年中,內部政治鬥爭又使他們落後得更遠;但在第四個十年時,一批新的領導人在來自北京的鼓勵和支持下,承認了過去政策失誤的嚴重性,並且走上一條嶄新的道路,開始改變廣東的面貌。
八0年代可視為社會主義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這時許多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已承認,社會主義制度並沒有帶來經濟進步。正值有些國家開始向資本主義世界吸取經驗,克服經濟停滯的困境時,廣東省的領導人已充分利用了這個難得的時機,並先走了一步。
(徐澤榮譯)
(李怡慧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