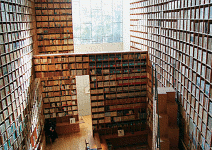兩道偌大的牆面瀑布,從兩旁高高的屋頂宣洩而下,形成川流不息的巨大水牆,畫面壯觀,令人震懾。一個個旅人從水牆內的長長迴廊穿過,若隱若現,顯得神祕、渺小。
水流匯集成偌大的水池,水面上映照著天空的光線與色彩,光影搭配著嘩嘩嘩的水流聲……,「實在是太震撼了」「啊,太壯觀,太厲害了」「真是敗給他」,置身在這樣的建築環境內,旅客讚歎聲不絕於耳,照相機鎂光燈更是閃個不停。
「你看,安藤的作品一定有水聲、光影、充滿聽覺與視覺的饗宴,」已經被眼前畫面震懾到很難挪動腳步的訪客,耳邊突然響起解說員的說明。
這是2月底、3月初,一百六十四位參加日本建築師安藤忠雄建築之旅的台灣旅客,所共同經歷的震撼。地點就在大阪市郊的狹山池博物館,已有一千四百年歷史的日本最古老水利設施。
四天的建築之旅中,不管是大建築,還是小基地建築,安藤的作品經常讓台灣旅客驚豔。
走進地底下的地中美術館,那間放置四幅莫內真跡的展覽室,畫作竟成了配角
知名的日本思想家、作家司馬遼太郎紀念館,坐落在大阪市郊傳統住宅社區內。旅客彎過幾個社區小路,走進一個住家小花園後,一進紀念館,就看到從地底延伸到四層樓高的屋頂、四面皆是書本環繞的巨大書牆。
當訪客抬起頭,仰望眼前這一幕壯觀的書牆時,解說員說著:「這樣的設計,就是要讓旅客被司馬遼太郎的藏書所包圍,要製造那種氣氛。」
距離大阪三個半小時車程、再搭船才能到的香川縣小島——直島,十八年來安藤已經蓋了兩座美術館。位於地底下的地中美術館,一走進去好似走進一座古代城堡。那間放置四幅莫內真跡畫作的展覽室,畫作卻變成了配角,屋頂透進來的光線角度、腳底下一小塊一小塊拼貼的大理石,才是大家研究的主題。
這是座美術館沒有錯,但更重要的是,整棟建築也是一座大型現代藝術品。
旅客在裡面穿過來、繞過去,欣賞建築內光影的變化,「安藤的光線運用已經出神入化!」「這個在台灣一定做不起來,怎麼會接受把美術館蓋在地底下?」「全部都用清水模,台灣的業主一定覺得不能接受,」旅客們七嘴八舌地討論著。
安藤建築之旅,就這樣在旅客不斷的讚歎聲中,從這一站走到下一站。
對西方而言,安藤是東方極簡禪味。對東方而言,安藤是西方光影
台灣人出國其實司空見慣,但是像這樣由交大建築研究所主辦的建築美學之旅,卻十分罕見。2月初報名新聞一曝光,徵詢電話就不斷,開放網路報名當天,不到四分鐘就已額滿。
儘管七成的團員來自建築、室內設計等相關科系的教授、學生、以及業者,但是也有內科醫生、科技新貴、美食家、一般的白領上班族混在其中。
不少報名參加這一次旅程的台灣旅客,參與動機只是期待一趟單純的美學之旅。「就是放自己幾天假,來放鬆,欣賞一下美的東西,」一位白領上班族說。
一位科技新貴也說,這十幾年來他每天隨身都帶著護照、電腦,隨時準備接獲指示,出國出差。一年前,他從原來的公司離開後,換了一個比較輕鬆的工作,「這是我第一次沒有帶電腦,也沒帶手機出國,我本來就喜歡安藤,喜歡看建築,」他興奮得好似這趟旅程完成他多年的心願。
安藤的魅力來自於他是目前日本在國際上最知名的建築師之一,得過無數個國內外建築大獎。他用最原始的混凝土為材料的清水模工法,塑造出最豐富的建築要素——牆面,可以做到光滑細緻,不會凹凸不平,也是全世界公認最好的。
不少評論者認為,「對西方而言,安藤是絕對的東方,因為他的風格極簡,又有禪味。但是對東方而言,安藤又是絕對的西方, 因為他重視光、影、水、造型立體的變化。」
沒上過正統建築課程的高中畢業生,自學成師,還應聘到東京大學任教
有趣的是,今年六十五歲的安藤,一生也充滿傳奇。
只有高中學歷,十八歲那一年,安藤決定把大阪、京都一帶的日本寺廟古蹟走訪一次。二十四歲,他踏上歐洲的土地,開始多年的歐洲建築之旅,臨摹一棟棟走過的建築。就這樣,沒有上過正統建築課程的高中畢業生,自學成師,中年後還應聘到日本學術殿堂的東京大學建築系任教。
高中畢業後,安藤還一度當過拳擊手謀生,也養成他好鬥、堅持、不輕易放棄的性格。
由於安藤的人生十分傳奇,使得這團建築之旅,除了觀摩建築、欣賞設計美學外,他的人生也成為旅行中重要的學習元素。
宜蘭建築師黃聲遠,事務所半數、共十四個員工參加這次參訪團。讓黃聲遠印象深刻的是,「怎麼也有這麼多非建築相關領域的台灣人,像內科醫生、高科技研發人員,也參加這個團?」
黃聲遠的體認是,愈來愈多台灣人把建築當成有助於自己哲學思考與美學的窗口。瞭解到台灣社會逐漸成熟,有這麼多人對建築有興趣,「這是一種鼓舞,也是一種提醒。」
安藤建築蓋到哪裡,樹就種到哪裡,而且時常發動社區裡的小孩子種樹
才剛從六年教育部次長職務卸任的范巽綠,之前她看過不少安藤的書,但是這一趟她有一個很大的發現,安藤建築蓋到哪裡,樹就種到哪裡,而且時常發動社區裡的小孩子種樹,「這種對自然環境的重視,是台灣建築師中相當少見的,」她說。
另一個范巽綠的觀察是,安藤的案子常常做很久,一做十、二十年。例如安藤在直島的建築規劃,已經進行了十八年,一步一步慢慢做,而不會急就章,這也是跟台灣很不同的地方。
而當台灣旅客分成小組聚在一起談天說地時,一個共同的感歎是,大家都感受到安藤在日本社會受到極大的尊重,「一個社會對專業的尊重與信任,才能孕育出大師。」
大家感歎,台灣已經出不了大師,誰也不服誰,這是台灣社會很大的悲哀。
一趟單純用美學角度出發的旅程,過程中可以迸發出這麼多想法,真是令人意外。
今年四分鐘就額滿,明年有興趣參加的人,動作要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