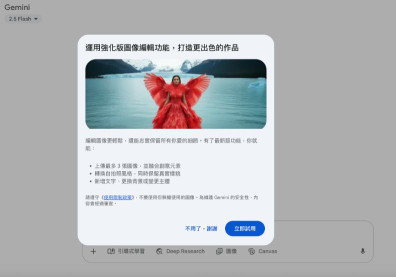1夢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秘書長黃旭田
改革急先鋒
他是律師,但卻將焦點擺在司法改革,擺在改善律師制度上。
律師的夢想可以有多大呢?讓黃旭田的改革故事告訴你。
年輕的你,想要幹一個打起政治官司轟轟烈烈、為人尊敬的偉大律師?
像美國律師奈德(Ralph Nader)─寫出《任何速度都不安全》的膾炙人口調查報導,當年讓跨國巨人福特汽車迫於消費者壓力服輸,召回數十萬輛會燒死人的Pinto轎車的那位了不起的小市民律師,那位號稱「美國消費者保護運動之父」的在野法曹?
像很多第三世界國家總統,在野時都是律師,以被壓迫者的代言人自居。
在台灣,機會已經不多了。從1979年「美麗島事件」、1988年「520農民遊行事件」後,就只剩下今年總統大選的驗票案了。可惜,驗票案涉及數百位、藍綠不同政治立場的律師團,讓人眼花撩亂,民眾實在記不得。
聰明的你,還有一條路,默默奉獻非營利團體,可以讓同業更尊敬你。
這裡介紹的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秘書長黃旭田律師就是一個實例。
監督法院,評比法官
41歲的黃旭田律師是少數非常熱心於司法公共事務的青壯派律師。
不滿於政府長期放任律師業停滯在「解嚴前的不合理結構」,黃旭田以全聯會秘書長身分,刻意要改革幾項沈痾。「和任何一個先進國家比,台灣的律師比例都是偏低的,即使是日本,也要大幅提高法曹比例,台灣呢?」黃旭田理直氣壯地問。
1995年,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成立,挑戰法界權威,97、98年連續兩年而且延續到2002年,針對法院法官的種種行為進行「觀察」。名為觀察,其實是監督,更重要的是,還把評分不到60分,排名最後六名的法官名單,公佈在媒體,引起一場「誹謗官司」。當時,元貞聯合法律事務所的合夥律師黃旭田就是司改會核心要角之一。
黃旭田和他的志同道合的義工律師們,針對幾項不合理的結構性問題:
1.觀察法官之法庭程序,檢討訴訟當事人及關係人在法庭上之地位及權利。
2.觀察檢察官執行公訴人職務之實際情形,檢討訴訟理念之落實與否。
3.觀察律師之法庭活動,檢討當事人權益有無受到保障。
長期參與司法改革
司改會咄咄逼人要求改革,外人看來,彷彿是繼1988年高新武檢察官的「吳蘇案」之後另一波「司法紅衛兵」;但歸根究底,不得不承認,他們是站在進步者的一方,要逼迫備受爭議已久、納稅人十分不滿的法官自我改革。(雖然近二年,法務部長陳定南曾公開批評,司改會也有路線之爭的問題,彷彿焦點已經轉移到了廢除死刑,他個人不苟同的方向。)
其實早在還是台大法律系學生時代,黃旭田就已經是校園社團的主角之一。在那個還是戒嚴的年代,他是熱衷校園活動的要角,奠下他日後以律師身分從事公共事務的基礎。
他喜歡參與改革。完成政大法律碩士學位後,有很長的一段期間,他參與「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的會務。他篤信台灣的司法改革具有高度之重要性及迫切。「台商不斷到大陸生根發展,台灣憑什麼要求台商根留台灣?除了教育、醫療,就是司法贏過大陸了。」黃旭田認為。
不斷挑戰律師制度
而且他還不怕得罪同業,擔任台北律師公會秘書長期間,他拿出念學位的研究精神,拼命用功研究先進國家的司法改革進程,尤其是日本,提供給台灣法曹同業參考。
台灣律師界最大的問題在故步自封。1989年以前,「軍系律師」(退伍軍法官轉任檢覈通過者)和「高考律師」(包含師專、非法律科系一般大專生)針鋒相對,在「高考律師」還是個位數字時代,還算相安無事,直到1989年「高考律師」及格人數首度破了百人,而且是將近三百人的「288事件」(指當年錄取了288位律師),律師業的改革呼聲問題全面浮現出來。
考試院雖以「288革命」鬆動整個律師的市場,但是不能管到律師業的執業環境。「律師執業需加入各地律師公會」「律師公會全聯會的會員代表制度」是兩個不合理的制度,也是黃旭田要求改革的對象。
黃旭田專門研究這些難纏的法令規章、制度設計,希望發掘一個切入點,點出台灣司法改革的希望。畢竟,他相信,司法存在的終極目的是協助全體人民實踐人的尊嚴與價值、維護社會秩序、增進全民福祉,律師公會也不應只是法曹菁英的貴族團體。
逐步推動法治教育
除了司法改革、律師制度改革,黃旭田還投身法律人很少涉入的「法治教育」改革,因為他發覺一般民眾並不瞭解司改會的努力,台灣雖自稱「民主奇蹟」「法治社會」,但一般民眾對「法治」的概念卻非常的模糊,要改變這種情形,必須對全民的「法治教育」著手,因此在批判政府的法治教育步調雜亂、教材不當、師資不足且不適任後,黃旭田以台北律師公會代表的身分結合了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及民間司改會組成了「法治教育向下紮根」特別委員會,引進了美國公民教育中心的一系列教材,正自小學、國中、高中逐步推動「法治教育」的改造。
律師公會的制度問題
在東台灣的花蓮、台東,因為法律案源較少,除非有地緣關係,剛考上牌照的年輕律師不會去加入台東或花蓮律師公會(通常是留在北、中、高三大城市),而在地律師們為避免外地的律師來來去去,於是把加入律師公會的門檻提高為5萬元,幾乎是一般公會的兩倍,因此外地律師不會優先選擇加入花蓮、台東的律師公會。而且一加入後,即使案子辦完,律師未必退出公會,因為下次再加入公會又要花5萬元,於是就會保持公會的會籍,但卻不常參加公會的活動,結果公會雖然有好幾十個會員,但能參與公會會務的律師,只有在地的十數人。
於是長期以來,像花蓮、台東律師公會差不多都是同一群律師在代表公會,像這樣的運作模式,在地方公會就發生人數「虛胖」而無法運作。
另外一方面,在律師全聯會的運作上,由於是以各公會選出的代表來組成,結果在台北地區執業的律師占全國律師人數一半以上,但是在全聯會的會員代表人數只占十分之一強,而且全國律師也沒有機會直接參與全聯會的會務,因此相較於美國的ABA(American Bar Association,美國律師協會)日本的日弁連,台灣的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的積弱不振,制度設計實為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