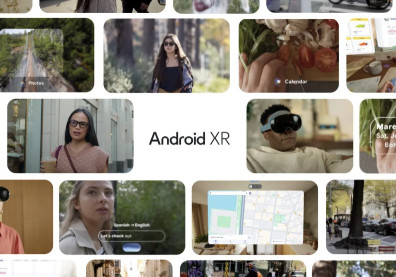「真的大災難可能橫阻在末來,但是拉扯著我們通向災難的下滑坡道,一年比一年陡。我們正在和時間賽跑,遲早斜坡的斜度與我們自己的動量會順著弧線將我們自己推到不歸路上。但是當斜坡更斜,災難拉得更緊繃時,我們辨識危機「拉力」的能力也會更強。在我們更接近歷史邊緣時,我們洞察自己處境真相的勝算會有戲劇性的改善。」
--美國副總統高爾,「瀕危的地球」
「在我心裡,人是第一位,族群從不是困擾。」客家籍、做過一些原住民調查,最近又為高雄柴山自然公園奔走的吳錦發說。
「在哪裡生活,就愛哪裡,就是這麼簡單。」前年從英國回台,目前致力於台中縣清水造鎮活動的饒大經也說:「談意識形態不太談得出正面的東西,不如從改善周遭環境、人與人的關係做起。」
困在族群問題的悶局中,有些人開始感到疲憊,打算換個姿勢。
土地洗禮運動熱絡
去年成立的中華民國義工總會曾作調查,發現全台灣各地有將近九十萬個人,想要擔任義工。今年,他們和外商惠普公司合作,準備以電腦網絡把各界義工供求做連線「撮合」。
街頭抗爭的年代褪色,社區運動成為台灣社會強力跳動的脈搏,「已經遍地開花。」一位社區工作者觀察,民國八十年代以後燃起的返鄉風潮,已愈演愈烈,它具有的尋根意涵,勝過在都市搞運動。
在嘉義縣朴子市高中教國文的蔡哲仁,幾年前曾是台北街頭反核示威的常客,後來嘉義笨港媽祖文教基金會成立後,也曾參與開疆闢土。「在哪裡做,總比不上自己家裡踏實、有意義。」受過社運洗禮,蔡哲仁認為現在是將社運在地化的時候。去年,他成立了朴仔腳文化工作陣,以社區刊物出發,針砭地方時事,希望凝聚地方意識,形成一股力量,制衡黑金勢力。
而留在都市的,也遭逢都市重建的浪頭,從台北都會推向南台灣的高雄。經台北市都市發展局有心鼓吹,已有二十個案子在各行政區展開。高雄最近也在鹽埕區,祭出第一個社區改造活動。
於是,以文學、鄉土教材、小型講座、動態活動為媒介,結合了媒體、原鄉民眾、田野工作者、各地中小學老師、文化工作者的新網絡「正在形成另一種意見系統。」原住民刊物「山海文化」總編輯孫大川觀察。他們不但企圖把在地人目光拉來關注公共領域,重新扭轉價值觀,也把地方的人力挖出來,跟外地的鄉親連線,把網絡擴大。
連企業界做公益活動也改絃易轍,加入這股浪潮。光寶文教基金會是企業界少數直接介入社區營造的例子,早先曾贊助台東布農族活動,之後又在一些鄉鎮推展社區文教工作、小學戲劇教學實驗等活動。
企業的足跡,也擴及較激烈的行動。例如,曾參與美濃反水庫運動的台灣時報主筆吳錦發還透露,去年抗爭人士開了一百五十輛車到美濃遊行,當中,美濃在高雄的企業界出錢資助很大。
「新的台灣經驗,是人透過親切的土地洗禮,對社會發生感情。」高雄信義醫院副院長、也是高雄保護高屏溪綠色聯盟會長曾貴海說。
衝突,非關族群本身
美國一度領導黑人建國運動的麥爾坎X,在把黑、白問題拉到高度緊繃時,有過辨識到自己帶來的危機的經驗,因而徹悟!「心靈之路將是唯一抵禦種族偏見之路……未經證明有罪的人,不再被定罪。」
當糾葛了文化、民族、國家認同的族群問題,逐漸壓迫住台灣所有人的呼吸,一些人開始奮力尋求解困之道。而這個覺醒的過程,更因為幾次選舉、中共武力威脅寺外在因素,更形具體、凝固。最大不同是,「人」和「家園」的焦點被突出了,「族群」的標籤被沖散了。
「尋求文化的認同變成主流,而與國家認同分家。」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廖炳惠分析:「族群問題是認同的衝突,不是族群本身的衝突。」
問題是複雜的,解決的方法,也不是簡化的概念,反而是困難的抉擇。「需要深而盤根錯節的思考、釐清。」廖炳惠認為。
當以人為終極關懷,視界便有所不同。
身為原住民,孫大川深感以往異族群彼此相遇,只是劇場式的相遇,而沒有真正的學習。要化解這種見面不相識的距離,只有靠每個人不停地修正。
蔡哲仁以前演講都用台語,現在卻覺得語言只是一種溝通工具,「不應賦予它太多族群傷害的色彩。」雖然他還是教小孩用台語,但在公開場合,他會看情況選擇最容易溝通的語言。
念花蓮東華大學族群研究所一年級的李紀平,大學時曾經是陳水扁競選台北市長時的義工,他一直認為族群不是問題,民主才是他的信仰。直到有一天,他回東華的寢室時,赫然發現門口被同學張貼了兩面國旗,和蔣公遺像,「他們以為外省人就是那樣的。」父親是外省人的李紀平說:「我才發覺自己丟得太快的東西,同學都還留著。」逐漸地,他改變以往採取強烈立場的做法,變得冷靜。今年總統選舉,當台北同學邀他替彭明敏助陣時,他還因為拒絕而被同學責罵「背叛」。
「人應該活得辯證一點。」五十六年次、剪了個平頭的李紀平說,以往他對上街頭抗議的老兵感到不屑,在花蓮與榮民接觸後,他才知道他們的真正想法,而有了同情。
向異文化學習
更大向度的異文化學習,應是外省新住民向已經在台灣三、四百年的閩南、客家人學習,而所有新移民更必須去向原住民學習。「即使原住民目前折敗在政治、經濟上。」臺原藝術文化基金會董事長林經甫說。
林經甫曾在大年初一到卑南族參加豐年祭,看部落作靈事。一早,由部落長者唸出對祖先懷念、山川、天地的詩歌,藉此教導、安慰、教訓未亡人。中午時分,由青年團以歌舞帶出「過去一年已逝,未來應該怎麼作」。黃昏時,青年團又回到聚會所歌舞,表達族群團結。「這種文化凝聚力,在漢族已被經濟、政治消眠了。」
文化認同的箭頭先指向歷史記憶。二十世紀末的台灣各族群,正有志一同地各自尋找過去的集體記憶;回家訪問自己奶奶唱的歌、生命史;尋找街廓老照片、舊古董;保護舊建築、民俗;重現民間戲曲、舞蹈……。「台灣有自己的東西,找到什麼是我們自己的根,是建立將來價值體系的源頭。」林經甫說,學會從尊重自己文化中,取得自信,在受到異文化衝擊時,才有助於吸收多元文化。
值得辯論的是,回頭凝視的視線,要到多遠?
「傳統有很多渣質,必須批判、揚棄,才能再生。」蔡哲仁說:「回去的目的不是複製,不是照單全收,而是好與壞、深不深厚的選擇。」
如果只是復甦、懷舊,無法有立體意義出來。有些人選擇以再創造的過程,注人現代的元素。
例如,臺原基金會介入台北迪化街社區活動,企圖將城隍廟民俗活動作一場宗教信仰現代化的改造運動。「我們在思索,歌仔戲、布袋戲、電子花車之後,會是什麼?」臺原民眾戲劇召集人鍾喬說。
讓文化有經濟方面的轉化,則創意更深。
在高雄經營「小王子」麵包的翁榮輝,將自己的舊家內部改建成現代化的麵包西餐廳,只為了向曾經有過繁華的鹽埕區老鄰居證明,舊社區也可以有第二春。
蘭嶼蘭恩基金會的林茂安,打算用台灣的現代工具,如開設電腦班、手工藝班、民宿經營班,行銷蘭嶼的文化傳統資產,培養蘭嶼人自立生活的能力。
創造性的設計,不只可以讓文化與經濟面結合,政治面也有機會。
孫大川舉例,原住民部落選舉,常常是未選先分裂,末蒙民主之利,便先受其害。
如果能恢復政治參與管道為兩線並行,除了一般選舉機制之外,另強化因祭典需要的司祭和頭目系統,既能保持某種現代機能,又能恢復部落生機。如此權力不會集中,有助多元的建構。
留線索,向上攀
而對沒有文字的原住民,也可建構一套書寫策略。例如,可用羅馬拼音或中文書寫,加上原住民象徵、語彙,形成特殊文體。
「政治性的文化運動,或文化性的政治運動,會是台灣未來幾年的重點。」林經甫因此預測。
還原也好、創新也罷,許多人同意,前進之前先後退,不斷返本開新地循環。不論還原或創新,必須有線索留著,就如天上有一顆星辰在那裡,可以給人辨識。「而四十歲這一代的責任,就是留線索。」孫大川說。
相較於過去綁白布條的街頭鬥士,這些人的面目,「恐怕對政府是更大的威脅。」朴仔腳的蔡哲仁身材不高、自信卻不小。
批判精神仍是他們主要的標誌,但卻是軟姿態的出現。「對抗公權力,我們儘可能妥善拿捏,不要壯志未酬身先死。」一位地方運動人士說:「有勝算才打,或者雖沒勝算,但引發的社會效果大,我們也會投入。」
但專業與數據是他們最大的武器。吳錦發自己去日本收集水庫相關資料,回到台灣以充分的數據告訴官員,台灣可以不再蓋水庫,終於阻止美濃一場可能的浩劫。
「有專業,才有可能不會被地方派系把持。」光寶基金會顧問陳輝明觀察。
許多地方社區運動的領導人都表示,他們學到最寶貴的資產,是民主方式的洗禮。醫師曾貴海說,綠色聯盟運作的方向,都經由共事者提出、反覆辯證,再去行動。藉由這種過程,成員學會彼此尊重,互相學習對方所長。
綜合各地社運團體經驗,只要自覺性夠強的團體,不管從什麼角度切入,到最後,多會觸碰整個在地人心污染的真實面貌:派系、黑道、官僚體系等文化的惡質面。一位社區運動者就聞到,解嚴前就成立新港文教基金會的陳錦煌,最近有「隱忍、伺機而動,想要轉型的味道」。
「最後決戰點,必須跟當地惡勢力對抗。」蔡哲仁觀察。但他也說,要改進不是靠那些人頓悟,而是慢慢去變化。
這些人相信,儘管現在還只是在找縫生根,但藉社會運動實際操作的過程,人的品質改變了,會形成善的循環。「一個影響一個,這種人愈來愈多的話,是一種隱微卻深沈的改造。」蔡哲仁說,如此慢慢擴展出去,再去逼體制改變。
「現在大家已經在谷底,我們的責任就是給一些東西,讓大家踩著往上爬。」孫大川如此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