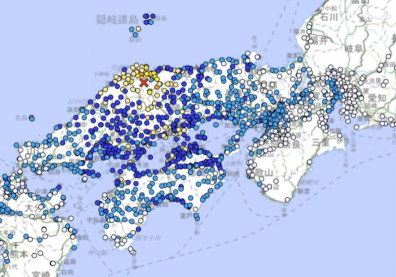他有個典型的以色列名字--以撒,與以色列人排名第二位的老祖宗同名。古史上的以撒,性格軟弱,曾為了保命,宣稱美麗的太太是自己的妹妹;面對與外族的水權相爭,則一再的退讓。
以撒拉賓從來不是這樣。
二次大戰時,他是戴陽將軍手下的精銳突擊隊,深入敘利亞境內破壞敵人的通訊設施;戰後他直驅英軍陣營內,救出兩百名被拘留的以色列難民;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占領耶路撒冷時,他率兵進行巷戰;一九七六年的六日戰爭,以色列對抗四個阿拉伯國家時,他是前線最兇悍的指揮官……。以色列前總理拉賓長達五十幾年的軍旅、政治生涯,就像他的國家,面對敵人,從不退讓。
從執槍之手到和平之握
然而,或許連這位一輩子硬頸前衝的浴血將軍自己也沒有想到,今年十一月全世界以如下的形容詞緬懷他:一位因退讓而偉大的人。
從不退讓的將軍到退讓的偉人……或許一個小動作就足以反映:
十一月四日夜晚,就在三顆子彈奪走他性命的幾分鐘前,以撒拉賓做了一件他從未做過的事:對著台拉維夫列王廣場上,數萬名以色列人,在「和平之歌」的歌聲中,抬起手臂,輕輕環繞與他在政壇瑜亮情結長達二十幾年的外交部長裴瑞斯。
對於曾經連裴瑞斯這個名字都不想提及的拉賓而言,這個小動作絕非易事。不過,更艱難的,他其實已經做過了。
兩年前的秋天,拉賓面對著一位真正的夙敵--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領袖阿拉法特,遲疑了一下,旋即伸出同樣的右手,首開以、巴和平之握。
從執槍之手到和平之握,拉賓伸出了一臂之遙,其跨越的歷史距離卻不是現實的尺度所能丈量。
透過拉賓的手,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簽下和平協定。去年的五月十七日,以色列將加薩走廊與約旦河西岸耶利哥城的民政權,交由巴勒斯坦人,結束了長達,一十七年的屯墾統治。根據拉賓的時間表,明年以色列的勢力將完全退出約旦河西岸,回到當初以色列建國的疆界。
在以色列,退,所需要的勇氣,應該更甚於前進。
拉賓在與巴勒斯坦和談中所放棄的,都是猶太復國主義先驅所堅持恢復的猶太人土地的核心;一九三七年時,當時的復國運動領袖本古里昂就曾說過:「任何一個猶太人民,都沒有權利放棄任何一部分的猶太土地。」那是猶太千年歷史中,上帝的應許之地。
這是為什麼在以、巴和平協定簽訂那天,以色列國會山莊的坡地上聚集了十幾萬人,他們對著拉賓怒吼指控:「猶太人的叛徒!」
面對這樣的指控,拉賓的回答是:「我是個軍人,但相信我,幾萬示威者的叫喊,還不如一個母親為陣亡兒子哭泣的眼淚,所給我的震撼。……我要尋找和平的出路。」
在拉賓所形容的「一面夢想一面作戰」的以色列,身為軍人對和平的企求,的確帶有無比的分量和內省。
自從以色列在一九四七年建國以來,「為生存而戰」已經消耗了這猶太夢想之國將近五十年的精力與長遠的夢想。就像以色列宗教家約瑟夫伯格所講過的笑話,一名以色列人問另一人:「你是樂觀主義者,還是悲觀主義者?」那人回答:「當然是樂觀主義耆,我深信今天比明天更好。」
以色列人當中,並不是只有拉賓才知道,若不與阿拉伯國家謀和,以色列人可能注定永遠成為「今天的樂觀主義者」。但他卻是採取行動尋找出路的人。
「是敵人才需要求和」
拉賓有行動的力量,因為他沒有讓歷史的包袱阻礙他正視現實。
幾乎全球的媒體在為拉賓蓋棺論定時,都提到他的和平行動是絕對的務實主義。
拉賓並非天生的和平信徒。六日戰爭結束、以色列占領了約旦河西岸與迦薩走廊之際,他曾經狂喜的表示:「以色列現在擁有比大衛王和所羅門王更勝一籌的疆界」;一九八四年,巴勒斯坦人掀起對以色列政權的非武裝抗暴,他下達的指令是:「打斷巴勒斯坦人的骨頭!」
然而,當他瞭解到,巴勒斯坦人丟擲的石塊永遠不可能因鎮壓而停止,他就決定使巴勒斯坦成為以色列與中東國家謀和的一塊基石;不是因為他喜歡,而是因為必須這麼做,他說:「是敵人才需要求和。」
一九九二年拉賓以「和平、安全」的競選訴求打敗對手,重登內閣總理寶座。上任第六天他即提議,願意在耶路撒冷與阿拉怕人會談。
拉賓謀和的速度就像講究快攻的以色列軍隊,他告訴阿拉伯人:「不要浪費時間。」不到一年,以巴和平協定就此簽訂。
當拉賓與阿拉法特談判,並決定將約旦河西岸自治權交還巴勒斯坦,他坦率的對媒體表示:「我已準備做出痛苦的讓步。」當他在美國白宮的草坪上與阿拉法特握手完畢,他再度皺著眉、毫不掩飾的說:「那是我從未夢想過,也最不願意握的手 如果求和的行動對拉賓而言是輕而易舉之事,也許他今天就不會在全球得到那麼高的評價。意志堅強的領袖很多,卻非個個都能放下個人好惡,為國家真正的需要義無反顧的向前,或者就退讓。
拉賓自己曾說:「選擇和平,也需要打一場無形的戰爭。」這位和平戰士在這場無形之戰中,最困難的任務不是與阿拉伯人周旋,而是打破以色列人思想的陷阱。
普立茲獎得主弗里曼在其著作「從貝魯特到耶路撒冷」一書中,以二次大戰「大屠殺恐懼症」,來形容當今許多以色列人的心態;充滿過去的悲情,裹上受害者的外衣,把巴勒斯坦人當成納粹分子,相信自己永遠處於被毀滅的危機、即便擁有最精良的武器,也不相信以色列有力量選擇和平……。
九二年競選時,拉賓告訴選民;以色列必須揚棄被迫害者的心態,「不要再認為全世界都在對抗我們。」
今年面對屯墾區許多以色列人「退讓就會淪陷」的聲浪,他仍然堅持:「以色列是強者,強者有能力選擇讓步。」
和平之役未竟全功
或者正如他對巴勒斯坦人民所說的:「你們不可能完全得到你們想要的,我們也不可能。讓我們抓住和解的機會。」這句話其實也是說給他全體的國人聽。 根據以色列軍隊的傳統,戰爭時,將領總在最前線。在這場和平之戰中,拉賓也走上了第一線,幫以色列人做了前所未有的勇敢選擇,就像國際前鋒論壇報上一篇悼念文寫的:「他突破了傳統與神話的迷思,超越了恐懼與被迫害的柵欄,把人放在第一位。」
將軍的和平之役尚未竟全功。刺殺拉賓的以色列青年阿米爾指責說:「他把以色列帶入性命交關的險境。」在年輕人冷靜而冷酷的語氣背後,依然可以看到深深的恐懼。他,屬於沒有能力讓步的一群,而這樣的人在約旦河兩岸的以、巴陣營裡,都不在少數。
以色列前總理梅爾夫人有句名言說:「寧願做錯而活著,不願做對而死亡。」不知是有心或無意,當十一月四日晚拉賓拒絕穿上防彈衣面對群眾,他似乎以反向的方式表明了這句話。
拉賓不是以、巴和平的第一個犧牲者,也不會是最後一個。而他為中東和平所選擇的退讓,可能還需要更多勇敢的人才有辦法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