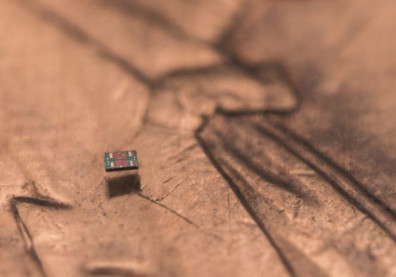「有緣,沒緣,大家來作夥,燒酒飲一杯,乎乾啦!乎乾啦!」出海的雅美人穿著丁字褲,在獨木舟上奮力划行,體力耗盡後大家舉杯唱和,歡盡四海……。一則啤酒廣告攝出蘭嶼原鄉的現貌,鏡頭下,海島顯得純真無慮。
海風吹拂東清村內的黃昏市場,六、七位約莫三、四十歲的雅美族男子對著棋弈,在屋前四方架空的涼台上閒聊。陰沈的雲霧垂降,雅美人原本在陽光下黑亮的膚色,只顯得黯淡無光澤。「沒有工作啦:」這群人嘟嚷著。
找不到頭路,只好看海
實際上,一個鏡頭說不盡蘭嶼海島正面臨失業的景況。根據蘭嶼鄉人口統計,全島有職業收人者僅占一四.七五%。朗島、東清、野銀、紅頭、漁人及椰油六個部落,村村屋屋面海而建,處處是無業的人。觀海,是蘭嶼人的悠閒,有時卻是一種無奈--找不到工作,只好看海。
雖然在職業別統計上,蘭嶼全島有近八五%從事農林漁牧業;但就雅美人而言,徒步到乾涸芋田裡掘墾芋頭、地瓜,潛入海裡刺魚僅是自給自足的體力勞動,沒有買賣,也無收人可言。
然而,明知道島上沒有工作機會,蘭嶼的勞動主力人口--介於二十五歲至五十歲的中青代雅美人,其中仍有不少人選擇回到海洋的故鄉。根據統計,在老人及孩童這兩個年齡層的男女比均為一:一的情況下,中青代男女比反而呈現一.五:一的情況,顯然回流的男性人口數遠超過女性。
十七歲就離開蘭嶼、滿懷憧憬到台灣發展的鄭新友,先在林務局描任造林的工作,因為收入不高,又選擇跑船流浪四方,接著是工廠、版模業等處;在打滾十多年之後,因太太在台灣過世,按照雅美人的習俗,他回到蘭嶼。但是「回來也不知道要做什麼啊?」鄭新友一邊說,一邊把頭撇向海。
十五歲就陸續在台灣住過不同地方的東清村民席.傑勒吉藍,因為太想念蘭嶼的海水,最後選擇歸鄉之路。在沒有工作機會下,他自己繪製雅美族的圖騰,做點手工藝品賣錢。
「失業」的雲霧在紅頭山盤桓,遲遲不肯散去。
舊稱「紅頭嶼」,蘭嶼自民國五十六年開放觀光。對當時出生的雅美小孩而言,「台灣真是天堂,蘭嶼卻如監獄,」蘭嶼作家夏曼.藍波安在(冷海情深)一書中憶起兒時看到台灣來的貨輪:「一路上我們雀躍地吶喊著:「台灣船,來啦!台灣船,來啦!」……希望貨輪下一趟再來時,我們能偷渡到台灣,這才是我們期待貨輪來的第一個願望!」而在終於踏上台灣之土,做些零工、開計程車後,藍波安也選擇回到蘭嶼--PONGSO NO TAO,人之島。
蘭嶼人沒有定位怎麼辦?
「貨輪承載雅美孩子的希望、年輕人的傍徨、老年人的焦慮。」藍波安寫出雅美人的台灣情結,也道出雅美中青一代夾在傳統與現代、世代交替間的沈痾。
三十年前觀光之門大開,把蘭嶼人推向一個想像的天堂--台灣,雅美中青代就在這時空環境下到台灣發展。一路跌跌撞撞,最後在「傳統包袱丟不開,又要面對外界不同族群」的壓力下離開,曾在人間雜誌和自立晚報服務、三十五歲的郭建平說道。
回蘭嶼四年,一直沒有工作的鄭新友說:「蘭嶼人沒有定位。」
觀光打開蘭嶼人外出的道路,也攪動小島的平靜。大量觀光客為蘭嶼人帶來羞怒,外來文化讓當年出生的中青代在傳統與現代的夾縫中求生存。
郭建辛記得讀小學時,某天和家人在涼台上吃飯,一位歐巴桑觀光客一腳步跨進平台,將手浸人全家還沒喝的湯,大聲呼道:「有啦,有摻鹽的啦!」
海天一頁湛藍。細紋垂布臉上的老人專注地看海,彷彿一眼把海的澄淨看透。一旁的中青代雅美人淡淡道「他們都是在等死。
老的拄著文化,新的卻在觀望
寒暑假期間,難見蘭嶼青少年的蹤跡,雅美阿公說他們都在台灣。待九月開學第一天,在蘭嶼中學的校舍內才見到人影。
為了看一看台灣,蘭嶼中學三年級學生謝惠珠在國一放假時,即一個人在高雄旅社過夜。雖然今年蘭嶼國中改制為完全中學,明年應屆畢業生可直升高中或高職,但是她還是會優先選擇到台灣就讀。「因為那裡東西比較多,」謝惠珠張著濃眉大眼,吐了吐舌頭道。
在蘭嶼,即使學生一路讀到高中都不用繳學費,還是難留他們想飛的心。才改制為完全中學,蘭嶼中學卻面臨收不到高中部學生的窘境。校長江銘鉦及輔導主任鍾銼波只得帶著名單到台灣,按圖索驥地「找到」十六名學生對他們動之以情。校長感慨學生的價值觀改變:「有的學生會直接問你「回來有什麼好處?」」
「老一輩的人拄著文化,新一輩的人卻都在觀望,」經過自省,郭建辛選擇到紅頭教會佈道,才能更瞭解族人的痛苦。
週日上午,紅頭教會詠唱雅美族聖詩「一九九六年新希望」的歌聲在紅頭村飄颺。教堂高掛的白色木十字架,刻畫有蘭嶼海象紋及象形紋的印記。環繞在教堂四周的歌聲唱道:「有主做我的朋友,我總是覺得生活無憂無慮;有主恩惠我,我總是覺得有了新希望。」掛滿黑、紅、白色珠串的雙手,隨聖歌的節奏拍合擊聲;然而,生活真的無憂無慮嗎?
一位雅美婦女為了幫先生辦理健保醫療看病,必須追繳積欠的保費。隔天,她拿了一簍地瓜和芋頭來充當保費。鄉長廖班佳也痛心:「要怎麼辦?我心裡也很難過。」
根據統計,全島只有二分之一人口加入健保,至於其中有多少人因未繳保費而中斷,連承辦人員也不清楚。
一面自省,一面思考出路
全島唯一的醫護單位,就是島嶼南端紅頭村內的衛生所。所內兩位內科醫師及一位牙科醫師除了處理專長疾病外,還得處理常見的交通意外傷害。比較嚴重的傷害,只得層層上報,請航警局派直升機支援。「但是飛過來的機率很低,」醫師周仁祥指出。
八月初,一位雅美老婦人蕭張逢龍因摔車自港口連跌落,經衛生所診所為開放性骨折,只得運送到台東就診。結果上午八點出事,一直等到十一點才搭上八人座小飛機拉開。周仁祥也懷疑:「老人家只能平抬,怎麼上小飛機的都不知道。」
去年被颱風浪沖壞的機場跑道正在整修,蘭嶼每天只有四班飛機來往台東。班機少,機票又比到綠島貴一倍,「蘭嶼的盛況不再,」在蘭嶼民航站待了五年的工作人員說。
面對資源的拮据及人口外移的現象,這些在台灣混過日子的雅美族中青代,都很想為蘭嶼做點什麼。郭建平正在蘭嶼籌備「丁字褲文化教室」,介紹蘭嶼的文化和建築等,讓台灣人能多瞭解、尊重蘭嶼文化。夏曼.藍波安在「刻意」失業期間,用力地寫出屬於蘭嶼的海洋文學,記錄蘭嶼島上的生活經驗。邱新友看兩艘盜採珊瑚的台灣漁船「不順眼」,即聯合村民齊力趕船。
他們一面自省,一面也在替蘭嶼思考出路。郭建平說,要減少人口外移,就要能提供貨幣。在有效計算土地承載量之下,也許農業加工是可行的路。另一方面,去年才到綠島「觀摩」過的蘭嶼鄉長廖班佳指出,發展觀光是必經的路。
漁人村入口處,公路旁矮白的護牆上幾個油漆大字寫著:「希望您來蒞臨本村」。
蘭嶼歷經三十年的觀光路,大起大落後,在幻滅中等待重建。